
在凝視死亡的現代體驗中,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之死無疑是個重大事件。1975年10月16日佛朗哥開始覺得胸口疼痛呼吸困難,起初他不以為意,以為只是小感冒,清楚他的心血管疾病病史的主治醫生卻不敢大意,立刻召來全國的心臟病專家隨時待命,隔天佛朗哥還召開了內閣會議,會議不到半小時,佛朗哥就因為冠心病心絞痛發作被迫離席,接下來將近一個禮拜,現代醫療傾盡全力也無法阻止死神:左心衰竭、內臟出血、尿毒症,一次次的急救與折磨據說讓這位四十年間主宰數千人生死的獨裁者虛弱地呻吟:「要死掉怎麼這麼難?」
佛朗哥的生死體驗如今已從奇觀變成常態,根據葛文德的說法,1945年以前一般人都在自己家裡過世,到了80年代,只有不到17%的人因為猝死才在家中過世。也就是說,將近八成的人在醫院,在病房渡過了生命的最後時光,同時,也經歷了佛朗哥那曾經被當作奇觀的痛苦:一次次地在醫療急救過程中倖存,又一次次地更接近死亡。
對死亡主題相當執著的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導演布紐爾(Luis Buñuel)在他的自傳《我的最後一口氣》對佛朗哥抱以無限同情,他說最糟糕的死亡是「用現代醫藥的回春妙手牽制死神,這是一種看不到終點的死亡,以希波克拉底之名起誓的醫生們,發明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精緻的酷刑:還好!還活著!有時候我真的很同情佛朗哥:用人工的方式活上個把月,代價是令人無法置信的折磨。」
而對同樣執著於死亡的傅柯來說,佛朗哥在他生死彌留之際所經歷的「看不到終點的死亡」,象徵的是兩種現代政治權力的戲劇性交會:一種是獨裁者佛朗哥所象徵的,絕對主宰生死的絕對權力;另一種是以調節生命為目的,主要透過醫藥與公共衛生系統而運作的生命治理權力。
傅柯的說法有時候給旁觀死亡的現代人一種假象,彷彿急診室的醫師有通天的能耐可以決定生死,但在與死神的拉鋸中,醫療現場經常只是被迫製造既生又死,不生不死的活屍(neomorts):在失去意識的狀態之下被保持「活著」的肉身,好延續法律人格的存在,或者進行器官移植捐贈,生命治理權力據說能把死亡抵禦在生命的邊界,實情是,在臨終者的醫療現場,往往只有生與死無法區隔的活屍狀態。
站在外科醫師葛文德的立場,認為醫療體系可以延長生命正是最大的迷思,事實上醫師無能挽救肉體的衰弱,更對垂死衰老者在老年安養體系中「沉悶、寂寥與孤力無援」的體驗無能為力,在這些生命「無限延長」過程中,伴隨的常常是折磨與痛苦,還有免不了的欺騙與謊言──「加油!一定會好起來的!」
旁觀死亡之人(家屬以及熱烈期待各種醫學奇蹟的媒體)與凝視死亡之人對臨終階段對「活得有價值」的歧見,是身處醫療現場的醫師糾結的地方,在葛文德講述的臨終故事中,凝視死亡的臨終者往往比旁觀死亡者更為豁達,他們不需要被擺佈在各種醫療儀器中倖存,他們需要的是有意義地活著:
令人痛苦的弔詭正在此處──我們大抵讓醫師來決定我們餘生要如何度過。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都把疾病、老化與人之必死,當成醫療問題。在社會再造的實驗中,我們重視專業技能,把自己的命運交付給醫學專業人士,卻不在乎醫學專業人士是否了解我們的需求。
葛文德鼓勵臨終者,建立創造自己生命意義的新社群──也鼓勵旁觀生命者放手,醫療體系不應該在兩者之間糾結為難,只有能幫助病人完成更大的人生目標,始終具有風險與犧牲的醫療才有插手的空間。
在他看來,凝視死亡的臨終者,事實上具現了我們所能想像,最崇高的豁達:他們時日無多,只尋求單純的快樂,像是親友的陪伴、規律的生活、享受美食、感受陽光灑落臉上的美好乃至於單純的奉獻等等,這當中絕不包括旁觀死亡者強用醫療體系強加給他們的,對生命的無意義延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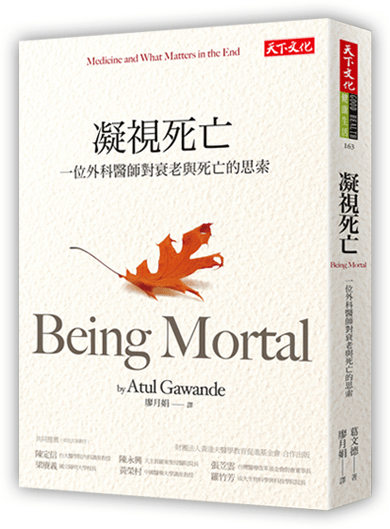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凝視死亡:一位外科醫師對衰老與死亡的思索》 Being Mortal—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作者:葛文德(Atul Gawande)
出版:天下文化
日期:2015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