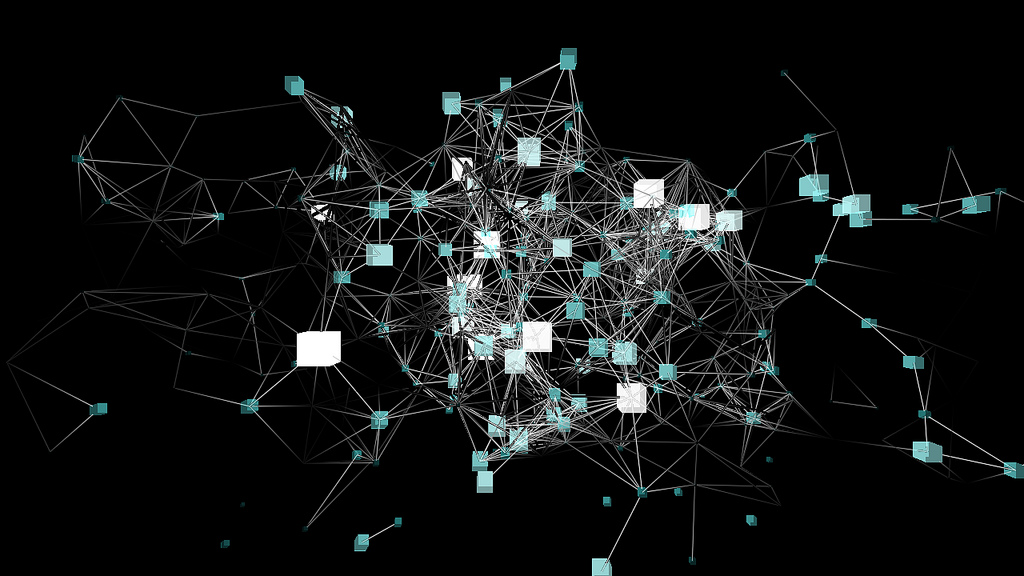
然後醫生說,你能治好我嗎?
我說,請相信我,絕對沒問題。
當他這樣問,我就知道成功了。他是這個月最後的客人,一直不好對付,拖拖拉拉了一個禮拜,終於能鬆一口氣了。我盡量簡單明確地對「他」下了幾個特定的指示,小心地完成結尾的部分,再讓「醫生」回來。
然後醫生說,結束了嗎?
我說,結束了。
將醫生送出事務所之後,我開始收拾東西。接下來我有五天的休假。當我還在細細品味著這件事的時候,主管從後面走過來。
主管說,辛苦了。
我說,嗯。
主管說,累了嗎?
我說,還好。
主管說,最近怎麼樣?
我說,普普通通的。
主管說,是嗎,那好。
到底想說什麼?主管不是會溫馨地噓寒問暖的人。
我問,怎麼了?
主管沉默了一下,然後說,有消息說那邊開始動作了,目的是什麼還不確定,不過無所謂,事務所的安全屋都準備好了。主管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我們不希望有任何風險。
我知道主管的意思了。
我說,有必要嗎?
主管沒有表情,緩慢地說,我們不希望有任何風險。
聽起來是無法商量了,事務所一向謹慎。
我說,我知道了。
主管點點頭,然後說,只是住個兩三天,就當作自己的家吧,裡面什麼都有,沒什麼不方便的,等一下會有人來接你過去。
我說,嗯。
主管像是在考核這個回應裡的涵義一樣,表情高深莫測。過了一會兒後他說,保重。然後安靜地離開了。
我坐在辦公室裡,等待著。事務所一如往常地安靜得不得了。我一直很難適應這個。事務所內部的隔間非常複雜,隔音良好,幾乎每個僱員都有各自的辦公室甚至是各自的走道,不會發生跟別人擦肩而過的情況。而這一切都是為了隱私。
我們的工作很特殊,是處理人的「身分」問題。不過,不是法律上的身分,而是精神上的身分。使用「身分」這個詞彙或許有些侷限。那或許可以也作為某種單向度的意識的標籤來說明。不過,這種說法也不是很好。那終究還是要以「身分」這個詞彙來表達最適當。
事務所專長的項目,是偏向職業性質的身分問題,比較講究技術性與專業性,不過準確性也相對地提高。所謂的「處理身分問題」,就是處理客人工作上無法負擔的身分混淆與疊合問題。客人的工作需要有一定的工作「對象」,客人與工作對象之間身分的歪曲,就是我們在處理的部分。
具體地說身分問題的影響。以上一位客人來說,他的職業是醫生,醫生就是他的工作「身分」。醫生的工作「對象」是病人,面對的就是病人的「身分」。他的工作建立在醫生的「身分」與病人的「身分」的關係上。但是因為某些原因,病人的「身分」片段地跑到了醫生的身上,儘管沒有任何客觀上的知識與能力的減損,這位醫生還是沒辦法面對病人了。
我們就是在處理這個。
有人輕輕地敲響門。
我說,請進。
門打開,一個年輕女人走進來
您好,她說。
車子已經準備好了,隨時都能出發,她說。
我知道了,我說。
我提起行李。她讓我先走出門外,關上門,帶著我走到停車場。那裡停放了三輛外觀一模一樣的黑色轎車。
車子都以不同的安全屋為目的地,同時出發,您可以任意選擇要上哪一輛車。她說。
真謹慎啊。我說。
我們不希望有任何風險。她說。
到哪裡都無所謂,我上了中間那一輛車。上車之前,她突然靠過來說,提醒您一下,請盡量不要外出,飲食都有專人負責準備。她停頓了一下,接著說,安全屋裡可能沒有足夠的娛樂設備,怕您無聊所以準備了這個。
她遞出一個黃色信封。
這是什麼?我問。
下一位客人的資料。她說。
我看了信封一眼,然後接過來。
是誰這麼貼心?我問。
主管交代的。她說。
我打開後車門,坐進去。駕駛座與副駕駛座都坐了人。
幫我謝謝他。我說,然後關上車門。
關上車門的時候她好像說了什麼,沒聽清楚,透過窗戶我望了她一眼,她保持微笑,直到車子遠離。
車子無聲地滑過城市,信封令人厭煩地躺在旁邊。我想我是真的有點累了。這個工作非常耗損精神,作為這個領域的頂尖與革新者,更是耗損精神。事務所也知道這個,對我總是非常禮遇。當然,那只會持續到某一天而已。等到大家都學會了新方法,我又會變回普通的僱員。
我想我是真的有點累了。
以我目前的財產來看,大可一走了之,夠我過好幾輩子了。但是我知道那都是紙上財富,終究是螢幕上的幾個數字而已。看不見、摸不到。只要有人彈一下手指,「啪」地一聲我又得回來賣命。
絕對不要與事務所作對。
對事務所來說,把一個人逼到走投無路比烤一片吐司還簡單。各式各樣的人來到事務所尋求協助,光是我服務過的客人就有﹕醫生、心理諮商師、法官、獄卒、律師、私人偵探、記者、專業線民、教師、函授教材業務員、房屋仲介、超級直銷員、政客幕僚、商業間諜、臥底情治人員、導遊、公益團體志工、禮儀師、算命師、神父、乩童、導演、經紀人、漁夫、單親媽媽、皮條客、伴遊女郎……從各種小地方累積起來的人脈與影響力,有時候比掌握幾個大人物還要更加強大,更何況,事務所對這兩套方法都相當嫻熟。
所以,絕對不要與事務所作對。覺得快要忍受不了的時候,就想一想斐濟的海洋吧。
車子無聲地滑入某間公寓大廈的地下停車場的時候,我被人輕輕地叫醒。副駕駛座的男人陪同我上去。我們搭電梯到五樓,然後走樓梯到八樓。他帶我到門前,抽出鑰匙打開門。
請進吧,按照規定我不能進入。他說。
他站在門口,等我進去。
我站在門口,等他給我鑰匙。
我們僵在門口。
呃,鑰匙……
我試著說。
我會替您關門的。他將手扶在門上說。
我走進去,然後聽見他鎖門的聲音。
該死的,他們不打算讓我出去。
我花了半分鐘逛了一遍後,坐在沙發上,然後就沒事了。這裡好像樣品屋一樣。我發呆了一會兒,然後又發呆了一會兒,再發呆了一會兒後。只好打開信封看看了。
但詭異的是,裡面什麼資料也沒有,只有一疊白紙。
搞什麼啊,我想。
我試著冷靜地分析,這樣的結果會出現只有兩種可能狀況,刻意的,或者非刻意的。我直接排除非刻意的狀況。以事務所的謹慎程度與嚴密的工作流程,不可能出現這種錯漏。
所以是刻意的。刻意的狀況也可以分成兩種,是事務所的意思與不是事務所的意思。
假設是前一種,這或許是某種測驗。測驗什麼?應變能力,還是我的清白?不太可能是後者,如果是後者應該要讓我有機會洩漏資料才對,而不是給我白紙。
假設是後一種,那表示事務所有環節被滲透了。目的呢?這麼做只能延遲我得到資料而已。延遲能怎樣?加工變造甚至銷毀資料。但是白紙不是反而令我起疑嗎?給我片段的資料不是更好?或許,是刻意向我展示事務所已經有他們的人了?安排接送的女人、車上的兩人,還是主管?這麼做是要由我的反應判斷是否要進行接觸嗎?
兩種假設並不相互排斥,有可能就是在測驗我面對事務所被滲透的應變。
我決定先不聲張。先觀察、後判斷。
這是我的格言。
四天後主管打電話過來。
「喂,過得怎麼樣?」
「還可以。」
「資料看了嗎?」
「嗯。」
我手心冒汗,緊繃地全神貫注在主管接下來要如何回應。
「很好。」主管輕輕地笑著說。「跟認真的人工作就是比較輕鬆,所以我喜歡你,知道嗎?才把這樣重要又有一點點麻煩的工作交給你。」
「嗯。」
主管停頓了一下。
「客人會過去你那裡。」主管沉穩地說。
「這裡?」我驚訝地問。「安全屋嗎?」
「這是上面討論的結果。」
「嗯。」
「我們不希望有任何風險。」
我等著主管繼續說。
「明天下午兩點過去那裡,沒問題吧?」
「沒有。」
「很好。」
然後主管就掛斷電話了。
無法判斷,我想。
沒辦法從主管的話語與語氣中驗證我的疑心,但是我的懷疑卻反而增加了。客人要到安全屋來?為什麼?真的是客人要過來嗎?
不知道。
晚上我幾乎睡不著,在心裡不斷思索著。如果一切只是測驗,那就沒什麼,頂多是證明我可能需要多幾個人保護。但如果不是呢?
先觀察,後判斷。無法判斷時,就以最糟糕的狀況考慮。
這是我的格言。
二年前,我開發了新的身分處理方法,成為事務所的珍貴資產。
一般來說,發生身分問題時,客人身上疊合了兩種身分﹕比較大而完整的原本的身分、比較小而破碎的工作對象的身分。舊方法是,把不屬於客人的身分直接剝除,讓客人的恢復原本的身分。但問題是容易復發,完全修復的機率只有50%。更嚴重的是,那個被剝除的身分,必須由我們來承擔。當我們把各個客人身上的不完全身分全部承擔下來,會造成很大的精神耗損,工作極限只有一年半。
新方法的步驟完全不一樣,是先拿走客人原本的身分,把有問題的身分留在客人身上。因為剩餘的身分並不完全,這時候客人會進入很不穩定的脆弱狀態。而已經具有客人原本身分的我,會直接使用這個身分應對客人目前的身分,也就是像正常時候客人面對他的工作對象一樣。以完全應付不完全,非常輕鬆,只要下幾個指令,像是「安撫」一樣,然後再把原本的身分還給客人就可以了。新方法最重大的不同,在於有問題的身分仍然在客人身上。我們只是把解決的「姿態」展現給客人,把解決辦法植入客人腦袋裡而已。新方法的復發率降到5%以下,而且能在相同的精神耗損下處理更刁鑽複雜的問題。這讓事務所站上這個領域的領導地位,也讓我成為敵人的眼中釘。
客人在下午兩點準時出現,戴著頭套,被上次副駕駛座的男人引導著走進來。我會在門外等。他說,然後就鎖上門。
我讓客人坐下來。
我說,可以拿下來了。
他拿下頭套。
他看起來非常年輕,好像不超過20歲。他的視線放在我的膝蓋上,態度平順不給人壓力,整體感覺好像缺乏個性。我採取被動姿態,暫時不說話,而他的被動姿態卻更徹底。這麼年輕讓我覺得不太可能是「接觸的人」。只是個煩惱的孩子吧。
我說,很抱歉讓你戴上那個。
他看了我一眼,又低下頭。
沒關係。他說。聲音平淡,沒有令人戒備的地方。
我說,你從哪裡知道事務所的?
朋友說的。他說。
我說,你有工作嗎?
算是有吧。他說。
我說,是什麼?
殺手。他說。
什麼?
他的回答讓我驚訝。但是我很快鎮定下來,因為我不太相信他。
我說,你在開玩笑嗎?
他看了我一眼,抿了抿嘴唇。
沒有。他慎重地說。
所以才要他到安全屋來嗎?因為不想在事務所牽扯到犯罪?不想留下教唆殺人的證據?
我說,對象是誰?
一個四歲的小孩。他說。
我說,為什麼要殺他?
不知道。他說。
我說,他有什麼特別的?
好像是某位候選人的女兒。他說。
我說,原來如此。
他輕輕點點頭。
我說,你試過了嗎?
還沒。他說。
我說,為什麼?
我想我下不了手。他說。
我說,為什麼?
她只是一個小孩啊。他說。
我說,你以前也這樣過嗎?
沒有,這是第一次。他說。
我說,不能乾脆放棄嗎?
不行。他說。
我說,為什麼?
有不得不這樣的理由。他說。
我說,說說看。
這是規定。以前有個人要殺我,可是下不了手。他後來自殺了,而我必須接替他,不然我也會被殺。他說。
我說,你還不想死?
對。他說。
我說,好吧,我知道了。
為了確定你的情況是我們能處理的,我需要催眠你。我說。我說了謊,這個不是一般程序。
他說,沒問題。
我讓他斜躺在沙發上,撥放音樂。這有助於放鬆。順著我的指令的引導,沒過多久,他進入了催眠狀態。
你真的是殺手嗎?我問。
他說,對。
聽見他的回答,我輕輕嘆了一口氣。真的是殺手啊。這件事並不怎麼動搖我的良心。反正人都是要死的,而這個男孩看起來不像是太凶殘的人。
你對那個小孩的感覺怎麼樣?我說。
他說,哪個小孩?
就是你要殺的那個。我說。
他說,我沒有要殺任何小孩。
什麼?
這是你剛才自己說的。我說。
他說,我說謊了。
為什麼?我說。
他說,因為我被這樣交代。
誰交代的?我說。
他說,我的僱主。
誰是你的僱主?我說。
他說,不知道。
是你的僱主要你到這裡來的嗎?我說。
他說,對。
為什麼?我問。問出這個問題讓我不安。在我說出口的當下,我感覺我好像已經知道他要如何回答了。
因為要來殺你,他說。
接下來的事發生得很快,他從沙發上彈起來,右手多了一把刀,向我刺來。我用左手撥開他的手腕,右手握拳、中指指節特別用力突起,朝他的喉嚨反擊。他被擊中,痛得蹲下來大聲乾嘔。
我想再給他一拳,奪下他的刀,但他很快重整態勢,半蹲著防備。他抬頭瞪著我。我趕快躲入廁所,鎖上門。
冷靜下來,我想。
我猜想,他大概事先被進行了相當深度的後催眠暗示,當他再被其他人進行強度較低的催眠,並問到特定問題時,會強制清醒並攻擊催眠者。也就是我。
我沒把握撂倒他,外面的人也不一定能信任。方法只剩下一個了﹕奪走他的身分。
這是我最擅長的。
要把別人的身分拿過來,只要將自己變成「無身分」就可以了。我的方法是把自己所有記憶與情感都埋入潛意識,變成一個「空心人」。當對方的身分過渡到我這裡後,記憶回復,我會形成某種雙重人格的狀態。
我事先對自己進行了催眠,只要我吹出特定頻率的口哨,就能自動完成這些動作。
我深吸一口氣。打開門。
我看見他猛然轉身,舉起刀。
他朝我跨出一步。
我吹起口哨。
在那瞬間,我明白,一切結束了,他就是最後的客人。
我成為了殺戮者。
我中了他們的計。
(本文為【小說無差別格鬥】第二季主題「然後醫生說」投稿作品)
圖片credit: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