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東尼‧賈德
譯|區立遠
十七‧話語
我是在話語裡長大的。每當在廚房的餐桌上,祖父、叔叔伯伯以及逃難者們氣勢洶洶地對彼此說著俄語、波蘭語、意第緒語、法語以及他們自以為的英語,爭相傾倒各種論斷與質問,這時種種文詞就從桌邊跌下,落在我所坐的地板上。從愛德華時期的大不列顛社會黨【註1】漂流出來的人物經常泡在我家廚房;他們愛說教,總是宣揚著「真正的大業」。我常常一連好幾個小時,高興地聽著這些自學出身的中歐人爭論著馬克思主義、猶太復國主義、社會主義等,直到深夜。當時我覺得,講話,好像就是大人存在的目的。這種印象後來也從未從我腦裡消失。
輪到我的時候,為了尋找自己的定位,我也講話。在同樂會上我會表演當場記住、複誦跟翻譯多國字詞。「喔,他以後可以當律師」,他們會說。「他能迷倒樹上的小鳥」:為此我在公園毫無成果地嘗試了好一陣子;到了青少年時期又試圖用倫敦東區佬的英語來施展我的魅力,但成效並沒有更好。之後我就脫離了在多種語言之間進行轉換的熱烈階段,開始追求英國廣播公司冷靜且優美的英語風格。
在一九五〇年代,當我讀小學的時候,英文無論是在教學上還是使用上,都是嚴守規則的。學校教導我們:哪怕是最微小的句法失誤也不可接受。對「好」英文的強調,正處於巔峰時期。拜英國廣播公司與電影院新聞短片之賜,我們說話的方式有全國通行的正確規範;階級與地區的權威不只決定你怎麼說話,還決定什麼話才適合說。「地方腔」充斥(我的口音也算),但是有上下尊卑的差別:通常根據社會階層以及距離倫敦多遠來排行。
處在高峰的英文散文正在消逝中;那餘暉深深吸引著我。讀寫能力普及的時代,也意味著讀寫能力的衰落,正如李查.霍加特在他感傷的散文《讀寫能力的用處》所預示。抗議與反叛的文學正在文化的地景中升起。從《幸運兒吉姆》到《憤怒的回顧》,以及五〇年代末的「洗碗槽」影劇,與階級緊密相關的語言習慣──也就是令人窒息的得體措辭以及「適當」的說話方式──遭受猛烈攻擊。然而那些「蠻族」本身在猛烈批評傳統的同時,都採取了一致認可的正確英文,而且還帶著完美的抑揚頓挫。閱讀這些作品時,有一個念頭從未出現在我的腦海:反叛,就一定要放棄優美的形式。
到我進大學的時候,遣詞用字成了我的「拿手好戲」。一位老師曾經模稜兩可地評論我有一種「能言善辯的演說家」天份,天生容易獲得所屬圈子的信賴(對於這一點我非常有自信),但又帶有一種圈外人批判的鋒芒。牛劍一對一的導師課會給言辭便給的學生很大的收穫:「新蘇格拉底教學法」(「你為什麼這樣寫?」「你這樣寫是什麼意思?」)會要求唯一的導生詳盡地解釋自己的想法;但這樣做又可能會讓害羞與深思型的大學生陷於不利,以致他們寧願在研討課上躲到教室最後面。我對自己善於表達的信心於是更加鞏固了:這不只是聰明才智的證據,而是聰明才智本身。
我是否曾經想到過,在這種教育情境裡老師的沉默也很重要?當然,沉默從來不是我擅長的項目,不論是當學生還是做老師的時候。我的一些最出色的同事們,隨著年紀漸長,在辯論或甚至談話時都退縮到不做清楚表述的地步,在明確表態之前都考慮再三。我真羨慕他們有這種自我克制。
***
能言善辯通常被認為是一種攻擊性的才能。但是對我來說,能言善辯的功效根本上是防衛性的:語言能靈活應變,就允許你製造一種假裝的親近感──一方面傳遞「我們很熟」的訊息,同時卻保持距離。這是演員做的事。然而這個世界並不真是一個舞台,而這麼做帶有某種不自然的成份在內:只要看看現任美國總統【註2】就會明白。我也號令語言來抵禦他人過於親暱的言行──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我對新教徒與美國原住民會有一種浪漫的偏愛,因為兩者都屬於沉默寡言的文化。
在語言的問題上,當然,外來者常常會被蒙蔽。我記得有位麥肯錫顧問公司的美籍資深合夥人曾對我說,早期他們公司在英國招募員工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幾乎無法挑選年輕的工作夥伴。每一個看起來都如此能說善道,分析時下筆如神:要怎麼分辨誰是真的聰明,誰只是演技精湛?
言詞可能騙人,以致有害與不值得信賴。我記得曾經著魔一般地讀著一本蘇聯史:那是年老的托洛斯基主義者以撒.多依徹,在劍橋的特理威廉講座上編織的一部形同幻想的歷史(《未竟的革命:俄羅斯一九一七至一九六七》,一九六七年出版)。那文字的形式是如此優雅地超越了內容,以至於我們毫不置疑地接受了後者:擺脫這本書的毒性是相當一段時間之後的事。修辭遣字的十足功力,不論訴求為何,不必然表示內容就有原創性與深度。
儘管如此,不清不楚的表達必定表示思想的缺失。一個習慣因為說話的意圖而非內容被讚美的世代,大概會覺得這個論斷很奇怪。清楚表達的能力本身在一九七〇年代成為被質疑的對象:人們從「形式」撤退下來,轉而偏好對僅僅是「表達自我」就不加批判地給予讚許,特別是在課堂上。但是鼓勵學生自由表達意見、避免他們被過早施加的沉重權威壓垮,是一回事;希望教師撤回對語言形式的批判,並期待他所授予的自由將有利於學生的獨立思考(「別擔心你說的方式,理念才是最重要的」),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九六〇年代過去了四十年,現在已經沒有多少指導者還有足夠的自信(或訓練)揪出學生不恰當的表達方式,並對他清楚解釋,為什麼這恰恰阻礙了智性的思索。我這一代人的革命,是導致這個崩潰的重要推手: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裡,獨立自主的個體都被賦予了不容低估的優先性──「做好你自己」這句話披上了變化多端的外衣。
今天,不管是在語言或藝術裡,「自然的」表現方式比技巧受到更大的喜愛。我們不加思索地認為,這樣可以更有效地傳達真理,就像更能夠傳達美一樣。但是亞歷山大.波普更了解此中奧秘。【註3】在西方傳統的許多世紀裡,你的立場表達得如何,與你的論述的可信度有緊密的對應。修辭風格也許有時簡約有時巴洛克,但是風格本身從來不是無關緊要的事。而且,所謂「風格」也不僅是文句調整的好壞:表達的拙劣顯示思想的貧困。語詞如果混亂難懂,最好的情況是代表理念也混亂,最壞的情況則代表偽造與假裝。
學院書寫的「職業化」──以及人文學者對「理論」與「方法論」的安全感刻意的死抱──常常偏愛故弄玄虛的風格。這從反面鼓勵了一種膚淺的「通俗」表達形式,像假鈔一樣在市場上流行起來。在歷史學科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電視名教授」的興起,其魅力恰好建立在他聲稱自己能招來廣大的觀眾──在這個同行學者已經沒有興趣繼續溝通的時代裡。然而,儘管上一個世代的通俗學術作品是一點一滴地將作者的權威注入平鋪直述的文字裡,今天「簡單易懂」的作者卻令人不快地突入觀眾的意識裡。吸引觀眾注意力的再也不是主題,而是那表演者。
***
文化自信的匱乏,會在語言上複製同樣的身影。這句話套用在科技的進步上也仍然成立。在一個臉書、MySpace與推特的世界(更不用說傳簡訊),簡短的間接指涉取代了詳盡的闡述。網際網路一度像是可以進行無限制溝通的契機,然而這個媒介日漸向商業化傾斜(「你買的東西定義你是誰」),造就了本身益發的貧困。我的孩子在同儕身上看到,他們在手機上使用的縮寫與簡稱開始滲透到真正的溝通:「很多人像簡訊那樣講話」。
我們應該為這個現象感到憂慮。當文詞開始變得破碎,它們所表達的理念也不能倖免。如果我們更重視個人的表達方式而輕忽形式上的慣例,就等於把語言私有化,一如我們將其他如此多東西私有化一樣。「當我用一個字」,矮胖子【註4】說,語調頗為輕蔑:「那個字就剛好代表我想說的東西,既不更多,也不更少。」「問題是」,愛麗絲說,「你怎麼能讓同樣的字代表那麼多不同的東西」。愛麗絲說得對:結果會是全盤混亂。
在《政治與英語》書中,歐威爾斥責他當時的人用語言來使人困惑,而非傳達訊息。他的批評所針對的是說話者用心不良:人們使用差勁的文字,是因為想說的東西本來就不清楚,不然就是故意閃爍其詞。然而我們的問題,依我看來,是不一樣的。今天,粗糙的文字所顯示的,是在智性上缺乏自信。我們說得很糟糕、寫得很糟糕,因為我們對自己所想的沒有信心,也不願意做明確而堅定的斷言(「個人意見認為……」)。我們並未遭遇「新語」(newspeak)的興起【註5】,而是冒著「無語」(nospeak)盛行的危險。
如今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意識到這方面的憂慮。在神經元疾病的牢牢掌握裡,我正快速地喪失控制語詞的能力──即便我跟這個世界的關聯已經被縮限到只剩下語詞。在我無聲的思想裡,這些語詞仍然以無懈可擊的紀律、在未曾減損的範圍內排成隊形──內部的景觀跟從前一樣豐富──但是我再也無法輕易地把它們傳達出去。母音與發嘶聲的子音從我的口中溜滑而出,連親近的助手都覺得音不成音、含混難辨。我的聲帶肌,這個陪伴我六十年的第二自我,正持續衰退中。溝通、表現、斷言:這些現在竟成了我最弱的項目。將存在翻為思想、思想化為話語、話語轉為溝通,這些將很快超出我的能力之外,而我就這樣被侷限在自我沉思的修辭風景裡。
儘管我現在對那些無法發聲的人有更多的同情,但我仍然鄙視含混不清的語言。自從無法自由與人溝通之後,我比任何時候都更體會到,溝通對群體是多麼關鍵。那不只是我們得以共同生活的手段,更是我們共同生活的意義的一部分。那些從小陪我長大的豐富的話語,本身就是一種公共空間──而適當維護的公共空間正是我們今天如此缺少的東西。如果話語陷於荒蕪,又有什麼能夠取代呢?話語是我們僅有的一切。
(本文為《山屋憶往》部分書摘)
註一:愛德華時期指一九〇一至一〇年。大不列顛社會黨是成立於一九〇六年的極左派政黨,至今仍存在,但人數少,在國會無席次。
註二:這裡指的是歐巴馬總統。
註三:作者註:真正的才情,是為自然加上出色的裝扮;時常被想到,但表達從未如此美妙。──亞歷山大‧波普,《論批評》(Alexander Pope, Essays on Criticism, 1711)
註四:出自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鏡中奇遇》(Looking Through Glass)(1872)。矮胖子是一個蛋型人物。
註五:新語是歐威爾在《一九八四》裡購想的人工語言,特色是簡化詞彙,消滅表達多樣性,凡能表達自由、革命與批評政府的用語都被刪除。預計於二〇五〇年全面取代「舊語」,也就是故事設定中一九八四年當時的英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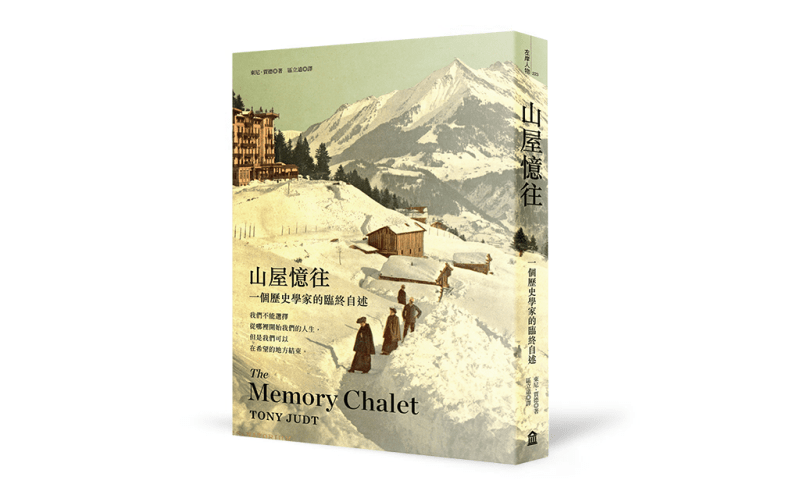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山屋憶往》Memory Chalet
作者:東尼‧賈德(Tony Judt)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15
圖片credit:fronterad.com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