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電影經常有種不在典型善惡二元價值論框架中的傾向,例如李滄東的《綠洲》探討了性障礙者的性、《薄荷糖》則是以人與國家的暴力為主題,又或者是朴贊郁的犯罪三部曲。我們首先必須要知道的是所謂善惡的概念是西方的、基督教式的,如同天國與地獄一般劃分出了世界的二端:一邊是A(善),另一邊則必然是非A(非善,即惡)。不受此價值觀囿限而創造出的作品,則會揭露出如此的標準篩選出的結果是被剪去的,而這創造的過程則是一種還原,把那些被丟棄的碎片給拼湊回來。
故事以從首爾調職到偏鄉擔任派出所長的李英男(裴斗娜飾)警官為起,剛到小鎮時受到的問候是一位老婆婆似乎酒駕騎著機車與李英男所駕駛所載的中年男警員說笑著:「你的新老婆啊?真走運啊你,今晚開心點啊!」看似無傷大雅的玩笑,卻無意地顯示出女人被預設是性對象的潛在台詞。
另一位女主角則是宋道熙(金賽綸飾),仍是國中學生,但衣服總是破爛,身體也經常渾身是傷。從校園霸凌被李英男介入起,到宋道熙所受到的家暴,展開電影的主要關懷:性、權力與善惡。
宋道熙的父親是朴容河(宋詩曦飾),而他的母親則是電影初始的那位婆婆,但父女之間並非親生,生母早就棄養了宋道熙,除了父親與奶奶長期的肢體與語言暴力對待之外,朴容河也是這漁村的經濟命脈,於是這樣的行為也似乎成為被睜眼閉眼、心照不宣地默許一般的持續。直到李英男如同啟蒙一般地告訴了宋道熙「大人打小孩是不對的」為止。
於是宋道熙學會了求救,當她受到暴力對待時,她跑到了李英男的門前敲著門,或許也正是因此讓英文的片名取為《A Girl at My Door》。她收留了她。她們一起用餐、購物,甚至洗澡,沒有親族關係卻反而相較於有者更加親密。甚至,連上門的是父親朴容河時,李英男也保護著宋道熙,讓她整個暑假都住在自家。
從開場的酒駕婆婆我們就可以發現鄉下與都市的差異不只是步調的快慢,甚至連法秩序共識都有所差別,就像長期酒醉施暴的朴容河只有多次收到李英男的警告,甚至以現行犯逮補也未解送檢調機關一般。但在故事進行中有位女子到此偏鄉尋找李英男我們才知道,她是同性戀,也是因此原因被調職至偏鄉,也因此她必須低調行事、不惹麻煩,以免讓自己甚至警界蒙羞。雖然《道》沒有透露更多,但縱使僅從側面以觀,韓國社會的性別天秤是傾斜的已非新聞,更不用說忤逆於傳統性別結合的同性戀,更是過於顛覆於傳統社會的價值秩序。
※你可能也想看:女性情慾的受制與流露:《屋簷下的她》(A Girl at My Door,2014)
然而,正巧的是敘舊感傷一吻的李英男與舊情人,正巧被朴容河載著外籍漁工給撞見,看似無異的招呼,實際則為抓到把柄給埋下伏筆。當故事發展至朴容河因多次暴行被警告無效,毆打著外籍漁工由李英男下令逮補後,朴容河的反擊即是指控李英男性騷擾未成年少女,於是一個所長頓時成為所囚。面臨到性犯罪調查的李英男,也在調查犯罪對於「事實」的詢問過程中,承認了她有碰觸宋道熙的身體,而宋道熙也在調查過程中由調查人員拿出的娃娃展示碰觸過程中指出了她被碰觸的身體部位。這裡的指示是模糊的,她所指出的位置是娃娃連身洋裝所遮蔽的部位,而李英男所陳述的碰觸是對一個長期受到暴力對待的未成年少女的關護,只不過因為她的同性戀身分所具有的性傾向,讓她百口莫辯。

故事的再度反轉在於宋道熙在所長李英男被逮補後,在父親再次喝酒施暴昏睡時,撥打電話給其他員警同時將自身的衣著褪去並解開朴容河的衣扣與褲檔並撫摸,朴容河的喝斥、喘息伴隨著宋道熙的哀嚎與佯作挨打,讓警員到場逮補了朴容河。後續的調查過程中,宋道熙翻供為前先所述是由父親所教唆,於是李英男才得以獲得「清白」,故事最後則在李英男即將調職離開鄉下時,臨時起意回頭找尋宋道熙後,在兩人的面部鏡頭特寫下由李英男說出:「妳願意跟我一起走嗎?」,伴隨著吉他和弦與人聲和諧配樂以及兩人的擁抱,李英男駕駛著,宋道熙安穩地睡著,故事結束於行駛在雨天道路的汽車畫面上。
這樣的結局有個當然的基調,也就是宋道熙終於有了可以歸屬的地方。但是,若配樂換成刺耳的小提琴聲呢?
宋道熙翻供的轉折是僵硬的,當然採取簡單的立場詮釋可以是她學會了生存,學會了自我保護,但礙於現行體制(包括法律以及社會)下,她以誣指、栽贓的方式讓父親朴容河受到拘捕。但這種虛偽指控所可能產生的另一種發展,已有 Mads Mikkelsen 所演出的《謊言的烙印》可見。尤其,宋道熙在說明遭李英男碰觸的身體部位時所具有的模糊性,也讓故事有了另一種被詮釋的可能:會否宋道熙真的受到李英男的性接觸?
固然我們無法就一個尚非成人的個體的行為判定其善、惡,因其未具一個「人」的基性—自由意志(的預設),然而宋道熙所指示娃娃所被碰觸的部位是無可否認地有其二人間具有其被性接觸的可能。當然這裡並非因為李英男的角色所具有的女同性戀身分即如此斷定,否則當屬預斷且具偏見,然而當我們將此身分再進一步拆解成「性傾向為生理女性的生理女性」時,我們可以再提問道:「性傾向為女性的成年人個體」與「未成年女性」共浴、前者碰觸後者的身體(縱使[假設]是基於關護的目的),是否合理、是否合法?進而,行為的合價值性又將否因為行為者的身分(例如生理性別)而「應」有異?特別是,雖然朴容河與宋道熙的父女關係是沒有血緣的,但二者於法律上仍具有親子關係的前提下,以我國的法律體制以觀,李英男的容留(即便是出於保護宋道熙的動機)也將有和誘罪的犯罪嫌疑。
這裡需要分成兩個情形討論,其一是若宋道熙確有被李英男性接觸,那麼她的翻供也將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式的行為表現,雖然這是與電影所想建立的印象有所差異,卻是不可被忽視的一個存疑;其二是李英男如其所述地並未有對未成年人宋道熙實施任何性接觸,那麼《道》的電影的具有的提問將是在於:當現行體制的極限仍無從張開一張足夠寬廣的保護網時,一個做出具有瑕疵(道德與法律上皆然)行為的人,是否應受非難苛責(例如誣控的宋道熙;容留未成年人的李英男)?就後者而言,類似這樣的道德質疑正是文初所提到的價值框架揭示—揭示價值框架。當我們慣於且無意識地進行評價時,我們是否該意識到我們是依循著什麼標準?又,此等標準是否有其限制?以及,這等標準讓我們看見什麼,又忽視了什麼?

我們該如何定性善人?如何定性善行?同理,惡人、惡行亦同。進而,是否存在著做出惡事的善人?又,是否存在著做出善事的惡人?說到底,善、惡又是什麼?我們都知道人無完人,但我們所具有的價值框架所設想出的善人、惡人就是一個理型的完人。《道熙啊》所留下的模糊空間及其所演示出角色所具有的道德瑕疵,都是在二元化的世界中讓我們看見二元化限制的線索。《謊言的烙印》即是一個適當的參照點,其中有著無辜者受誣陷的不正義的清晰描寫,因此我們所思考的會是在善惡的價值體系中如何避免善者受到非善(惡)的對待,或是反之。相對的,在《道》的故事中卻有著不無辜者受到制裁(朴容河)以及不無辜者不受到制裁(宋道熙,以及或許李英男)的模糊處理,雖或能讓人直觀地得到道德情感滿足,但若爬循著上述線索,我們將得以反問結果是否能正當化手段?「應得」該如何地達致?惡人受到(未必正當、合法)制裁的親痛仇快感,又或者非惡人未受到制裁(甚或從未視作問題),更是讓應得所源出的價值標準被顯現的瞬間。
當然,對於既有價值的挑戰將有造成價值真空的可能,但若不冒著價值這道德失序的風險,我們將永遠生活在一個因循苟且的傳統社會中。傳統並不等同於錯誤,但也不等同於正確,但可以確知的事情是,若我們停止思考此等道德疑難,我們將只是以為自己活在生命之流中的幻想,實際卻腳踏在一灘死水之中。
電影資訊
《道熙啊/屋簷下的她》(도희야 / A Girl at My Door)─丁朱里,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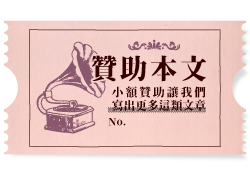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