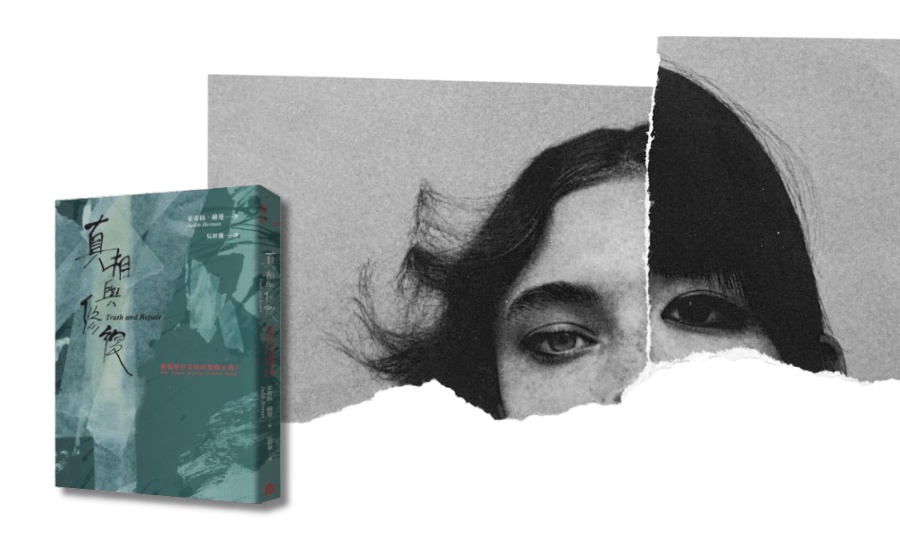
文|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譯|吳妍儀
原諒?
許多倖存者也同意他們希望「放下」加害者,還有他在她們心靈中代表的一切。某些倖存者描述了她們持續的怨恨感受還有她們的復仇幻想,幾乎就像是加害者的暴力留下的異物或有毒殘渣,而她們渴望擺脫這些東西。藝術家艾咪.萊佛德(Amy Bradford)是一位強暴倖存者,她描述了一個夢境:一隻恐龍來了,然後踐踏強暴她的人。在夢裡她樂不可支;醒來以後,她卻覺得這個夢很怪異。她人生中最不想要的就是更多的暴力。
有趣的是,她丈夫比爾.布萊佛德對於自己心存報仇的念頭這一點比她坦然得多。我常常發現真是這樣,對於自己的報復欲望,倖存者的親友比倖存者本人更直言不諱、更沒有心理衝突。在倖存者熟識她們的施虐者、還可以看到他們的某種人性的時候,尤其如此。比爾.布萊佛德說他真希望可以殺死那個強暴犯,他說這個強暴犯是「一股邪惡力量,不是人類」。但即使如此,當他被問起一個真正的道歉是否會有所差異的時候,他都有被撫慰的感覺。「我想,如果我可以把那個強暴犯安置到一個座位上,」他說,「我知道這種事絕對不會發生,但如果他願意承認這事情很糟,表達後悔,向她道歉,然後也向我道歉,我想那會有幫助。我厭倦憤怒了。天啊,我聽到自己這麼說還真驚訝!」
另一位強暴倖存者,莎拉.強森(Sarah Johnson),一位護理師,說她真希望她可以讓高中時在一場派對裡強暴她的男生,感受「世界上最糟的痛楚」。「我知道有人講到原諒,」她說,「但我還憤恨不平。我永遠無法原諒他。」然而一會兒以後,她補上一句:「如果他說:『莎拉,我很抱歉,我需要幫助。』我會說:『謝謝你,神啊!』然後我就不會這麼恨他了。」再一次,光是想到一個道歉,似乎就撫平了想報仇的感受。看來就算是在想像中,真正的道歉也帶有幾分魔法。
現在重新替自己取名為V的劇作家兼女性主義行動家伊芙.恩斯勒,在她的書《道歉》裡把這個魔法發展到極致。這是以她父親的聲音寫成的獨白,他在她小時候對她施加身體與性的虐待。她以自己身為劇作家的創造力量,召喚出已故父親的靈魂;他在生前從沒有向她道過歉。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她描述自己寫下那份道歉是一種解放的實踐,「轉化了我心目中的他。」作為一種方法,她列出在加害者(想像中的)內心必須發生的四個步驟:首先,對於是什麼讓他能夠犯下罪行,進行深度的內省;其次,完整詳細地承認他的作為;第三,發展同理心,感覺並理解他施加的傷害所造成的影響;最後,負起完全的責任,並且道歉。這些步驟明顯類似匿名戒酒會實踐的十二步驟計畫。第四步驟,「一份徹底而無所畏懼的道德清單」,導出後續對於所有受傷害者的承認、道歉與彌補。
在寫下這本書以後,V改了她的名字。雖然寫這本書很痛苦,但在書完成的時候,她覺得她從父親的掌握中釋放出來,而且不想再以父系姓名作為自己的身分認同了。她用「老頭子,消失吧」這句話結束這本書。憑藉她的想像之力,她設法跟能夠補贖、有可能與之和解的父親,創造出一種「我與汝」的對話。她做出結論:「在真誠的道歉被提出也被接受的時候,它創造出一種煉金術式的,在身體上、精神上與性靈上的解消,消除了對身體的侵犯、仇恨與怨懟,以及對於復仇與憎恨的需要。這實際上就是原諒的感受。」
然而,V也提出警告,就算加害者確實真誠又完整地道歉了,永遠不該期待或壓迫受害者原諒。我的報導人完全同意這一點。在她們感覺到原諒的社會壓力太強的時候,她們很容易覺得怨恨而抗拒原諒。
抗拒原諒
現代基督宗教的教誨頻繁勸誡受害者要透過原諒超越她們的憤怒,而不是採取行動對抗那些侵犯她們的人,而且人們總是特別建議女人跟其他從屬群體的成員要有原諒的美德;她們情有可原的怨恨可能會讓掌握權力的人感到不安。原諒的好處被宣揚為不只是為了受害者的靈魂,也是為了她的心智健全著想。私立基督教非營利機構坦伯頓基金會提出了一種新做法,建議記錄犯罪受害者接受所謂「原諒治療」後的效果。有個獲得贊助的研究,就描述了一個以亂倫倖存者為對象的每週治療計畫,原諒就是其明確且核心的訴求。這位作者基於非常有限的資料,主張和任何其他已知的治療相比,學習原諒對這群人產生了更正向的效果;普遍而言,創傷壓力領域內大多數的專家並不支持這個判斷。
倖存者有充分理由懷疑原諒施暴者這個觀念,尤其是在還沒有強烈信心認為對方真正改變態度時更是如此。在一篇題為「原諒的棘手問題」的布道文中,新教牧師同時也是家暴的倖存者安妮.瑪麗.杭特(Anne Marie Hunter),解釋了她為什麼質疑要原諒的宗教命令:「深刻的真理如下:原諒是很美妙而且很基督徒的事情。而有時候原諒是錯的。因為我們現在知道,施虐者通常會在事後表示懊悔。他們說他們很抱歉。他們說他們會改。他們說絕對不會再發生了。可是沒有國家認證的家暴者處遇計畫的幫助,事情就是會再度發生。」杭特牧師太清楚道歉與悔恨的表現了,就算當時看來很真摯,也可能是施虐者用來持續控制受害者,最有效的辦法。
杭特自己的倖存者使命,是致力於教育神職人員及宗教會眾家暴的現實狀況,並且改變讓教會跟施虐者站在同一陣線的父權教條與態度。她理解她的工作挑戰了基督教信仰過去一千七百年來確立的基本結構。「如果妳心目中有個評斷嚴苛、全能又全知的神,那聽起來很像個施暴者。相信神站在施暴者那邊的虔誠女性會說,『那就是我要背負的十字架』。宗教社群的偏見是強迫原諒。他們大喊『和平、和平』的時候,根本沒有和平存在。」
用不著說,杭特的觀點在現代基督教神學中是有爭議性的。耶穌不是勸誡祂的追隨者送上另一邊的臉頰嗎?作為回應,她引用了一位家暴倖存者告訴她的話:「我把一邊臉頰送上來,再把一邊臉頰也送上來,我現在整張臉都沒了。」照杭特看來,問題在於勸誡受害者原諒她的施虐者,總是比直接對抗施虐者、實際上制止暴力來得容易許多。「我還沒有聽到有人說『我設定界線是因為我是個基督徒』,」她說,「比起叫受害者原諒,我們需要思考的是讓加害者悔改並且改變行為。」
雖然這可能是少數觀點,但堅持真正的悔罪必須先於原諒的並不只有杭特。天主教神職人員中的顯赫成員,都柏林總主教與愛爾蘭首席主教也採取類似的立場。迪爾穆德.馬丁首席主教在表達他對天主教神父性虐待兒童這種遍及世界的禍害是如何痛心時,反省到在他的經驗中,加害者沒有真心悔過,對倖存者來說是「最大的侮辱」,而他補充道:「在加害者拒絕承認事實的全副意義時,很難談到對加害者做出有意義的原諒。」
這樣的立場與十二世紀學者摩西.麥蒙尼德斯的猶太教教誨是一致的:原諒必須透過實踐「teshuvah」(悔改)或懺悔掙得。根據現代宗教學者葉拉哈米爾.高立克的說法,「『teshuvah』的元素包括嚴格的自我檢視,並且要求加害者透過坦白供認、表示悔意,並且盡一切可能努力糾正他犯下的錯誤,來跟受害者互動。」高立克拉比補充說,沒有「teshuvah」的原諒,實際上對一個道德社群來說是毀滅性的。「因為雖然給予力爭得來的原諒,可能是能修復情緒、令人振奮又有啟發性的慈悲之舉,但給予不勞而獲的原諒並非仁慈,而是冷酷無情,而且可能只是進一步讓加害者與受害者對道德的區別變得麻木不仁。」
從這些宗教領袖的觀點來看,和解應該只有在達成正義以後才得以發生。而正義意味著社群已經介入來制止虐待,施虐者也承認他先前的作為,對他的行為負起完全責任,而且願意做任何必要之事來補過,藉此顯示他的悔悟。這些領袖挑戰我們這些旁觀者,要終止我們對父權暴力加害者的積極或消極共謀,並且擔負起嚴肅而繁重的任務:向他們問責。這不是倖存者可以獨自辦到的事情,也不該只是她們的責任。這項任務需要道德社群做出一種新的承諾。
書籍資訊
書名:《真相與修復:創傷倖存者如何想像正義?》 Truth and Repair: How Trauma Survivors Envision Justice
作者: 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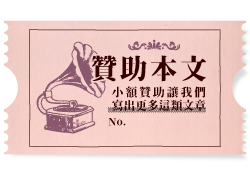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