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書中堅決把歐洲的兩個半邊整合進一個共同的故事。」
儘管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意圖上南轅北轍,那並未帶給它們的受害者什麼慰藉。

文|Tony Judt
譯|黃中憲
事後來看,最引人注目的,乃是這種刻意忽略的心態普見於各地。主動遺忘猶太大屠殺的,不只是那些有理由不去思考此事的地方──例如奧地利(人口只有戰前德國十分之一,卻供應了一半的集中營警衛人力)或波蘭──還包括義大利(大部分國民沒理由該為此事感到羞愧),以及英國(除了此事,英國人都用驕傲、乃至懷念的心情看待戰時歲月)。冷戰的迅速揭幕,當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還有其他理由。對許多歐洲人來說,要談二次大戰,重點不能擺在猶太人身上(除非要怪罪他們導致戰爭爆發),只要主張猶太人苦難可能是二次大戰史的最重要部分,就會深受痛恨。
猶太大屠殺只是人想忘掉的諸多事物之一而已:「在戰後蓬勃發展的年代……歐洲人藏身在集體失憶後面。」(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語)數百萬歐洲人曾與法西斯行政當局和占領軍妥協,曾與戰時占領家鄉的敵人機構、敵人統治者合作,有過私人的屈辱、物資生活的困頓和個人悲劇,面對如此不堪的過往,他們自有充分的理由予以忘記,或對己更有利的是,予以錯記。後來被法國歷史學家昂利.魯索(Henry Rousso)稱之為「維琪症候群」的現象絕非只見於法國。「維琪症候群」指的是長達數十年難以承認戰時真正發生的事,極力想堵住那段回憶,或以不致損害戰後社會之脆弱聯結、可資運用的方式重塑那段回憶。
在歐洲,每個曾被占領的國家,都發展出自己的「維琪症候群」。例如,義大利人戰時的貧困,包括在自家和在俘虜營裡的貧困,使公眾把注意力移離義大利人帶給他人的苦難──例如在巴爾幹半島或在義大利的非洲殖民地。荷蘭人或波蘭人向自己宣說的戰時事蹟,將支撐國家的自我形象長達數十年──特別是荷蘭人非常看重他們戰時反抗占領者的國家形象,同時又極盡所能遺忘有兩萬三千荷蘭人志願投身納粹武裝黨衛軍一事:那是來自西歐的最大一支武裝黨衛軍。就連挪威都有一段往事需要消化:一九四○年四月前或那之後,超過五分之一挪威軍官志願加入維德肯.吉斯林(Vidkun Quisling)的新納粹組織「國民聯盟」(Nasjonal Samling)。但儘管解放、反抗、遭遣送出境者──乃至敦刻爾克大撤退或一九四四華沙起義之類慘烈事蹟──都可以用於製造補償性的國家神話,猶太大屠殺一事卻毫無「可資運用」之處。
在某些方面,要德國人處理、承認他們罪行的重大,其實較容易。當然,一開始並不是如此:我們都已知道「去納粹化」是如何以失敗收場。在聯邦德國成立初期,歷史的教授止於威廉帝國。庫特.舒馬赫早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就勸告他的同胞,最好開始「破例談談德國和全世界的猶太人」,但這類政治家是罕見的特例,在四○、五○年代,除開他們,德國公眾人物都對希特勒的「最後解決辦法」隻字不提。美國作家艾佛烈.卡津(Alfred Kazin)評論此事道,對一九五二年他在科隆的學生來說,「這場戰爭結束了。這場戰爭不能提。我的學生對這場戰爭隻字未提。」西德人回顧過往時,回顧的是他們本身受過的苦:五○年代底的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人把戰後盟軍的占領視為「自己一生最慘的時期」。
誠如某些觀察家在一九四六年就預料到的,德國人成功與希特勒劃清界線:把希特勒當代罪羔羊獻給世人,藉此避開自己應受的懲罰和道德責任。對於希特勒所帶來的惡果,德國人的確相當痛恨──但那是因為他傷害了德國人,而非因為他和德國人傷害了其他人。這些年裡許多德國人覺得,希特勒鎖定猶太人迫害,與其說是他最大的罪行,不如說是他最大的錯誤:在一九五二年的某項民調中,將近四成西德人並不介意告訴民調訪問人員,他們認為國內沒有猶太人對德國「比較好」。
附近沒有可令人想起納粹暴行的事物,使這類心態更為盛行;納粹特意將他們主要的死亡集中營設在遠離「舊德意志帝國」之處。但就算鄰近可令人想起納粹暴行的事物,不代表就比較能體會猶太人的苦難。達豪是慕尼黑的郊區城鎮,從市中心搭有軌電車就可抵達,但當地人並未因此就較能理解當地所曾發生的事:一九四八年一月,巴伐利亞議會一致表決通過,將當地納粹集中營的所在地改闢為「不願工作、不與人往來者」的強制勞動營(Arbeitslager)。誠如漢娜.鄂蘭於一九五○年走訪德國時所觀察到的:「不管在哪個地方,都可注意到當地人對曾經發生過的事毫無反應,但這究竟是因為刻意不願為過往悲痛的心態,還是感情真的麻木的外在表現,很難說得準。」一九五五年,法蘭克福法院宣告曾提供齊克隆B(Zyklon-B)毒氣給納粹黨衛軍的某公司總經理佩特斯博士無罪,理由是「證據不足」,無法證明那東西曾被用來毒死集中營裡的人。
但在這同時,德國人──歐洲境內只有德國人──無法否認他們對猶太人做過的事。他們可以避而不談,可以堅稱自己受苦,可以把責任歸在「一小撮」納粹黨員身上,但無法藉由將種族滅絕的罪行扣在別人身上,來卸除自己的責任。就連艾德諾,雖然在公開場合只表示同情猶太「受害者」的遭遇,從未指名道姓說出加害他們的人,也不得不與以色列簽訂賠償條約。此外,不管是英國人、法國人、乃至普利摩.李維的義大利同胞,都對列維的自傳興趣缺缺,但《安娜.法蘭克日記》(的確是較淺顯易懂的一份文獻),卻成為德國史上最暢銷的平裝書,一九六○年時銷售量已超過七十萬冊。
德國人開始捫心自問的原因,乃是對東線戰場上的德國人罪行展開遲來的調查所促成的一連串審判。這些審判始於一九五八年在烏爾姆(Ulm)一地對戰後「干預團體」成員的訴訟,繼之以對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逮捕和起訴,而其高潮則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八月間法蘭克福一地對奧許維茨集中營警衛的審判。這些審判也讓集中營倖存者自戰爭結束以來,首度有機會公開談論自己的遭遇。在這同時,聯邦德國延長了殺人罪的二十年追訴時效(儘管尚未將追訴期廢除)。
這一心態上的轉變,主要是兩個因素所促成,即五○年代底出現的一波蓄意破壞他人財產的反猶作為,以及愈來愈多跡象顯示,德國年輕人對第三帝國完全無知:他們的父母完全未告知他們第三帝國的事,他們的老師則避談此事。從一九六二年開始,西德十個州宣布,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這段歷史──包括滅絕猶太人──將成為所有學校的必修課。於是反轉了艾德諾在戰後最初的假定:從此,德國民主要健全,就得記住納粹主義,而非予以遺忘。於是,愈來愈受關注的,乃是種族滅絕和「違反人道罪」,而非在此之前一直被認為與國家社會主義關係最密切的「戰爭罪」。從此要讓新的一代了解納粹暴行的本質──和嚴重程度。《明星雜誌》(Stern)、《快報》(Quick)之類通俗雜誌將不能再歌頌「好」的納粹分子,也不能再像五○年代那樣淡化集中營的歷史意義。公眾已開始認識到德國晚近歷史有令人無法接受之處,有不光彩之處。
但不該誇大這一改變。六○年代,西德總理基辛格和聯邦總統漢斯.呂布克(Hans Lübke)都曾是納粹黨員──誠如年輕一輩評論家所貼切指出的,這是聯邦德國的自我形象裡明顯的矛盾之處(見本書第十二章)。而且,道出納粹的真相是一回事,承認德國人民的集體責任又是另一回事;這時大部分政治人物對於集體責任仍然不表示意見。此外,認為「要不是有這場戰爭」希特勒會名列德國最偉大政治家之林的西德人比例,雖從一九五五年的四成八降為一九六七年的三成二,後一數據(儘管絕大部分是老一輩受訪者)仍令人無法放心。
真正的轉變出現在下一個十年。一連串事件紛至沓來──一九六七年以阿的六日戰爭、一九七○年西德布蘭德總理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受害者紀念碑前跪下、一九七二年以色列運動員於慕尼黑奧運選手村遭殺害、一九七九年一月德國電視播映《猶太大屠殺》迷你劇集──使猶太人和猶太人的苦難成為最熱門的德國公共議題。其中,那部迷你劇集最為重要。它是最道地的美國商業電視產品──情節簡單、角色刻畫大部分缺少深度、敘事內容極盡煽情之能事──(誠如第十四章裡指出的)受到從埃德加.雷茨到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等歐洲電影導演的痛斥和厭惡。他們指責這部劇集把德國史轉化為美國肥皂劇,使得應該始終是不可說、無法理解的東西,變得淺顯易懂。
但這些侷限本身正說明了這部劇集為何衝擊如此大。它在西德全國性電視台連續播放四晚,收視者據估計達兩千萬,大大超過成年人口的一半。它播放時,馬伊達內克(Majdanek)死亡集中營的前警衛也正好在受審──提醒收視者這件事還沒了結。這對公眾的衝擊非常大。五個月後,聯邦議會表決通過廢除殺人罪的追訴時效(但在此應該指出,投票反對此議者,包括後來出任總理的柯爾)。自此之後,德國人將是對猶太大屠殺了解最深入的歐洲人之一,且帶頭使每一代民眾認識該國的滔天大罪。一九六八年時,只有四百七十一個學校團體參觀達豪,到了七○年代底,一年參觀的團數已超過五千甚多。
了解──且公開承認──四十年前德國人對猶太人所做的事,乃是很大的進步;但誠如八○年代「歷史學家的衝突」所會彰顯的,要把那段過往放在德國史、歐洲史裡,仍是棘手且未解決的難題。有些保守學者,包括在這之前一直很受敬重的歷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對於「希特勒、他的組織、他的罪行是獨一無二、獨具一格的」這種主張,感到不安。他們主張,如果要了解納粹主義,就得把它擺在當時的時空去了解。據諾爾特的說法,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和它某些古怪的作為,主要是在回應布爾什維克主義:它們出現於列寧與其接班人所提出的榜樣和威脅之後,在某種程度上仿效那榜樣和威脅。在一九八六年六月《法蘭克福匯報》上某篇臭名遠播的文章裡,諾爾特主張,納粹主義的罪並不因此而減輕;但沒有布爾什維克的先例,就無法完整解釋納粹的罪行。於是,眼下該重新思考納粹時代,把「猶太大屠殺」擺在更廣闊的現代種族滅絕模式裡去思索。
諾爾特所激起的回應,主要來自于爾根.哈伯馬斯。哈伯馬斯,一如恩岑斯貝格、鈞特.葛拉斯和「懷疑一代」的其他成員,年歲夠大,對納粹主義存有記憶,因而對於欲「限制」德國人責任的任何作為,都抱有強烈懷疑。「胡說八道,」哈伯馬斯如此回應諾爾特:探討納粹主義時,重點不在將它「擺在」什麼時空或將它「歷史化」──像這樣的誘惑,所有德國人都沒有權利再度沉迷其中。納粹罪行──德國罪行──獨一無二:獨一無二在其規模,獨一無二在其野心,獨一無二在其尚未被完全探明的邪惡。照諾爾特所主張的那樣,依據當時的時空背景來理解納粹,必然隨之將德國人的責任暗地相對化──這種背景主義(contextualization)式的理解,一定要完全禁止。

但對哈伯馬斯的大部分同胞來說(包括以比較和時空背景為治史首要要求的歷史學家),他的不妥協立場太苛求,只有他少數人能夠長期堅守。德國人對「猶太大屠殺」一事的公開討論,在九○年代時達到最高峰,當時官方大動作表達他們後悔過去所犯的錯誤,德國人沉浸在作家彼得.施奈德所謂的「某種自以為是的自我仇恨」中──但「猶太大屠殺」蔚為顯學的新現象不可能永遠不墜。要每個新一代德國人永遠活在希特勒的陰影裡,要他們為德國過去獨一無二的罪過承擔責任,使那罪過成為他們國家認同的基準,這實在是最基本的要求──卻也是最不合現實的奢望。
在西歐其他地方,緬懷、承認的進行,首先得打破當地為自利而抱持的錯覺──而這一打破過程通常花上兩個世代、數十年。在奧地利,《猶太大屠殺》一劇的播映只晚了德國兩個月,但產生的衝擊和在德國完全不能比。直到八○年代中期,有人披露奧地利總統庫特.華德翰(Kurt Waldheim)曾為納粹德國國防軍殘酷占領南斯拉夫出過力,(一部分)奧地利人才開始嚴正質問自己國家與納粹相關的過往,但仍不完整。事實上,華德翰先前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時,國際社會無人特別拿他的戰時經歷作文章,此一事實使許多奧地利人更加懷疑,他們是否受到特別的苛求。畢竟戰後奧地利已出過一位猶太裔總理──社會黨的布魯諾.克雷斯基(Bruno Kreisky)──比德國好得多。
但沒有人對奧地利人寄予厚望。他們大抵上看不出有必要為其晚近歷史而困擾,晚至一九九○年仍有將近四成的奧地利人認為自己國家是希特勒的受害者而非其共犯,仍有四成三奧地利人認為納粹主義「好壞兼具」,而這現象只證實了他們自己和他人的偏見。在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鄰國瑞士,情況又不一樣。一九四五年後,有四十年時間,瑞士的戰時前科絲毫未受到追究。眾人不只遺忘了瑞士人曾極力不讓猶太人入境;相反地,在通俗小說和各地的電影裡,瑞士還被描寫為安全避難所,凡是能來到它邊界的受迫害者,都受到它的歡迎。瑞士人自認心安理得,受到舉世欣羨。
事實上,到一九四五年為止,瑞士人只接納了兩萬八千名猶太人,其中有七千人是戰前得到接納。戰時難民拿不到工作許可證,靠當局向有錢猶太裔居民強徵來的捐款過活。直到一九九四年六月,伯恩當局才正式承認,瑞士於一九三八年十月要求德國在所有德國猶太人護照上蓋上字母J的舉動──不讓猶太人進來的辦法──乃是「無法容忍的種族歧視」行徑。如果瑞士犯錯的程度只是如此,那當然就不必太苛責於他們,畢竟英國、美國雖從未要求在猶太人護照上標記其族裔身分,但說到拯救猶太難民,這兩國也沒什麼好自傲於人。但瑞士人的惡行遠不只是如此而已。
(本文為《戰後歐洲六十年》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戰後歐洲六十年(上下冊套書)》〔新版〕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作者:東尼.賈德(Tony Judt)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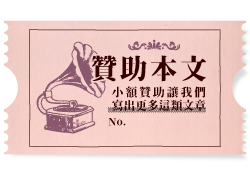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