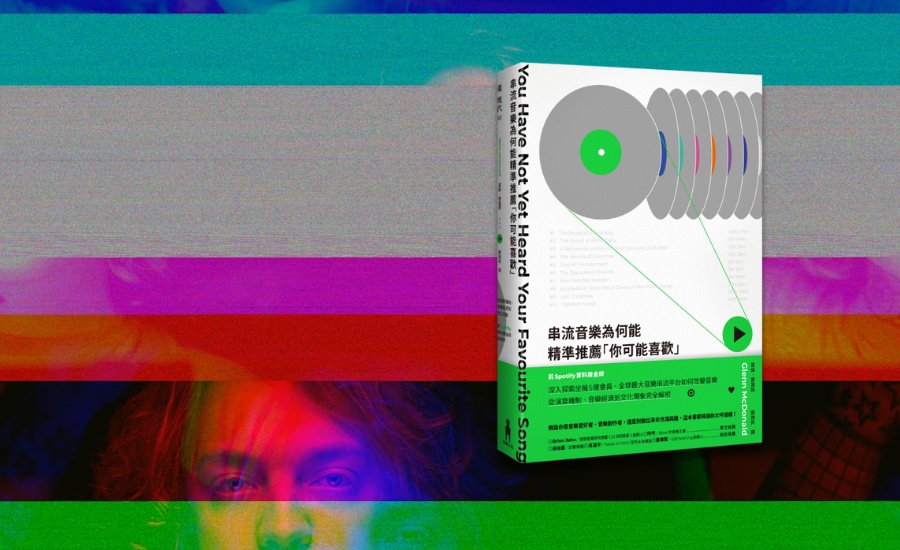
文|葛倫.麥當諾(Glenn McDonald)
譯|鄭煥昇
串流,就是監控資本主義。
至少,絕對是資本主義。至於要不要加上「監控」的前綴,要看你覺不覺得串流在其運作所需的資訊交換以外,還做了更過分的事情。
你按下歌曲的播放鈕,跑在你手機或電腦上的應用程式就會發出訊息給串流服務伺服器。這則訊息會找到你打算播放的歌曲,因為那正是重點所在,然後就是你串流帳號的使用者ID,因為串流服務需要以此判斷你有沒有權限播放那首歌。你按下暫停或跳過或換到另外一首歌時,應用程式會發出另外的訊息給伺服器。這些訊息本身並沒有在監控什麼,就像燈泡也沒有在監控將它打開或關掉的牆壁開關。
然而燈泡並不會記錄下自身的開或關——除非是所謂的智慧燈泡——但串流服務會記錄你的操作行為。他們不得不如此,不論在內部運作上或法務層面上都是,因為他們必須支付權利金給音樂的授權方,而這些權利金的計算會牽涉到歌曲、帳號、日期與時間。但即便在不牽涉到權利金的時候,各種合理執行的線上服務都會記錄其日常運作,如此一來我們才能監測線上服務是否正常運作、正常並診斷問題。任何一個你使用的線上應用程式或任何你造訪的網站,都幾乎必然會以某種方式記錄你在點擊時做了什麼事。
這些記錄包括了一些涉及你與你行為的額外資訊,且其中大部分都關乎軟體本身:你用的是哪個版本的應用程式,你是在什麼樣的裝置上使用這個程式,你是在程式裡的什麼地方要求播放這首歌,你最後一首歌播了多久,你特地用滑鼠或手指點擊了什麼去切換歌曲。大部分的這些記錄,都還是為了維持應用程式運作正常的基本所需,或是不搞錯你現在在什麼頁面上,諸如此類的。至於其餘的記錄則是為了對特定功能的行為表現與效能進行歷時監控。
串流服務也會知道你是從哪個IP位址的電腦發出應用程式的訊息,因為網路就是這麼運作的。IP位址能讓我們知道電腦位於網際網路上的什麼地方,就像現實中的街道地址與公寓門牌可以對應到實際的地點。網路上的IP位址是登記在案的,且大部分都至少在名義上關係到物理性網路硬體在現實中所處的特定位置。
看著自己在Spotify上的活動記錄,我可以看出當我在筆電上播放音樂時,我的播歌請求來自於登記在麻省劍橋的一處IP位址,而那也正是我居住的小窩。要是我把裝置轉換為就擱在筆電旁且連結同一個WiFi的手機,那IP位址仍舊會是同一個,物理上的位置也不會改變。但要是我關掉手機的WiFi而不移動手機位置,那5G手機提出的要求就會被記錄為來自我電信公司基地台的登記地址,位置在紐約。如果這算是監控,那我只能說其精準度也低得太搞笑。
你初次註冊Spotify帳號,表格會問你至少四個關於你個人的問題。第一個是你身在哪個國家,這個問題通常是系統自動判定的,因為音樂授權會因國家而異。第二個問題是你的電子郵件地址,因為顯然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現在的孩子對電子郵件的態度,就像我們當年容忍傳真機一樣。第三個問題是你的生日,這是為了遵循與年齡有關的法規,也是為了判斷你能不能聽懂跟傳真機有關的笑話。第四個問題是你的性別。性別問題的選項會出於各國社會背景與法律規定的不同而在各地區有些許差異,但在大部分狀況下,給你的選項組合會是「男性、女性、非二元性別」。現階段你必須三選一才能繼續註冊下去,但這其實不算合理,因為音樂的世界不分性別。
當然,話又說回來,音樂始終來自人性,人性往往少不了性別,而世上大部分地區的整體音樂品味都會隨著年齡與性別而有所差異,且幅度幾乎不輸國籍與語言所代表的差別。由此性別登記從串流業者的角度來看,就成了實務上的一種統計優勢,因為你可以藉此把同國家、同年齡、同性別的舊使用者他們已經喜歡的音樂,推薦給什麼都還沒有播放過、宛若一張白紙的新使用者。
我在理論上反對這種做法,也很希望能在實務上反對這種做法,因為我個人的音樂品味絕不限於我這個族群的人。但屬於我們這群人的獨特品味,確實是形成在上世紀八〇年代的美國調頻電台上,那是一群青春的少年聽眾,而我正是當中的一員。所以沒錯,只要加拿大搖滾樂團凱旋合唱團(Triumph)的〈魔力〉(Magic Power)歌聲一響起,我就會一秒回到十五歲,彷彿當年那台Panasonic RX-5150手提音響又出現在我身旁了,我只要手一伸就可以摸到上頭那個可以調整「音場」的開關。沒錯,加拿大前衛搖滾樂團匆促(Rush)的〈住宅區〉(Subdivisions)能讓我聽著旋律就回到我成長的郊區,心中像是得到了某種滿足。
更進一步說,所有跟我同年、聽同一個廣播長大但卻在串流註冊表上點選「女性」的美國人的集體串流品味,都能瞬間讓我想起當時最典型讓我不喜歡的流行音樂:肯尼・羅根斯(Kenny Loggins)、卡莉・賽門(Carly Simon)、巴瑞・曼尼洛(Barry Manilow)、夫妻檔組合艾希弗與辛普森(Ashford & Simpson)與狄翁・華威克(Dionne Warwick)。而也許最能說明情況的事實是:在我所屬的國家、年齡群體中一首少數男女通吃的單曲,是柏林合唱團(Berlin)那首影響深遠的合成器搖滾申辯之作——〈別再說了〉(No More Words),而我還記得那天我爸媽看到我從唱片行帶回家的不是又一張外國人合唱團(Foreigner)的專輯,而是柏林合唱團的黑膠時,他們的反應從困惑漸漸轉為擔憂。他們也不真的喜歡外國人合唱團的〈一身熱血〉(Hotblooded)或〈冷冽如冰〉(Cold As Ice),但至少他們聽得懂歌曲傳達的溫度,同時到外國人合唱團為止,他們也還看得懂我的點唱機英雄大概是什麼模樣。但柏林合唱團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存在,一種不僅我爸媽看不懂,而是連我也看不懂的存在,但讓我看不懂也正是他們對我的魅力所在。
你在聆聽的過程中,就會一邊對這些低級的人口分布推論產生強化或駁斥的效果,而隨著時間過去,你便能確立自己的聆聽模式。資料的量會穩定變化,但不太會改變的是資料的形狀。Spotify永遠不會知道你的族裔出身、你的政治立場、你職業取向、你的收入多寡、你的購物習慣,或是你的用藥清單。它不會知道你都跟Apple手機的人工智慧助理Siri說了什麼,不會知道你在網路醫生網站(WebMD)查了什麼,不會去交叉檢索你的Netix上有哪些待看清單或你在YouTube上訂閱了哪些頻道。它看不見你穿著某個樂團的周邊T恤,它無從得知你身上那件樂團T恤是三十五年前購買的,它更不會知道左邊那個戴著帽子的樂團成員昨天剛去世,而悲傷的你現在需要聽的是哪一首歌曲。
太多蛛絲馬跡會決定你下一首想聽的會是什麼歌曲,但只要你不在Spotify上面聽,Spotify就不會知道。我通常不太會被推薦我一九八二年喜歡過的歌曲,因為光是聽現下美國青少年在Discord(註1)上的合成故障饒舌(註2),或是聽舞步整齊劃一的日本偶像團體在金屬核(註3)樂團的伴奏下熱唱,我就已經忙不完了。也因此我比較常被推這些新歌。我們的品味幾乎可以被無止盡地迴響。
但到了今天,我還是不會被推薦任何一種有望再次改變我品味的音樂,就像泰莉・努恩(Terri Nunn)的呢喃吟唱曾經在我還是個美國少年時讓我喜歡上那樣。阿瑪鋼琴(註4)呢?來自挪威的美式音樂呢?這些跨越音樂時空的蟲洞我必須自己去找出來。有些時候你會踏出對自己的既定認知、變成有點新的一個人,但這種時刻少之又少,少到難以為其最佳化。更輕鬆而可靠的做法,是繼續餵食你已然熟悉的東西。
註:
① 一個社群間的免費即時通訊軟體暨遊戲數位發行平台,並於二〇一九年停止了遊戲數位發行。
② Glitch Rap,一種結合了饒舌(Rap)和電子音樂中的「故障」元素的音樂風格,其中故障是一種電子音樂風格,特點是利用音樂製作中的錯誤和故障(如雜訊、音頻切割、數位或類比錯誤等)來創造獨特的節奏和聲音效果。
③ Metalcore,金屬系音樂的一個分支。
④ Amapiano,二〇一〇年代中期在南非出現的浩室音樂支派,為浩室音樂、爵士樂和休閒音樂的混合體,鋼琴是這種音樂風格裡的重要元素,且通常是現場演奏,所以當中帶有許多即興創作和實驗的色彩。
書籍資訊
書名:《串流音樂為何能精準推薦「你可能喜歡」:從演算機制、音樂經濟到文化現象,前Spotify資料鍊金師全剖析》 You Have Not Yet Heard Your Favourite Song: How Streaming Changes Music
作者:葛倫.麥當諾(Glenn McDonald)
出版:木馬文化
日期: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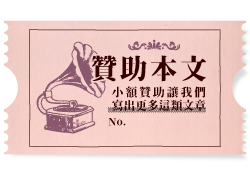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