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一個自由派代表導演,過去阿莫多瓦以其誇張獵奇的情慾故事來體現其中的現實殘缺與人性光輝,但自從《切膚慾謀》與《沉默的茱麗葉》後,可以逐漸看到他的收斂。特別是在《痛苦與榮耀》自傳式劇情片裡,我們突然意識到這個男人確實已是成熟老者而非派對小伙。當他先後擔任西班牙獨裁屠殺紀錄片《沉默正義》監製,然後再自己拍出同樣與尋找親人遺骸有關的作品《平行母親》時,他的社會關懷已經走到無法不直接提及現實政治的地步。
《隔壁的房間》更是如此,雖然是改編自他人作品,但完全可以感覺到片中角色所思所想,是上世紀自由派關心與擔憂的事情,正如他們自由的情慾生活方式也屬於上個世紀那樣。
與此同時,儘管死亡元素並非第一次出現在阿莫多瓦的作品裡,至少在《我的母親》裡死亡就是推動角色的關鍵元素,但《隔壁的房間》中,死亡卻是核心議題。不只因為故事主線是罹患癌症的戰地記者找一個不是她最熟的朋友陪伴她安樂死的過程,同時也因為片中的角色一邊回憶上世紀挑燈夜戰於新聞還有享樂的黃金年代,一邊覺得對於現實無能為力的感慨。那是蒂妲·絲雲頓扮演的與女兒不睦的瑪莎,也是茱莉安·摩爾扮演的恐懼死亡的英格麗,當然也是與她們兩個都曾有過一段情的約激進環保與人類自願絕育倡議者達米安,由翰·特托羅飾演。
他們的無能為力體現了一個殘酷事實: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老自由派不死,只是難以起舞。

就像瑪莎為了救人衝入其實沒有人的起火房子的明顯意象一樣,名畫《克里斯蒂娜的世界》(Christina's World)展現出了一種渴望與無能,彷彿上世紀那些認為自己對於越戰或者美國在外面哪個地方打戰而有所愧疚的左派份子,深度的自我厭惡最終導致無可挽回的自毀。
用簡單的鏡頭讓演員盡情對話到場景與時間變換也不在乎,是本片一個「形式即內容」的特色。正如茱莉安·摩爾與蒂妲·絲雲頓的同框對話是本片的招牌看點,當使用文字的人對文字的作用產生疑惑,語言的交流就成了最後一條救命索,所以片中作為關鍵機關的門才會是以視覺阻斷的方式來呈現。
「如果門關上,代表我走了。」
瑪莎告訴英格麗,她不是她的首選,這是片中的重要設計,因為真正與瑪莎最親密的友人甚至女兒都不願意陪她安樂死。
如果那個人對你這麼重要,你要怎麼想像一種可能性:她前一晚還在跟你於火爐旁看基頓的電影,然後隔天突然掛掉?
一道門,阻絕了視覺,卻阻絕不了聲音,那些聲音是亡者的耳語,哪怕他們走後都依然難以斷絕。

寫作,就是把腦子裡的聲音化為文字,你不能做它的主宰,你只能服侍它,直到它不斷召喚你,正如人試圖用安樂死來戰勝癌症一樣徒勞,或許也與人從事環保行為試圖拯救地球然後來拯救自己一樣。
「如果我先殺死自己,癌症就無法殺死我。」瑪莎如是說。
不過千萬別誤會,《隔壁的房間》真的不是一部嚴肅沈重的電影。確實,它有點憂鬱,但也充滿笑語還有希望,這是阿莫多瓦的態度或許也是他想傳遞的資訊,當片中一直遲遲未未現身、與瑪莎疏遠的女兒出現時,我們看到的仍舊是蒂妲·絲雲頓的臉。這是完美的孤雌生殖,就像片中瑪莎獨自撫養女兒卻又與其極度疏離一樣,同樣的臉可以寄宿不同的靈魂,同樣的靈魂亦可能長成不同的臉。

老自由派已經拿那些掌握權力的粗魯警察沒辦法了,他們無法再去推擠,衝撞,或者在他們的槍口上放花,他們公領域參與的時代已經結束,與當代年輕自由派的主張有所隔閡,無論是倡議還是手段,他們花更多時間回顧自身,並思考該如何面對自身世界的凋零,那不只是他們的身體,也是他們的心智。
但他們仍然留下了些什麼,哪怕他們絕望的認為,自己對後代有所歉疚,正如瑪莎的女兒與她有張同樣的臉一樣,她不是少女,而恰恰是一個看起來也事業有成的壯年人。
《隔壁的房間》如同阿莫多瓦的其他晚期作品一樣,是老自由派的末日與反思,而這與一些碎嘴老人不同的是,自由派雖老去但文化素養仍高,也確實燃燒過什麼,讓一切結束得如此優雅與悅耳。
電影資訊
《隔壁的房間》(La habitación de al lado)─Pedro Almodóvar,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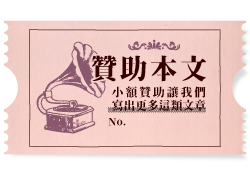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