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布魯斯・芬克(Bruce Fink)
譯|郭貞伶
佛洛伊德以有人公開羞辱我們時發生的狀況為例來說明。遇到被人羞辱時,有人會立刻加以駁斥,並還以顏色;有人會毆打或賞對方一個巴掌;有人則是什麼也不說,事後卻一再反芻那些難聽的話,忖度對方罵的是否有理,在想想自己的優點之後,很可能會難過、生氣或淚流滿面地確定那人是錯的。在所有這些狀況裡,事件會在當下引發一定程度的身體應對(例如,賞人耳光)、或是產生隨後的內心活動,這些都會讓事件所引發的憤怒或羞辱感立即或逐漸地消退(這意味著「激動狀態」的消退或「釋放」)。
我們並不會忘記這件事,不過在我們立即做出反應的狀況裡,它即使有影響也不會持續太久。如果是事後一再反芻,我們會把這件蒙羞的事和生命裡其他較為正向的事件擺在一起,把它當成我們尚稱平順的日子裡一件不足掛齒的倒霉事,(在大多數情況下)情緒緩和下來是遲早的事。佛洛伊德對此的說法是,「透過聯想(association)的過程,伴隨事件而來的情感消失了」── 聯想,在這裡意指「某個記憶與其他許多記憶產生連結」。
然而,有些人會認為這樣的公然受辱令他們顏面盡失而窘迫不已。在受人侮辱時,他們措手不及,無法做出回應,並因此深受打擊或是感到受傷,甚至拒絕再次回想對方說了些什麼。他們似乎相信,最好假裝一切都沒發生過。我們或許會感到詫異,不過就是被人羞辱一番,不管那些話多麼粗俗、有辱斯文或惡劣喧囂,為何這些人會因此大受打擊或是感到受傷?假如對方的侮辱不是直指,而是以某種方式暗指他們心知肚明而且希望隱瞞的事,他們顯然會更丟臉、更加無地自容。那些話若是根本子虛烏有,或許不會讓人耿耿於懷。說不定就像法國人說的,Il n’y a que la vérité qui blesse── 這句話字面上的意思是「唯有真相令人痛苦」,而其寓意為「最傷人的莫過於真相」。
佛洛伊德自己至少在兩處說過類似的話:「我們都知道,指責本身要有點料才能『一戳中的』;唯有這些才能夠激怒我們」,以及「沒打中要害的指責,不會讓人總想著要辯駁」。然而,正中(或差一點打中)要害的指責、侮辱、指控、輕蔑,是可能造成創傷的;也就是說,它有可能會讓一個人努力想忘掉這件事曾經發生。
我有一位分析者多年來欺瞞妻子,與很多位女性有婚外情,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他偶而會指謫他的老婆亂搞男女關係。某一天,當他的老婆終於指控他對她不忠,他竟勃然大怒,無法自抑,他一直認為自己小心翼翼地隱瞞外遇,不可能會有人疑心他偷吃。他甚至試圖忘了整件事情,也讓他的老婆一起忘了這檔事,即便如此,他還是感到心煩意亂,氣了好幾個星期。
然而,即使我們想把真相拋諸腦後,真相也不會放過我們。無論我們多麼努力想遺忘一件事,想把它隔離開來,想跟它切得一乾二凈,它還是存在著,而且似乎想找到出口,想找到機會現身。它持續吞噬著我們,彷彿正在潰爛化膿,或是像癌症般生長及轉移,要求我們付出越來越多的能量,才能讓它保持不見天日。簡言之,它變成了「病原的」(pathogenic)── 也就是說,它會產生某些病態的東西。正如佛洛伊德所說,「受到抑制的意念,它的報復方式,就是成為病原意念」;也就是說,它對我們展開報復,是因為我們對它的抑制。
如果我的情緒爆發至少有部分是抑制所致,則這類情緒爆發最有可能會被周遭的人視為「不理性」,因為它看來與當下的情況不成比例 ── 例如,多年來我抑制了對某位家人生氣的念頭,終於有一件小事觸怒了我,我的怒氣遂如火山爆發,一發不可收拾。我越是想克制自己對那個人的報復、批評或懲罰 ── 也就是說,我越是想放棄自己去做某事的慾望,越是無視或背棄自己的意願 ── 我的感覺就越糟,愧疚感就越強烈,內在的憤怒情緒就累積越多,最後情緒爆發時就可能變得更極端。「在這類情況中,情感的質是合理的,但是在量上卻非如此。……這種過量,來自於那些先前仍處於無意識而且受到壓抑的情感」。
難以觸及的被抑制念頭及願望
無意識不能進入意識。
── SE V, p. 615(強調為原文)
為了凸顯日常清醒時的思慮有多麼難以觸及被隔離/被抑制的記憶,請容我暫時用電腦領域偶而會發生的事情來加以比喻。儘管這種比喻在諸多方面都不夠精確,卻有助於讀者理解佛洛伊德所說的隔離(isolation)或斷開連結(dissociation)的意思。
當下存在於電腦隨機存取記憶體(RAM)的資料 ── 簡單來說,就是眼前在螢幕上所看到的內容 ── 好比是人類在當下所意識到的內容;且讓我們稱呼它為M4。如果我們現在正想著、或正談到M4,那麼M4就是我們可以觸及的。我們雖然沒有想著、或沒有談到M5或M6,但只要它們在我們的心中與M4有連結,那麼我們很容易就能想到或談到它們。與其說M5或M6是我們有意識的,不如讓我們先使用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所發展出來的概念,把它們稱為是「前意識的」(preconscious)。在電腦的世界裡,我們可以透過點擊,將M5、M6與其他可以開啟和讀取的檔案連結起來。雖說它們現在並不存在電腦的RAM中,但只要點擊兩下滑鼠就能讓它們出現。
有使用過一陣子電腦的人都知道,有些硬碟檔案儘管還在,卻無法開啟或無法有效讀取;就像無意識的材料,我們試圖清除的電腦檔案很少真的被刪除掉。近幾年來,檔案變得可以上鎖,這類檔案只能被製作檔案的人打開(假設他或她記得正確的密碼!),或是可以加密,這麼一來就只有擁有鑰匙的人才能讀取檔案。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最令人受不了的是不斷更新版本的文書處理軟體,例如Microsoft Word,它就無法開啟早期操作系統建立的舊文件檔案。Mac使用者經常收到一個令人抓狂的訊息是,他的舊文件「使用的檔案類型在此版本已經無法開啟」。過去這些年來,蘋果電腦往往會用以下這則訊息嚇唬那些粗心大意的使用者:「檔案無法開啟,建立這個檔案的應用程式已經不存在。」
已經成為無意識的記憶、念頭及願望,就像這些檔案:我們可以說,建立這些檔案的應用程式已經不存在。然而更好的說法或許是,能夠找到、開啟並讀取這些檔案的應用程式,還有待被設計出來。精神分析實務所涉及的就是創造出一整個系列的應用程式,可以用來搜尋、開啟及讀取無意識的內容,這些內容是一個名為「抑制」的單向應用程式的產物。「抑制」的設計是用來使事物消失,而不是讓事物再度出現,從而抵銷它自身的效果。
精神分析師必須從事的,是一個約略等同於「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的過程:將一項產品拆開,看看它一開始是如何被組合起來,使其可以如今日這般運作。分析師這麼做不是為了學習如何引發抑制,而是要逆轉被稱為抑制的應用程式所造成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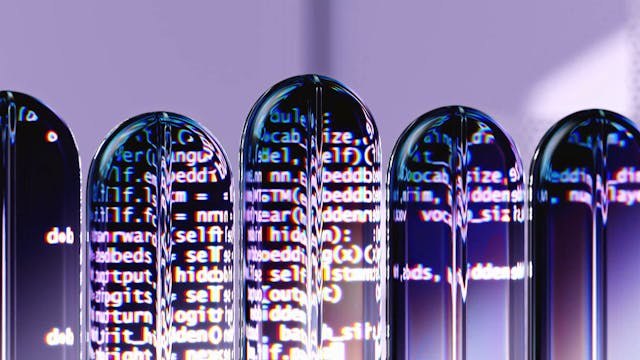
讓我們想像一下,在我的生命中,有個發生在親戚家浴室裡的創傷事件。為了有效地忘記這件事 ── 也就是說,為了確保我再也不會有意識地想起這件事 ── 我必須也遺忘發生在那間浴室、甚至那間屋子裡那個區域的每一件事。如果我還記得那一天發生的其他事情,我可能會發現我也必須讓這些記憶退出意識之外,還有涉及創傷事件的那個人或相關人等,一整串記憶都必須移除。
創傷越是重大,能夠透過聯想鏈(chain of associations)或是意識流來讓我記得發生什麼事情的念頭數目就越龐大,而它們也都必須被一併丟棄。這麼一來,就會有為數不少的記憶區塊最後終得退出意識之外;也就是說,它們不再儲存在我的「前意識」中的記憶網絡,不再是硬碟可讀取的部分;現在,硬碟彷彿被「分割」了。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受到抑制的記憶就像是電腦病毒一般,會繼續在幕後工作,通常會在某個人的「資料庫」中創造越來越多的空白區塊。
我們平常偶而會短暫發生這樣的狀況,例如我們一時想不起某個人的名字,突然間,我們會連其他一些人名都記不得了,明明沒多久前這些人名都還話到嘴邊,我們很有把握自己會記得的。無法提取這些人名的情況可能不會持續很久,不過,在突然想不起來的那個名字與其他人名之間,已然形成某種連結,導致與它相關的任何一個人名都無法進入意識中。在這種情況下,失憶現象通常只是暫時的,但是在其他情況中,失憶的時間可能會持續更久,讓一個人「真的想也想不起來」。正如拉岡所言,「我們必須一直將其假定為無意識之基礎的,正是這種不可觸及性」。
無意識並不是一種「潛在性」
最複雜的思想成就可以在沒有意識的協助下達成。
── Freud, SE V, p. 593(強調為原文)
雖然不見得能夠了解所有人,但我們往往是透過理解最極端的個案,才開始懂得沒那麼極端的個案是怎麼一回事;在醫療上亦是如此,病情較嚴重的案例,會比病況較佳的案例更讓人看清疾病的發展過程。因此,透過跟相當嚴重的病人工作,讓佛洛伊德得出一個根本的結論:思考 ── 亦即在不同的記憶或意念之間建立聯想鏈結 ── 是在兩個不同的層次上運作,一個是意識可以接近的層次,一個是意識無法觸及的層次。後者這種層次的思考相當自動化,不需要我們意識的意向參與;這種思考的存在意味著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首度提出的:我們並非自己家裡的主人──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自己頭腦的主人。只要我們以為自己能意識到我們所有的想法及意向,我們就錯得離譜了。「意識的分裂」幾乎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
許多精神科醫師及哲學家都反對這一開始令人相當吃驚的理論。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的精神科醫師往往認為歇斯底里病人是假裝的,他們只是不想記得自己宣稱不記得的事。他們還譴責歇斯底里病人在其他方面也幾乎都是裝模作樣,尤其是跟疾病有關的部分,他們認為這些病人是詐病以逃避責任。哲學家斷言這種人是出於「自欺」(bad faith),他們不願意努力活著,是因為他們刻意不想面對自己的過去或現在。
這種不願意或「自欺」往往會出現在病人向治療師訴說自己的過去時,佛洛伊德自己就給過好幾個這樣的例子,當他詢問沒有被催眠的病人,某個狀況(例如,某個症狀)可能是什麼原因,病人立刻就說,他什麼都想不到。可是,在佛洛伊德按壓幾次病人的額頭,向病人保證他一定想得出來之後,病人終究承認他的確有想到什麼,並補充道,「我本來第一次就可以告訴你了」,然後解釋他覺得自己在第一次被問時內心浮現的答案太「沒什麼」或者「太蠢了」,所以根本不值得一提。正如佛洛伊德後來告訴我們的,正是在病人說某事很蠢或沒什麼時,我們必須給予最大的關注!
身為分析師,我們必須經常使用自己的猜想,來鼓勵分析者說出他對夢中元素的聯想,也就是夢中元素讓他想到的東西,無論是一個字詞、一個畫面、或是一個動作,這個聯想早已來到分析者的心上,只是他或她不願意透露。人們可能會把這樣的狀況認為是不好意思、害羞、羞恥,或甚至是自欺(我們要採用沙特對「自欺」的貶抑用法嗎?我是不想),但是對分析師及分析者來說,這些狀況與第一次說出那些早已被遺忘、並且數十年來無法接近的記憶,在感受及表現上是截然不同的。
在經過一段長時期的分析工作後,許多分析者在某個時間點會有一種什麼東西快要見光的經驗,他們隱約感覺到自己一直知道些什麼,卻從沒有表達出來、沒有承認過;佛洛伊德寫道,有時病人會說:「事實上,我一直都知道,我只是從來沒想過」。或許有人會以為這是現象學家所說的潛在性(latency),但容我再說一次,現象學家所說的這種情形在經驗上(我敢說「現象學上」嗎?)跟真正的無意識顯露時,分析者有時會感到震驚和氣惱的情況,非常不一樣。
真正的無意識顯露時,分析者往往會一時感到混亂困惑,接著會進入一段為時頗長、有時讓人心神不寧,但卻成果豐碩的聯想工作期。所謂的潛在性跟抑制是相去甚遠的兩件事情。無意識的內容並不是那些我們隱約知道的東西 ── 恰恰相反,它的出現就算不至於令人恐慌,也經常會讓人感到震驚,特別是在分析的早期。無意識不是人們可以從容以對的東西,就無意識而論,人們必須做大量的聯想工作,才能夠將被抑制物(the repressed)與其他的印象及念頭連結起來,也就是把被抑制的M1與M4、M5、M6連結起來。
佛洛伊德的看法是,所有重要的事件都銘記(register)或鐫刻(inscribe)在心中的某個地方,而我們的任務是要找到通達它們的方法 ──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發明一些技術,能夠通往被鎖上、加密、遮蔽或破壞的意念、願望及記憶。自由聯想是我們通達它們的主要技術,這需要我們花時間,動用聰明才智,才能幫助分析者學習怎麼做自由聯想,並且願意進行自由聯想。
(本文為《在診間遇見佛洛伊德:從聆聽、對話,到理解》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在診間遇見佛洛伊德:從聆聽、對話,到理解》 A Clinical Introduction to Freud: Techniques for Everyday Practice
作者:布魯斯・芬克(Bruce Fink)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4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