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譯|林徐達、梁永安
我個人對「天堂」的好感無疑因為一件事情而提升:我剛剛才與六歲大的兒子參觀完在皮卡迪利圓環(Piccadilly Circus)的特羅卡德羅娛樂中心舉行的「金氏世界紀錄」展覽。在經歷過幾乎一切都被以昂貴和操弄的手法異國情調化和過度膨脹化之後,我發現順著人類博物館的樓梯走進一個空曠、知性的空間讓人有鬆一口氣的感覺。這裡也有誇張的成分(例如一場最大型的豬祭和最多的貝殼或鈔票),但總算還在一個人類尺度內呈現。入口處那張相片中的男人的穿戴實在是十足異國情調的。(《金氏世界紀錄》會這麼說:「世界最大的羽毛帽!」)不過不管是他的微笑和直視眼神,還是平凡的波浪鐵皮,在在讓他顯得平易近人而容易理解。就在我觀察雜貨店的雜亂商品時,我發現了日常事物的古怪性:印有「天堂」字樣的一盒盒……餅乾。
「paradise」(天堂)這個字是源於古波斯語,再透過希臘文、拉丁文和古法語流傳至今,原先指的是一座花園或公園,即一個四面有牆的閉合空間。
新幾內亞高地是地球上最後的閉合空間之一,其山谷被認為是「失落」的山谷、其居民被認為是「未與外界接觸的」或「石器時代」的人群。維吉人(Wahgi)與外界的接觸發生得有多晚,可從這接觸是在一九三三年由飛機達成的事實可見一斑。利希—泰勒巡邏隊(Leahy-Taylor patrol)快速地跟進,將維吉人推入這個展覽所稱的「現代性的速成課」。我們會對於這類「首次接觸」的故事心存懷疑是有原因的,因為它們常常是靠著打壓更早的接觸史或忘掉原住民的旅行經驗的知識,來確立外人的發現行動。然而不管維吉谷的「花園」圍牆是的可滲透性有多高,清楚的是,很多原先對白人一無所知的高地社會,在廿世紀後半葉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急劇變遷。「天堂展覽」用一種清晰的精細度追蹤了這個過程。
展覽並不是沿著一條前/後的軸線來呈現新幾內亞高地的變遷,並沒有一條先於「外來」影響之前的「傳統」基準線。反之,我們都被拋進了轉變之中。現代性的影響是立即和戲劇化地縮影在雜貨店的多種多樣商品上。湧入的新財富,讓維吉人得以補償死於戰爭的人、負擔聘禮,還有以比從前更「傳統」的方式舉辦豬祭。外來的影響未必意味著傳統的失落。藉著將雜貨店和有啤酒商標的盾牌設置在波林屋和豬祭展之前,展覽混淆了一個將儀式與傳統、商品與現代性叢集在一起的常識性敘事。相反地,展覽中的所有展品都預設了雜貨店的存在,預設了維吉人在地區性、全國性與國際性力量的糾纏中混雜的生產活動。
維吉人之類的高地族群在「接觸白人之前」便在儀式中使用貝殼這一點,足以證明他們很久以前便與大型貿易網有所連結。一九三○年代礦工飛機的航線貫穿這些來源,增加了儀式中可用貝殼的供應量。新財富的流入讓人們可以輕易地從新幾內亞其他地區進口天堂鳥的羽毛。稍後,咖啡豆的收入支撐了這類有價品的積累。到了一九七○年代,豬祭舞者(照片中看起來是徹底的「傳統」模樣)頭飾上的火烈鳥羽毛又大根又漂亮,見證著把啤酒瓶引入波林屋組合的同一種變遷。如果我們仍然希望將火烈鳥羽毛與傳統聯繫起來,將啤酒瓶與現代性聯繫起來,我們必須步步為營。
我們很難從一個線性變化的角度理解維吉人的物質文化,很難將其放入一個接觸前/接觸後的架構。「大男孩口香糖」包裝紙看起來是屬於雜貨店的東西,但在摺起來和編織為頭帶之後,它們卻明顯成為了豬祭服飾的一部分。儘管它們在性質上和羽毛不同,但功能是一樣的。事實上,如果色彩是顯著特徵,那麼在翻譯和甚至在功能對等上便無太大問題。反之,火烈鳥羽毛在形狀和顏色上都與它們取代的紅羽天堂鳥羽毛截然不同。它們也是從維吉谷以外的地區進口,也是「商品」。這樣的話,一位展出維吉人物件的策展人有什麼理由只展出火烈鳥羽冠而不展出口香糖包裝紙頭飾呢?他有什麼理由只展出貝幣而不展出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紙鈔呢,特別是後者被綴在聘禮牌匾的時候?臂環裡的貨幣又是怎麼回事?「天堂展覽」讓這一類問題無法迴避,當我們參觀過豬祭區和大提袋區再繞回到雜貨店(這個小展覽的銜接空間鼓勵這樣做),我們對裡面的東西有了全新觀感。我們對「傳統」和「現代」的定義、對儀式用品與商品的定義,已經有效地被打亂了。
「天堂展覽」具有溫和的反身性。它挑選展品的方式挑戰了什麼是值得展出和什麼不值得展出的既有假設。有鑑於雜貨店的存在──它可說是一個集合體中的集合體──「維吉人的物質文化」可以是指維吉人使用的任何物品。但實際上,展覽的焦點則是較窄地集中顯示在傳統的維吉文物與新物料和新商品的互動。因此,舉例來說,繪著啤酒商標和「六到六」標語的盾牌在展覽中占有顯著位置,但卻看不見同樣繪有這兩種東西的彩繪迷你巴士──這種巴士穿梭於新幾內亞不同區域。(展覽專輯中只有一張彩繪巴士的彩色照片。)這是因為,盾牌可以表現一種「傳統」活動──氏族間戰爭──的持續性和混雜性。反觀巴士作為新舊物質文化中介的角色卻不那般明顯。但如果是一個關於地區貿易史的展覽,則可以把它包括進去。

無論如何,在雜貨店給出了一開始的錯愕之後,整個展覽都緊貼著「部落」生活常見的物品與活動,有效地展示它們是如何適應新的限制與可能性。「天堂展覽」聚焦在戰爭與結盟、盾牌與武器、聘禮支付、貝幣、豬祭、宗教變遷和婦女的手工藝品。它的基本策略是在接受的部落範疇內運作,翻譯它們,複雜化它們和歷史化它們。這裡質疑了兩個互有關聯的刻板印象:偏遠的部落民族被認為要不是原始和未與外界接觸,不然便是受到進步的汙染。儘管這種非黑即白的假設在專業的人類學領域中不再具有主導作用,但它們在一般大眾的心中卻仍然非常盛行。人們持續追求純粹的「原始」,從「石器時代」的達賽狄人(Tasaday)特定的歷史困境,到熱門電影《上帝也瘋狂》中的嘖貢桑人(!Kung San)──他們因為一個從飛機上丟下的可樂瓶子而向文明醒覺──的受歡迎可見一斑。在人類博物館中,維吉人的形象既是部落的也是現代的,既是地方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他們不能被視為封閉空間的居民,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是一個失落的天堂還是被保存下來的天堂裡。
我回想起展覽剛開始時看見的海報:一位臉部與胸部有著彩繪的男子,微笑並戴著令人炫目的羽毛,站在一面波浪鐵皮牆前。牆上寫著:「考威儀.愛匹(Kauwiye Aipe)以黑色的天堂鳥羽毛裝飾,慶祝他和兄弟合開的新店開張(一九七九年)。」一個現代的場合和一種隨意的異國情調氛圍:框出愛匹的羽毛和金屬都是進口的。鍍鋅牆壁的質地和骨架,還有它剛漆上的淡藍色,將這個「部落性」表演放入了一個當代時刻。當我參觀展覽時,發現自己被這種彩色相片所吸引。它們的份量看來異乎尋常的吃重,並且經由反思後得出,對這展覽的整個歷史化策略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
在民族誌性質的展覽中,照片通常都是用來呈現文化「脈絡」,並且根據風格和顏色而被歷史地編碼。紅褐色暗示十九世紀,鮮明的白色與黑色標誌了一個比較接近現在的過去,「真實」的色彩和坦率或隨興的姿勢則暗示了當代歷史。至少對我這一代人而言,褪色彩色照片會讓人產生一種「五○年代」的情懷,而展覽中至少有一張重要照片──一九五○年代聘禮牌匾的照片──是這種歷史「色調」。但大部分相片是明亮鮮豔的彩色照。為數眾多的放大照片與博物館展品的既有趨勢背道而馳:後者是將展品(包括新的物品)呈現為來自另一個時代的瑰寶。透過使用彩色照片,可以讓展覽者與展品的批判項目帶入當代時光(但這並不意味著相同的時代)。
在「天堂」展出的所有照片中,唯一非當代的相片是探險家利希在一九三三年「首次接觸」時期所拍的黑白照和最後壁板(「展覽的生成」)上的照片。前者是恰當且無可避免的,因為一九三三年只有黑白照片,而且黑白也符合這批照片的歷史編碼。但後者似乎就有問題了。為什麼一位維吉人為展覽雕刻展品的過程被拍成黑白小照片,但十年前的豬祭卻是以全彩呈現?為什麼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工作背景看起來像是另一個時代,有別於展覽中其他地方所呈現的複雜的、當代的、真實的、歷史的時代?由於展覽的規模有限,手法也有點極簡主義的味道,「展覽的生成」壁板可說是呈現了恰當的人物與活動。但由於照片沒有色彩且尺寸過小,讓人覺得這些照片是事後才添加,而不是原構想就有。即便這一展區規模不大,但仍是放得下一張拍攝製作大提袋的婦女的彩色大照片,而非只是以小張尺寸的黑白照呈現。至少,我可以找到一種方法來展示歐漢龍在高地的形象,這是展覽和目錄中都缺少的。低調與權威在這個缺席中如何達成共謀?
作為一個一貫的歷史化策略,「天堂展覽」對彩色大相片的使用打破了在西方場合把非西方展品加以美學脈絡化和文化脈絡化的既有成規。美學性呈現通常會排除或最極小化這些相片脈絡的使用。若展覽中出現照片,通常都是小張的,或者是置於距離展品較遠之處,以便參觀者專心欣賞展品的外形特徵。文化性的處理方法則是傾向於納入使用中的物品的照片。但是在上述兩種狀況中,照片都不能太過顯眼以致影響了參觀者對實物的注意力。西方博物館對物件的壓倒性重視──不管是因為物件的美、稀有或代表性而加以收藏、保存與展示──讓物件與脈絡之分、主題與背景之分成為了關鍵分別。「天堂展覽」──一個透過物質文化來看待歷史變遷的展覽──走在一條細線上,既維持又模糊了這種區分。
(本文為《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部分書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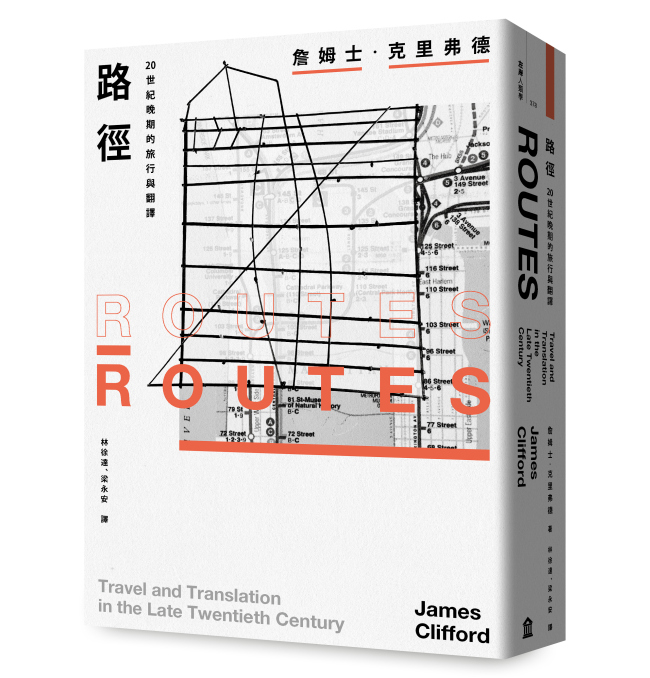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作者: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4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