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p.jpg)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晚年被痛苦包圍,1920年他的女兒蘇菲死於流感,1923年他的外孫海因茨也夭折,同年他被診斷出罹患癌症,前前後後接受了33次手術,極度的疼痛使他預先寫下遺書。儘管如此,他卻沒有注意到另一個危機正在靠近:納粹將會迫害他,燒他的書,企圖監禁他全家,他必須仰賴過去的患者,譬如波拿巴公主(Marie Bonaparte)等人的奔走請託才能成功逃走保住性命。
佛洛伊德一生深愛奧匈帝國,他完全不覺得自己是猶太人有什麼問題,而這種情況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最為明顯。儘管其他人紛紛逃離納粹,並鼓勵佛洛伊德也這麼做,但在納粹掌權的德國與奧地利合併後,佛洛伊德依然猶豫不決,資深記者安德魯‧納哥斯基(Andrew Nagorski)說:「為什麼佛洛伊德讓自己陷入這種極其危險的境地?逃離對他來說是相對容易的方式,他為什麼不早點離開維也納呢?」納哥斯基的著作《拯救弗洛伊德:將他帶往自由的救援者》(Saving Freud: The Rescuers Who Brought Him to Freedom)探討了這個問題,一部分敘述了佛洛伊德人生的最後幾年;一部分記錄了1938年作為佛洛伊德「救援隊」的患者、同事和合作者的事蹟;並描繪了一座城市與世界處於災難邊緣的光景。
1938年,納粹第一次來到佛洛伊德的公寓,準備沒收任何「不當取得」的資金,妻子瑪莎(Martha Freud)請他們把步槍放在傘架到桌邊坐下,她從家裡的保險箱拿出現金給他們。即使納粹粗暴地動手並威脅開槍,長子馬汀(Martin Freud)仍設法藏匿了一些不利文件;他還賄賂了另一個人,讓他帶著一個足以定罪的物品離開。波拿巴公主則趕到維也納,穿著華麗的衣服坐在通往佛洛伊德公寓的樓梯上,將佛洛伊德的檔案和珍貴文物藏在裙內偷偷運到希臘大使館。威廉‧布列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 Jr.)則直接求助羅斯福總統,讓一輛掛著美國國旗的大使館汽車停在佛洛伊德家門前。馬克斯‧舒爾(Max Schur)甚至為馬丁和安娜(Anna Freud)提供了自殺藥以防萬一,並拒絕跟佛洛伊德的家人一起離開,除非他也離開奧地利。
但自始至終,直到最後一刻,佛洛伊德似乎仍在「否認」周圍發生的事情。毫無疑問,佛洛伊德鄙視納粹,但他堅信納粹的行動永遠不會成功,他對布列特說:「一個孕育出歌德的國家不可能變壞。」後來,他堅稱納粹主義永遠不會在奧地利獲得支持,並安慰波拿巴說:「我們的人民沒有那麼殘忍。」佛洛伊德對奧地利國內的右翼不抱任何幻想,但他深信天主教傳統不可能讓這個國家支持國家社會主義,他對莎樂美(Lou Andreas-Salomé)堅稱:「正是這樣的天主教傳統保護我們免受納粹的迫害。」如果沒有,那奧地利至少會受到國際法的制約,他向歐尼斯特‧瓊斯(Ernest Jones)保證說:「我們將受到法西斯主義、政黨專政、消滅反對派、反猶主義的攻擊,但我們應該保持獨立的和平規範,法律不可能剝奪少數群體的權利。」然而,每一個這樣的期盼,無論嚴峻與否,都擱淺在佛洛伊德於別處所稱的「現實原則」的荒涼海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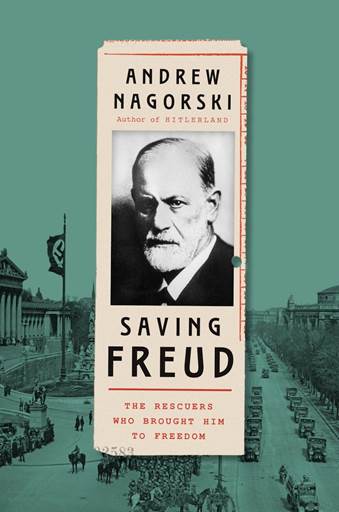
佛洛伊德避免花太多心思擔心納粹,但納粹肯定花了很多時間打佛洛伊德的主意。納粹的宣傳毫不手軟地把目標對準了精神分析這門「猶太科學」,一幅又一幅漫畫用最原始的刻板印象醜化猶太精神分析師,他們是唯利是圖的小販和變態,想要把孩子性感化,引誘純潔的日爾曼女性到床上。
《血液與土壤而生的德國公共健康》(Deutsche Volksgesundheit aus Blut und Boden)在1933年的月刊宣稱:「精神分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證明猶太人永遠不會帶給我們德國人任何好處。即使他提供我們5%新穎且顯然是好的東西,但學說裡的95%對我們是具有破壞性與毀滅性的。」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企圖把佛洛伊德全家都關起來;戈林(Hermann Göring)似乎勸阻了他。在戈培爾(Joseph Goebbels)親自參加的一場焚書活動中,佛洛伊德的書被扔進了火焰,廣播員宣佈:「為了對抗毀滅靈魂、對性生活的高估,為了高尚的人類靈魂,我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的作品獻給火焰!」儘管如此,佛洛伊德卻對瓊斯說:「我們(德國)取得了多大的進步,中世紀的時候他們會燒死我,現在只燒書了耶。」
佛洛伊德並不是唯一的目標。在德國蓬勃發展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清除了猶太人和猶太同情者,更名為德國心理研究與心理治療研究所,並負責把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去猶太化」,發展出一套適合雅利安人心理的精神分析理論。研究所的一些學者設法移民到巴勒斯坦,有些人甚至帶著個人藏書逃跑;但其他書籍和學者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納哥斯基寫道:「以前自由的德國出版的書籍被沒收存放在萊比錫,其中包括維也納的出版物。15名猶太精神分析學者沒能加入逃離德國的行列,很快就死在了集中營。」
佛洛伊德決定離開時幾乎為時已晚。只有準備乘坐專機飛往維也納的瓊斯不斷地懇求,才打動了他的理智;只有他深愛的女兒受到直接的威脅,才打動了他的內心。安娜被傳喚到蓋世太保總部,差點被送進集中營,而佛洛伊德才終於醒悟過來。

隨之而來的是最後關頭的匆忙行動,他們一邊藏匿書籍把家當運出國,一邊確保資金和文件齊全,以支付所謂的「帝國稅」(Reichsfluchtsteuer)——納粹向尋求離開德國的猶太人所徵收的稅。即使有了波拿巴和布列特的現金幫助,情況還是相當緊急。當時的歐洲對猶太難民並不友好,佛洛伊德家族需要不少於20份的外國簽證——佛洛伊德一家,他們的傭人,舒爾一家,還有各個姻親。為了從英國政府手中獲得這些東西,瓊斯不得不動用強大的人脈關係。
為了沒收猶太人的財產,納粹佔領了佛洛伊德家族擁有的維也納出版社,並嚴厲要求他們透露所有的外國資產。安東‧邵爾沃(Anton Sauerwald)是納粹指派來監督這次掠奪的「託管人」。邵爾沃是一名年輕的化學家,讀研究生時他跟一位年長的猶太教授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但這位教授後來去世了。之後,他依然是一名狂熱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他譴責出版社的非猶太人與「猶太豬」合作,並告訴舒爾,他認為猶太人不是「必備的人口組成部分,在或許令人遺憾但為了目的可不擇手段的情況下,猶太人必須被消滅」。這就是一個為蓋世太保的粗魯行徑道歉的男人的矛盾之處,他對安娜說:「你還能指望什麼?這些普魯士人並不認識佛洛伊德。」但邵爾沃——根據安娜的證詞——卻成為佛洛伊德家族成功逃亡的關鍵人物。
納哥斯基寫道,在走訪出版社的過程中,「邵爾沃有條不紊地閱讀了許多佛洛伊德的作品,並發現自己越來越被佛洛伊德對精神分析的博學與理論所打動」。隨後,邵爾沃向上級隱瞞了一些佛洛伊德家族資產的證據,並偷藏了幾份可能會把他們送進集中營的檔案。他將奉命銷毀的書藏起來,協助整理了剩下的書存放在奧地利國家圖書館,這些書籍在那裡安然度過了戰爭。
當家人最終拿到簽證時,佛洛伊德被要求簽署一份聲明,發誓他沒有受到惡劣對待。他照做了,還寫了一篇附錄:「我衷心地向大家推薦蓋世太保。」這又是一次經典的佛洛伊德式諷刺。我們想知道,但無法知道,他當時對邵爾沃抱持著怎樣的看法,或是具體在想些什麼。我們也無法確定邵爾沃到底幫了佛洛伊德的四個姐妹多少忙,或是他能夠幫些什麼。佛洛伊德的四個姐妹留在了奧地利,在戰爭後期邵爾沃探望了她們,並且可能保護了她們。四個姐妹在邵爾沃被轉調到德國空軍不久後,便死在了集中營。

多虧了救援隊,佛洛伊德夫婦最終抵達了倫敦。他在波拿巴保護下的一所小房子安頓下來,佛洛伊德對她秘密保存的所有物品感到驚奇,他說:「所有的東西都回來了,除了我以外。」佛洛伊德確實在那裡,但也不在那裡。他一如既往地工作,1939年完成了最後一本書《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這是一部在當時和現在都很奇怪和有爭議的作品。重死的難民佛洛伊德寫了摩西的各個面向,有時是埃及人,有時是希伯來人,有些是真實的,有些是神話的,而所有面向——謀殺、欺騙、內疚和理想化——交織而成摩西這個複雜的人物,一個被迫流亡的曲折故事。
佛洛伊德依然見到了像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倫納德(Leonard Woolf)和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這些重要人物,他還坐下來為達利(Salvador Dalí)畫了一幅肖像。他為《BBC》錄製了一段錄音,還被拍到遞給嬰兒一些花。最後,當癌症惡化變得極其痛苦時,他要求舒爾遵守諾言,而這位好醫生照做了。回到維也納時,沮喪的安娜問父親:「如果我們都自殺不是更好嗎?」佛洛伊德的回答很簡潔:「為什麼?只因為他們希望我們這麼做?」但現在,這個處在人生結尾、告訴家人自己唯一現實的希望是「在自由中死去」的人,卻以自己的方式面對了死亡。
也許這是回答納哥斯基對於為什麼佛洛伊德花了這麼長時間「否認」的部分答案。簡單地說,他想死在家裡,並堅持完成願望,直到這個家不再屬於他,或者被拖到外面去死,納哥斯基寫道:「佛洛伊德的宇宙中心是山坡路19號(Berggasse 19,現為佛洛伊德博物館),他和瑪莎在那裡養育了六個孩子。他在那裡定期會見患者,撰寫文章和書籍,每週三晚上他會跟維也納精神分析協會的成員聚會。他習慣於一些例行公事,比如晚上在環城大街散步,走訪城市裡著名的咖啡館,抽雪茄,看報紙。」換句話說,佛洛伊德依附於一種生活方式,依附於生活在一個特定的地方。他喜歡用特定字詞解釋自己,1926年他對一位記者說:「我的母語是德語。我的文化、我的成就都是日耳曼的,我一直認為自己就是日耳曼人,直到我看見德國和德屬奧地利的反猶情緒增長。從那時起,我更願意稱自己為猶太人。」
但即使是這個版本的佛洛伊德,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行事,因為他是一個對猶太復國主義持懷疑態度的猶太人,他也拒絕了逃往巴勒斯坦的邀請,並將最後的作品獻給了一本關於摩西的書,它被許多猶太人譴責為可恥,甚至是背叛的作品。佛洛伊德的矛盾仍然存在,而納哥斯基的作品更凸顯了這點。正如舒爾尖銳地的評論,佛洛伊德或多或少「忘記了希特勒也是奧地利人」的事實。但話說回來,正如安娜多年後所觀察到的:「回顧過往,總是很容易知道什麼是對的,知道應該做什麼,以及什麼時候應該做。」假如我們處於相同處境,承擔著相同責任,誰能保證我們能想得比佛洛伊德更周到,或者採取不同的行動呢?今天,隨著得來不易的權利被推翻,隨著世界局勢不穩與經濟危機逼近,隨著民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脆弱,把我們自己放在佛洛伊德的立場上,或許也讓我們去質疑和反思,現階段的生活有哪些部分可能會約束我們,以及哪些幻想和依附是我們無法想像從生活中失去的。
原文出處:New Republic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