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埃金(Hugh Eakin)的著作《畢卡索之戰》(Picasso’s War)雖然標題出現了畢卡索,但他只是相對次要的角色,從序言就能清楚發現這點。戲劇性的開頭將讀者帶回1924年約翰‧奎因(John Quinn)紐約家中所舉行的一場晚宴,奎因是一名華爾街律師,也是現代藝術和文學的先驅贊助人。咖啡端上來後,奎因帶朋友和其他現代藝術愛好者欣賞他的新收藏,埃金寫道:「他們被巨大的矩形所包圍,在夜間與之相遇既令人著迷又詭異。」如果從書名來猜,讀者可能會以為這裡說的巨大矩形是巴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某幅油畫,但並非如此。
這幅畫是亨利‧盧梭(Henri Rousseau)的著名作品《沉睡的吉普賽人》(The Sleeping Gypsy,1897年),目前收藏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盧梭是自學成才的藝術家,曾任職法國的地方海關。畢卡索著迷於盧梭的作品,把他介紹到自己的現代藝術圈內,甚至為他舉辦了著名的宴會。我們在書中後面瞭解到,畢卡索協助說服奎因購買了這幅油畫,在這裡盧梭是主角;畢卡索只是背景人物。
這本書的副標題為「現代藝術如何來到美國」,故事主角是兩個美國人,而不是畢卡索(他繼續以偶然的方式出現):第一個是奎因,然後是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創館館長巴爾(Alfred H. Barr Jr.)。埃金利用這兩個角色帶領讀者走過美國人擁抱20世紀歐洲現代主義長達數十年的歷史,這是一個斷斷續續的、偶然的,並非註定的結果。現在已經沒有人記得奎因,不過巴爾仍被譽為開創性的藝術史學家和博物館館長。
這兩個人都具有「阿甘」的特質:總是出現在各種重要的歷史時刻。某些情況下,他們是這些時刻的關鍵人物——比如奎因在1913年組織開創性的軍械庫展覽會(Armory Show)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其他情況下,它們只是在正確(或錯誤)的時間出現在正確(或錯誤)的地方。例如巴爾在1927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鞏固權力的時候參觀了蘇聯的現代藝術收藏;1933年德國國會大廈焚毀、納粹開始接掌德國政府之時,他恰巧就在那裡養病,並親眼目睹了隨後納粹對現代藝術的攻擊。

埃金記錄了這兩個主角如何努力讓美國藝術家、鑑賞家、收藏家和公眾接受畢卡索與其藝術圈,因此,《畢卡索之戰》最重要的貢獻不在於描繪這兩個人或他們喜愛的藝術家生平,而是以娛樂的方式詳述了大西洋彼岸現代藝術世界的開端。在學術刊物和一般資料來源中,這段歷史通常主要是從知名藝術家的角度來講述,而藝術家的經銷商、其作品的收藏家,以及負責展出藝術品的博物館策展人都被邊緣化。埃金的故事顛覆了常規的劇本,他書中的經銷商、收藏家和策展人——也就是藝術產業——才是故事的核心。
埃金的重點放在20世紀的藝術界。不過在整個故事中,偶爾還是會出現19世紀的藝術家,如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愛德加‧竇加(Edgar Degas)、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法國印象派畫家與其藝術之路標誌著現代藝術的一個轉捩點:它如何走向公眾,並且銷售給收藏家。
從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末期,法國藝術家透過政府贊助的沙龍展覽展示他們的新作品。由於受到各個群體與體裁的壓力,這個體系在19世紀下半葉崩潰了。那些被排除在沙龍之外的藝術家,比如印象派畫家,開始尋求其他方法來展示和銷售作品。社會學家哈里森‧懷特(Harrison White)和藝術歷史學家辛西亞‧懷特(Cynthia White)在1965年出版的《Canvases and Careers》探討了「經銷商-評論家體系」的出現。在這個體系下,印象派和其他現代藝術家越來越仰賴經銷商把自己的作品推銷到市場上,隨著向公眾展覽藝術品的管道不再侷限於評獎的展覽,藝術家和經銷商必須用其他方法來展示與證明新作品的價值,而藝術評論家填補了這個空缺。於是,報刊雜誌上盛讚作品的評論,逐漸取代了沙龍的榮譽獎章。
儘管懷特夫婦關注的是印象派畫家,但其他學者認為經銷商-評論家體系真正的轉變發生在隨後的20世紀初,也就是埃金故事的起點,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描繪了逐漸成為主流的經銷商-評論者體系。簡而言之,埃金告訴讀者目前的制度如何讓藝術進到市場,如何被接納為藝術品賦予其經濟價值,並最終被世人推崇與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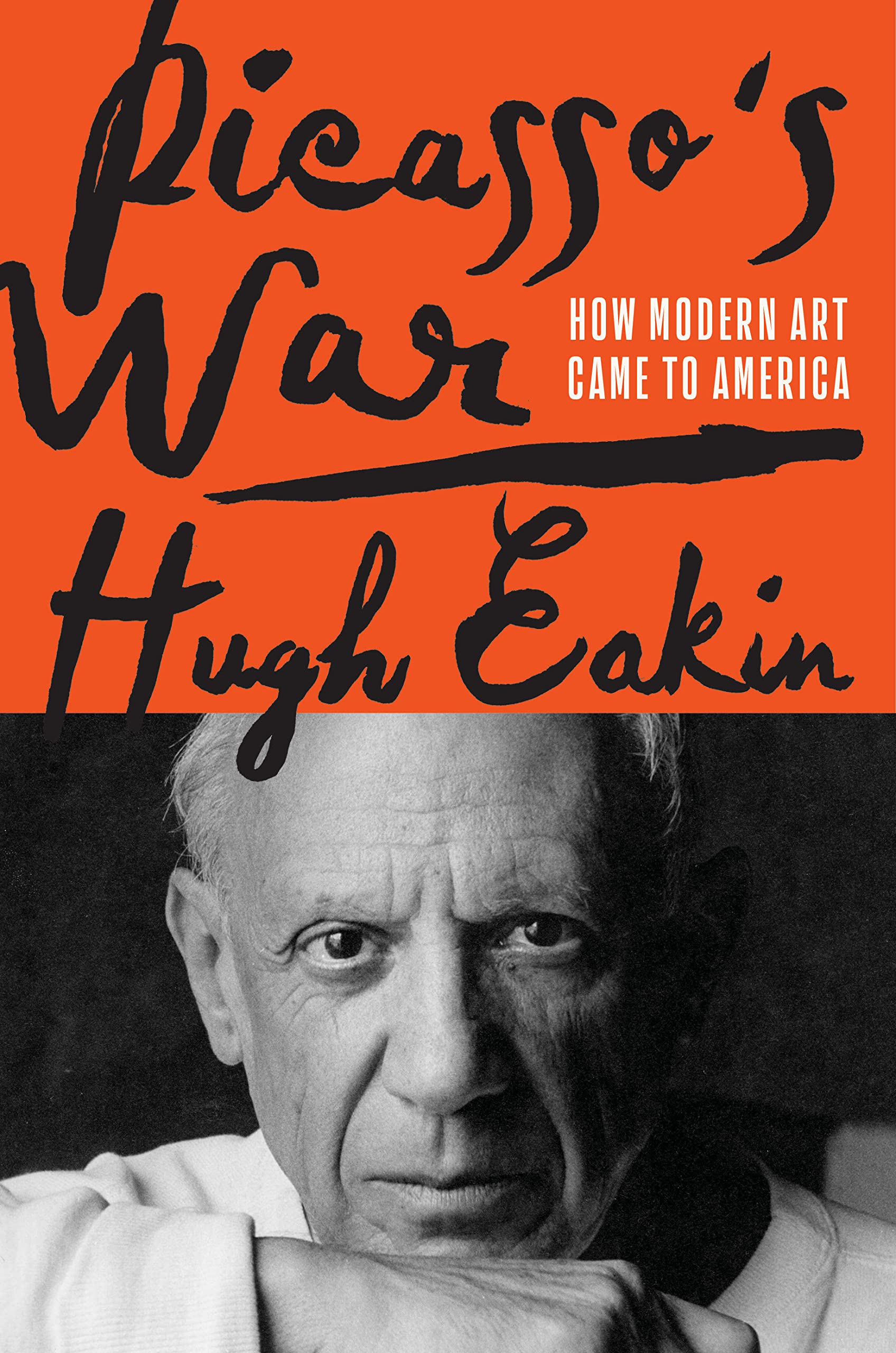
在一些藝術史紀錄中——也許是外行人的印象——藝術品經銷商往往被形容為靠著藝術創新而獲利的「寄生蟲資本家」。不過在《畢卡索之戰》裡卻不是這樣:經銷商得到了應得的待遇。例如畢卡索和他的朋友與同行——如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和安德烈‧德蘭(André Derain)——在1910年左右可以自由自在地創作和合作,因為他們在巴黎的德國藝術品經銷商丹尼爾-亨利‧坎韋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保證會買下他們產出的任何東西,他們可以一起到法國南部旅行,然後一起創作,坎韋勒的經濟支持讓藝術家得以無後顧之憂的發揮創意。
讀者能從埃金的書瞭解到,這種藝術創新、商業成功和聖人化的過程——理論上聽起來很高尚——往往是相當醜惡的。在美國走向推崇現代藝術之路的過程中,稅法需要進行修改,難看的離婚也必須解決。此外,還發生了兩場世界大戰,導致藝術家受傷或死亡,猶太裔經銷商也不得不逃命,其收藏品則被當成敵人的資產或被納粹掠奪。埃金故事的主角也是那群觀點矛盾、性格存在缺陷的人。在數百頁的書中,奎因以英雄般的現代藝術擁護者形象出現,但後來我們看到,儘管他有一些猶太朋友,但他卻是一個極端的反猶主義者。他的信件充斥著對畢卡索的長期經銷商保羅‧羅森伯格(Paul Rosenberg)的糟糕言論,以及對東歐猶太人逃離種族暴力而移民至紐約的惡毒評論。
正如埃金所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幾個方面鞏固了畢卡索和現代藝術在美國的地位。首先,當法西斯主義者和獨裁者譴責現代藝術偏離常規時,自由民主與激進前衛的創新藝術之間產生了連結;其次,藝術品、藝術家和藝術品經銷商在戰爭期間需要一個安全的避風港,而遠離戰場的美國自然成為了最好的避風港。
當戰爭在歐洲肆虐時,巴爾和現代藝術博物館組織了一場轟動一時的畢卡索展覽,這次展覽的作品都是在法國淪陷前剛從巴黎搬出來的,它奠定了現代藝術博物館成為美國藝術品味引領機構的地位。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該展覽在北美的幾十個城市展出,成千上萬的參觀者湧入只為觀賞一場幾年前還被美國媒體嘲笑的藝術家所舉辦的回顧展。故事裡的主角事實上或許根本不關心人權、不關心自由,但他們知道沒有比納粹與法西斯崛起還更好的時機,可以慫恿美國人去認識與購買現代藝術作品;恐怖的戰爭和大屠殺,間接使得畢卡索登上了20世紀藝術界的巔峰。
原文出處:Foreign Policy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