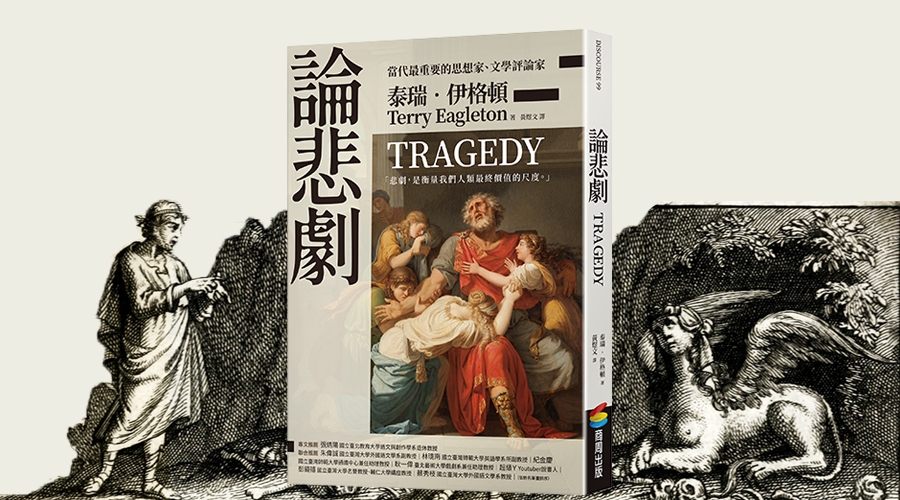
文|泰瑞.伊格頓
譯|黃煜文
《伊底帕斯王》(Oedipus Tyrannus)存在著與算術有關的弦外之音,這是長久以來一直能明顯看出的事實。伊底帕斯的父親拉伊俄斯(Laius)在三條道路交會處被殺;與伊底帕斯鬥智落敗的斯芬克斯(Sphinx)是不同生物的混合體;斯芬克斯用來嚇唬當地人的謎語,不僅與數字有關,也將人類存在的三個階段融合成一個問題。《伊底帕斯王》有一個著名的待解難題,那就是拉伊俄斯是被一個人還是被數個人殺害。如果殺人者有數人,那麼就不能說伊底帕斯犯下弒父的罪行;但是,無論我們是否做了任何事,或者我們永遠無法確知自己做了任何事,我們仍可能有罪。如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評論,他說:「整個希臘悲劇認為這種純屬偶然的觀念使我們既有罪又無辜,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伊底帕斯暴躁地強調,一就是一,一不會大於一,然而事實上伊底帕斯自己正是一大於一。伊底帕斯既是兒子,又是丈夫;既是父親,又是兄弟;既是罪犯,又是立法者;既是國王,又是乞丐;既是本地人,又是外地人;既是毒藥,又是解藥;既是人類,又是怪獸;既有罪,又無辜;既眼盲,又洞察;既神聖,又受詛咒;心思敏捷,卻腳步緩慢;既能解謎,又無法參透奧祕。伊底帕斯總是善於視自己為無物。如一名批評家所言,伊底帕斯展現出「自我算術上的不穩定」。我們永遠無法確定,一究竟是多少。計數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單純直接,殺死拉伊俄斯的人究竟有幾個一直無法得出一致的結論就是明顯的例證。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無數祖先的後裔,這些祖先就像許多纖細的絲線交織在一起,使他們成為難以閱讀的文本。無論如何,從索福克勒斯的戲劇可以明顯看出,與後現代主義的看法相反,並非所有的複數都是良性的,並非所有的混和都是善意的,並非所有對身分的堅持都能有所啟發。
伊底帕斯雖然大於一,但他的數量並不會比任何人多,因為所有的個人,如果我們僅從人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來思考,都必然不完全與自我等同。此外,在象徵界占據一個位置,等於同時扮演一整串角色(母親、姨嬸、堂表姊妹、姊妹等等),就跟《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裡自以為是的波頓(Bottom)想做的事一樣。無論如何,成為自己或多或少都帶有一點表演性質。《伊底帕斯王》與其他作品也許是與角色扮演有關的劇作,但作為一齣劇場作品,《伊底帕斯王》也是雙重角色的具體實例,它顯示的自我不穩定及其他原因說明了柏拉圖為什麼在《理想國》(Republic)中對戲劇表演的態度如此冷淡。戲劇的雙重性在於它在某種意義上將城邦反映回城邦本身,我們曾經提到,這種做法不僅挑戰了自身的同一性,也肯定了自身的同一性。如果觀眾能用疏離的眼光看待自己,讓自己擺脫以往對自我的理解,觀眾將可吸收這種危險的知識,並且逐漸接受它。
跟其他人一樣,伊底帕斯對自己的看法及其他人對他的看法,兩者之間是分裂的。以他是亂倫的弒父者來看待他,顯然與他自己看待自己是不同的,而伊底帕斯無意間說出模棱兩可的言語—就跟任何人說話一樣—其真實意義主要是從他者的觀點(語言、親族與社會關係構成的整個領域)來決定,而非由他自己意識中的意圖來決定。自我的真實與主體的真實不相吻合。某個外來的事物在這具因為能自我決定而沾沾自喜的身軀中行動與說話,並且持續在他的話語中以謎語般的弦外之音出現,事實上,這個事物甚至潛藏在他的名字裡,瓦解他的想像認同,最後驅使他步入死亡。
伊底帕斯如何說話與他如何被說,兩者之間的差異顯示人性本身是諷刺的化身。其諷刺之處在於,最初建立意識主體的事物—他者或社會潛意識—注定會規避主體對它的認識,因為沒有任何觀點可以整體地掌握它,他者的他者並不存在。無論如何,自我藉由遺忘自身的形成而得以存在,因此自我雖屬於人們認同的一部分,但人們永遠不可能與自我的認同完全同一。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說,一個人永遠不可能只是一個人,因為主體一開始要存在必須經過一段原始的分裂過程。當伊底帕斯終於遇見真實的自我時,他會覺得眼前的真實自我彷彿陌生人。當他面對自己真正是誰時,也就是他完全忘卻自己的時候。認識的危機也是盲目的時刻。知識照亮一切,但耀眼的光芒會讓你看不清。當真實被揭露的時候,我們將得知無知與受騙的事實。
身為統治者,伊底帕斯已經是許多人的綜合體,他一肩扛起整個社群的責任。伊底帕斯對祭司說:「我的心不只是承擔我自己的重量,也承擔你及所有人民的悲傷。」在獨特的亂倫算術中,每個人也是幾個人的綜合體。亂倫禁忌認為二合一是行不通的,但性欲拒絕接受這樣的非難。在一般的性生殖中,一加一等於一,我們把多重結果的例子放到一邊,就以這個性生殖行為的公式來說,女性伴侶合併擁有四個角色,她是丈夫的妻子,也是丈夫的母親,她是他們的孩子的母親,也是他們的孩子的祖母;男性伴侶也一樣,他是這名女性的兒子,也是這名女性的丈夫,他是他們的孩子的父親,也是他們的孩子的兄弟;而孩子是女兒、姊妹與孫女?亂倫因此是個特別引人注目的諷刺例子,一件事物既是自身又是他物,各樣的諷刺遍布索福克勒斯大作各處。
然而我們已經看到,一件事物既是自身又是他物—例如,一個女人同時是母親、堂表姊妹、姑姨與女兒—乃是象徵界的構成特徵;所以無論亂倫的問題是什麼,它都不可能是純粹多樣性的問題。越界已經是司空見慣。柔卡絲塔(Jocasta)為了緩解這個惡劣的局面,便說許多男人都曾在夢中跟自己的母親上床。此外,為了讓親屬系統有效運作,亂倫的可能必定永遠存在。如果角色必須靈活到足以相互結合,那麼不正當的排列組合有時就是會發生。從這點來看,逾越常軌其實也是常軌的一種樣態—就像伊底帕斯一開始也帶著受傷的腳,文明社會也誕生於暴力的起源。最初,欲望產生了象徵界,但欲望總是不會乖乖待在適當的位置上。
怪物傳統上是一種生物,就像斯芬克斯一樣,牠抹滅區別、竄改差異而且混合原本應該各自明確的特徵。理查德.麥卡比(Richard McCabe)表示亂倫隱含「認同的喪失或不確定」,「傳統親屬詞彙的混淆導致倒退到巴別塔(Babel)時代,明確的價值因此變得模糊不清」。 羅蘭.巴特形容亂倫是「意想不到的字彙」,這是出自現代的一句經典低估。怪物是一種無法對「那是什麼?」的問題回覆明確答案的事物,如同人類自己也無法回覆一樣。從這個意義來說,伊底帕斯與斯芬克斯是鏡像,也是對立者。如果「人類」是斯芬克斯謎語的答案,那麼身為人類發言者的伊底帕斯便承認了人類是醜怪的雜種,因此與斯芬克斯是類似的,而就在此刻,伊底帕斯心智的機敏也顯示自己優於斯芬克斯。
伊底帕斯自己就是謎語的答案,正如他自己就是他正在追捕的歹徒。這種自我指涉的處境帶有某種溫和的喜劇成分,暗示著毫無意義地追逐自己的尾巴。它反映較為陰暗的亂倫喜劇,而且可以作為還不錯的玩笑主題。正如艾瑞絲.梅鐸(Iris Murdoch)《斷頭》(A Severed Head)裡的人物所言,這類玩笑無疑是對撼動心靈深處的性欲模式的一種防禦。但亂倫關係也顯示某種不協調,而這正構成幽默的主要成分。伊底帕斯評論自己面臨道德敗壞的處境—「是新郎又是兒子」、「兄弟與兒子的父親」、「從我出生之處生子」—他的話充滿驚悚的機鋒。這種黑色喜劇的調性也出現在美國諷刺作家湯姆.雷勒(Tom Lehrer)創作的關於索福克勒斯主人翁的歌裡:「沒有人像他一樣愛自己的母親,/他的女兒是他的姊妹而他的兒子是他的兄弟。」斯芬克斯的謎語其實很類似我們在耶誕拉炮裡發現的笑話。亂倫是一種極度精簡的形式,被一部本身就足以稱為精簡的奇蹟之作的劇作描繪出來,以笑話的角度來說,這類精簡的形式可以省卻我們的心力,讓我們毫不費力地放聲大笑。
怪物與亂倫都意謂著類別的混淆。然而,如果象徵界裡的事物無論如何都混合了各種事物,那麼為什麼只有亂倫被挑出來成為令人憎惡的事物?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亂倫對城邦構成威脅。在沒有異族通婚關係的狀況下,性愛,城市的建造者,將一直深鎖於家庭領域之內。如弗蘭科.莫瑞提(FrancoMoretti)所言:「亂倫是一種欲望形式,它使鞏固與維持財富網絡的婚姻交換—在權力依然與具體的人連結的社會裡—無法持續。」亂倫是一種反社會的熱情,它讓欲望與安頓下來的社會形式分離,因此使象徵界面臨由內崩解的危險,連帶地也使象徵界維繫的整個意義世界出現危機。亂倫任意竄改意義,它是一種無意義或荒誕的物種,因此更像是一種謎語。
所以,人必須在婚床上遭遇外來者,如果他跟伊底帕斯一樣,沒有在婚床上遭遇外來者,那麼最後他將成為自己的外來者。亂倫禁忌的部分意義在於讓你從想像的領域—亦即同一、相似與相互反映的關係—往外走向他者的領域。家庭是情感親密的地方,與政治國家不同;但家庭必然也有助於維持國家(舉例來說,家庭是生產勞動力的地方),因此家庭無法讓你擺脫國家。想像界不能凌駕於象徵界之上。古希臘人清楚地區分家庭感情或對親屬的愛,以及對外人或非親屬之人的情欲依戀。亂倫破壞的正是這種對立關係。而這也顯示以下的事實,用艾瑞克.桑特納(Eric Santner)的話說,性欲「本質上就是違常的,本質上就是會超越它的目的功能(在作為經濟單位的家庭中進行生殖)」。如果性欲本身是違常的,那麼作為性欲適當形象的,應該是亂倫而非家庭單位。
與《伊底帕斯王》一樣,《奧瑞斯提亞》與《安蒂岡妮》也涉及家庭與政治領域之間的爭端。如果《安蒂岡妮》開啟了家庭與國家的對立,那麼《伊底帕斯王》也是一樣,只是沒那麼露骨。安蒂岡妮的名字暗示她對性生殖秩序的反對,亂倫也是如此。亂倫破壞性生殖秩序,不僅因為亂倫會產生殘缺的後代(畸形的斯芬克斯本身就是亂倫的產物),或因為意識到這點可能會完全阻礙性生殖,而是因為亂倫會藉由戲仿一般正常傳承的方式在世代間傳承下去。如果安蒂岡妮生下孩子,她的孩子會擁有一個是外祖父的舅舅。甚至可能出現雙重亂倫,例如在湯瑪斯.曼(Thomas Mann)的小說《神聖罪人》(The Holy Sinner)中,亂倫生下的孩子又娶了自己的母親。為了阻止人把不幸傳遞給人,因此必須切斷這條致命的血脈傳承。
書籍資訊
書名:《論悲劇》 Tragedy
作者: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出版:商周出版
日期:2021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