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暢銷作家謀害親生小孩,只因她們佔據先生的愛?
八歲雙胞胎妹妹,因忌妒殺了姊姊?
丈夫的復仇!製造妻子的死亡意外?
奪取別人聲名、金錢,甚至另一半的夢遊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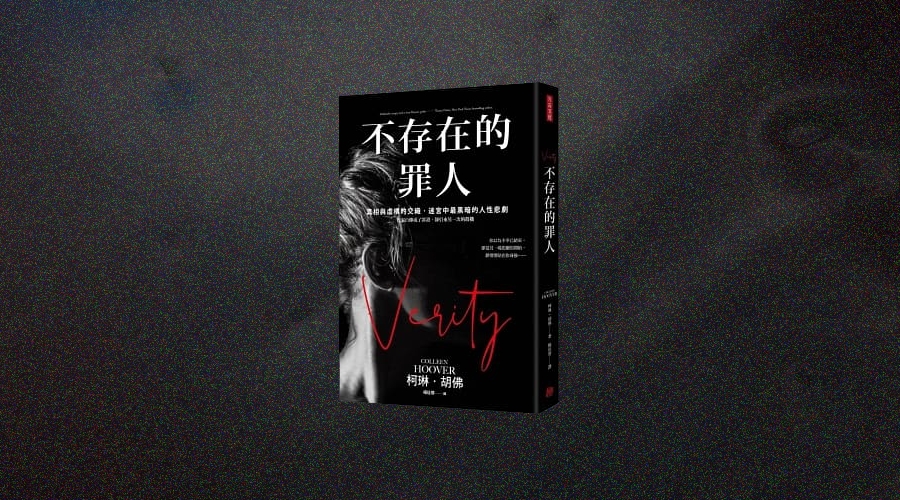
文|Colleen Hoover
譯|楊佳蓉
鮮血還沒濺到我身上,我先聽見了他頭顱裂開的聲音。
我倒抽一口氣,連忙退回人行道上,一腳的鞋跟沒閃過路緣的水泥塊,我抓住禁止停車的標誌桿子穩住腳步。
那人幾秒鐘前還站在我前面。我們跟著一群人等紅綠燈,他早了一步踏上柏油路,就這樣被卡車撞上。我一個箭步想阻止他─只在他倒下的那刻抓到滿手空氣。他的腦袋落到輪下前,我閉上眼睛,卻還是聽見宛如香檳瓶塞噴出的啵咕聲。
是他的錯,誰叫他要低頭看手機呢。或許是因為他之前好幾次過這個路口時都平安無事吧。真是太大意了。
周遭傳來尖銳的吸氣聲,但沒人尖叫。肇事車輛副駕駛座上的乘客跳下來,在男子身旁跪下。幾個人衝上前幫忙,我退離現場。不需要多看一眼,就知道輪下的男子死定了。只要看看我自己原本雪白的襯衫,看看上頭飛濺的血跡,就知道與其叫救護車,找靈車來還比較快。
我轉身遠離事故現場,找個地方喘口氣,但號誌在這時亮起綠燈,身旁行人邁開腳步,我無法在人潮中逆流而上。經過那輛卡車旁邊時,好幾個人的視線甚至沒有離開手機。我放棄移動,停下來等人潮散去,回頭瞄向事發處,視線盡量不對上死者。卡車司機站在車尾講電話,瞪大雙眼。大概三四個人在一旁協助,還有人懷抱著獵奇心態,舉起手機錄下怵目驚心的畫面。
假如我還住在維吉尼亞州,事故肯定會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大家都會停下來幫忙,掀起恐慌,人人驚叫,新聞記者在幾分鐘內抵達。但這裡是曼哈頓,人車相撞的事故層出不窮,只是徒增不便;有些人的行程受到耽誤,有些人的衣服毀了。這種事大家都看多了,連登上報紙版面的機會都微乎其微。
使我心有芥蒂的疏離感正是我十年前搬來此處的原因。像我這種人就該住在人口稠密的都市裡,沒有人會在乎我怎麼過活。這麼大的地方,遭遇比我還可憐的人多的是。
我在這裡跟隱形人沒有兩樣。無關緊要,曼哈頓太擁擠了,對我無暇多顧,我就愛這樣的氣氛。
「妳有沒有怎樣?」
我抬起頭,一名男子扶著我的手臂,上下打量我的襯衫,評估我的傷勢,眼底滿是關切。從他的反應我知道他不是鐵石心腸的紐約客,或許他目前住在此處,無論他來自何處,那裡絕對不是個會磨盡同情心的地方。
「妳有沒有怎樣?」陌生人重複問道,直視我的雙眼。
「沒事,不是我的血。我剛好站在旁邊……」我沒有再多說什麼。我目睹那個人慘死。我離他好近,他的血噴了我一身。
為了成為隱形人而來到此地,即使我只是個軟弱的普通人,我的目標─努力變得跟腳下水泥地一般冷硬,顯然成果不太好,方才目擊的一切全都積蓄在我肚子裡。
我按住嘴巴,唇邊黏膩的觸感令我連忙縮手,又是血。我低頭盯著襯衫,這麼多血,全都不是我的。我捏著胸口的布料拉起來,但逐漸乾涸的血液把衣服黏在我皮膚上。
應該要用水洗一洗。我開始頭暈,想揉揉額頭,捏捏鼻樑,可是不敢摸自己的臉。我望向還抓著我手臂的男子。
「我臉上也沾到了嗎?」我問。
他抿唇,移開視線,掃過四周街道,伸手朝附近一間咖啡廳比畫。
「店裡一定有洗手間。」他說著,一手按住我的後腰,領我走過幾間店舖的距離。
我望向對街的潘頓出版社大樓,那是我在車禍發生前要去的地方,已經很近了,離我趕赴的會議只有十五、二十呎遠。
不知道那個被車撞死的人,離他的目的地有多近?
陌生人替我按著咖啡店門。一名女子兩手各端一杯咖啡,打算擠開我走出店外,看到我的襯衫時,她迅速退開,讓路。我走向女廁,門鎖住了,男子推開男廁的門,示意要我跟上。
他沒有鎖門,走向洗手台,轉開水龍頭。我看了鏡子一眼,幸好沒有想像的那麼糟。我臉頰上的幾滴血顏色轉深,眉毛上還有一小片血沫。算我走運,襯衫首當其衝。
男子遞上沾溼的擦手紙巾,在我擦臉時又往一疊紙巾上淋水。我終於聞到血味。刺鼻的氣息把我的心思帶回十歲那年,事隔多年,強烈的血味仍舊揮之不去。
一陣反胃襲來,我試著憋氣;我不想吐,可是想脫掉襯衫,馬上。
我抖著手解開釦子,剝掉襯衫,放在水龍頭下任由水柱沖洗,又從這個陌生人手上接過一疊溼紙巾,擦掉染上胸口的鮮血。
我上半身僅存這件最不好看的胸罩。他轉頭朝向門留給我隱私,但沒有離開洗手間,而是把我們兩人鎖在裡頭,不讓其他人撞見我半裸的模樣,如此高尚的騎士風範令我坐立不安。我看著他的鏡影,渾身僵硬。
有人敲門。
「馬上好。」他說。
我放鬆了些。在必要的時刻,我只要尖叫,外頭還是有人聽得見的。
我專心清洗,把頸子跟胸口的血跡擦掉後對著鏡子檢查頭髮,腦袋左右轉了圈,只在掉色的焦糖色髮絲間找到一吋長的黑色髮根。
「來。」男子解開自己那件筆挺白襯衫的最後一顆釦子。「給妳穿。」
他方才脫下的西裝外套掛在門把上,抖下原本扣得一絲不苟的襯衫,露出白色汗衫。他肌肉結實,長得比我高,他的襯衫會把我淹沒,不能穿成這樣去開會,但我別無選擇。我接過來,又拉了幾張乾紙巾擦乾上身,再套上襯衫,扣上釦子。看起來可笑極了,不過至少被輪胎輾爆、噴了別人一身血的不是我,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拎起浸濕的襯衫,接受它已經無法挽救的事實,丟進垃圾桶,扶著洗手台凝視自己的鏡影。兩顆疲憊、空虛的眼珠子回望著我。它們方才直擊的驚悚景象使得淺棕色虹膜轉為混濁的深棕。我用掌根揉揉臉頰,想擠出一點血色,可惜徒勞無功。我還是面如死灰。
我靠著牆面,視線離開鏡子。男子將領帶揉成一團,塞進外套口袋,端詳我好幾秒:「看不出妳是很冷靜還是嚇傻了。」
我沒被嚇傻,但也不確定自己是否冷靜,只能承認道:「我也不知道,你呢?」
「沒事。我運氣不好,看過更糟的景象。」
我歪歪腦袋,試圖解析這句意味深長的回應的言外之意。他轉頭避開我的雙眼,使得我更專心地凝視他,納悶究竟有什麼場面比人的腦袋被卡車輾爆還要驚悚,說不定他真的是土生土長的紐約客,又或者是在醫院工作。他散發出的幹練氣息往往能在掌握他人生死的人士身上嗅到。
「你是醫生嗎?」
他搖頭:「我做房地產的,以前是。」他上前朝我肩膀伸手,拂去我襯衫─他的襯衫─上的什麼東西。他收手,看著我的臉,後退一步。
他的眼睛顏色跟剛才塞進口袋的領帶一樣,帶黃的翠綠色;他面容俊秀,但不知怎地,他好像希望自己不是長得這副模樣,幾乎到了因為長相吃過虧的程度;他似乎不想獲得旁人關注,想在這座城市裡成為隱形人,就跟我一樣。
大部分的人來到紐約是為了嶄露頭角,剩下的人只想隱姓埋名。
「請問如何稱呼?」他問。
「洛玟。」
我說出自己的名字後,他停頓了一兩秒。
「傑洛米。」說完,他打開水龍頭洗手。我的視線還是放在他身上,無法克制好奇心。比剛才車禍還要糟的景象是什麼?他說以前是房地產業者,但這一行再怎麼難熬,也不該讓一個人變得如此陰沉。
「你遇上了什麼事?」我問。
他在鏡中對上我的目光:「什麼意思?」
「你說看過更糟的景象,是什麼?」
他關水擦手,轉身面對我:「妳真的想知道?」
我點頭。
把擦手紙巾丟進垃圾桶,雙手往口袋一插,他的舉止令廁所裡的氣氛更加凝重;他直視我的雙眼,但整個人有些抽離現實。「五個月前,我從湖裡撈起八歲女兒的屍體。」
我猛然吸氣,按住自己的頸子。他眉宇間挾帶的不是陰沉,那是絕望。「真是遺憾。」我低語,真的。為他的女兒感到遺憾。為自己的好奇深感歉意。
「妳呢?」他靠著檯面,一副做足準備的模樣,彷彿他一直在等待這樣的對話,等待有個人出現,讓他的悲劇顯得沒那麼悲劇。體驗過最黑暗遭遇的人總是如此,四處尋找跟他一樣的人……比他還慘的人……利用他們來讓自己好過一些。
開口前,我先吞吞口水。跟他相比,我的悲劇可說是微不足道。我想到最近的一次,
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實在是難以啟齒:「我母親上禮拜走了。」
他的反應跟我不同,沒有半點反應,是不是因為原本期待我的悲劇更可悲呢?可惜沒有,他贏了。
「她是怎麼過世的?」
「癌症。過去一年我都在家裡照顧她。」第一次對人說出這件事,感覺到手腕脈搏突突跳動,忍不住用另一手握住:「我好幾個禮拜沒出門了。」
我們凝視彼此好一會。我想多說什麼,但從沒當著陌生人的面討論如此沈重的話題,我有點想結束。這樣的對話究竟要如何發展?
話題在此打住。
他再次看著自己的鏡影,將一縷黑髮撥回原位:「我要去開會了,妳真的沒事嗎?」他在鏡中對上我的視線。
「嗯,沒事。」
「沒事?」他質問似地重複我的語尾,我的「沒事」跟他的「沒事」似乎是不同的概念。
「沒事的,」我重複:「感謝你的協助。」
我不合時宜地希望他能笑一笑,不知道他笑起來是什麼樣子。他聳聳肩,開口道:「好吧。」說完,他打開洗手間門鎖,幫我擋著門板,但我沒有邁開腳步,而是繼續盯著他,我還沒準備好面對外頭的世界。他的善意令我相當感動,想多說幾句話,找個方法報答他,比如說請他喝杯咖啡,或是找機會歸還襯衫。我不由自主地被他的無私善行吸引─這樣的善心人士現在已經很少見了。是他左手的婚戒催促我向前走,離開洗手間,走出咖啡廳,回到聚集了更多人的街道上。
救護車來了,擋住雙向車流,我走回車禍現場,心想是不是該做個筆錄什麼的。一名員警忙著抄下其他目擊者的證詞,我在旁邊等著。其他人的說詞跟我的沒有任何差異,但我還是向員警報告,並留下聯絡方式。我不確定自己的證詞能幫上多少忙,畢竟沒有看到他被撞上的那一瞬間,只是剛好近到聽見聲音罷了,近到被噴成抽象潑墨畫布。
我轉頭看到傑洛米端著一杯咖啡走出咖啡廳。他橫越馬路,專心往目的地前進。他的心思已經飛到別處,離我遠去,或許是想著他的妻子,思考回到家要如何跟她解釋自己的襯衫跑哪去了。
我從包包裡掏出手機,確認時間。距離跟柯瑞還有潘頓出版社的編輯開會還有十五分鐘空檔。少了陌生人在旁邊讓我分心,手抖得更厲害了。咖啡有用,嗎啡更絕對有幫助,然而母親上禮拜過世後,安寧照護人員已經從我家把所有的藥物跟設備收回,可惜我難受到忘記藏一點起來,不然現在就能派上用場了。
(本文為《不存在的罪人:真相與虛構的交織,迷宮中最黑暗的人性悲劇》部分書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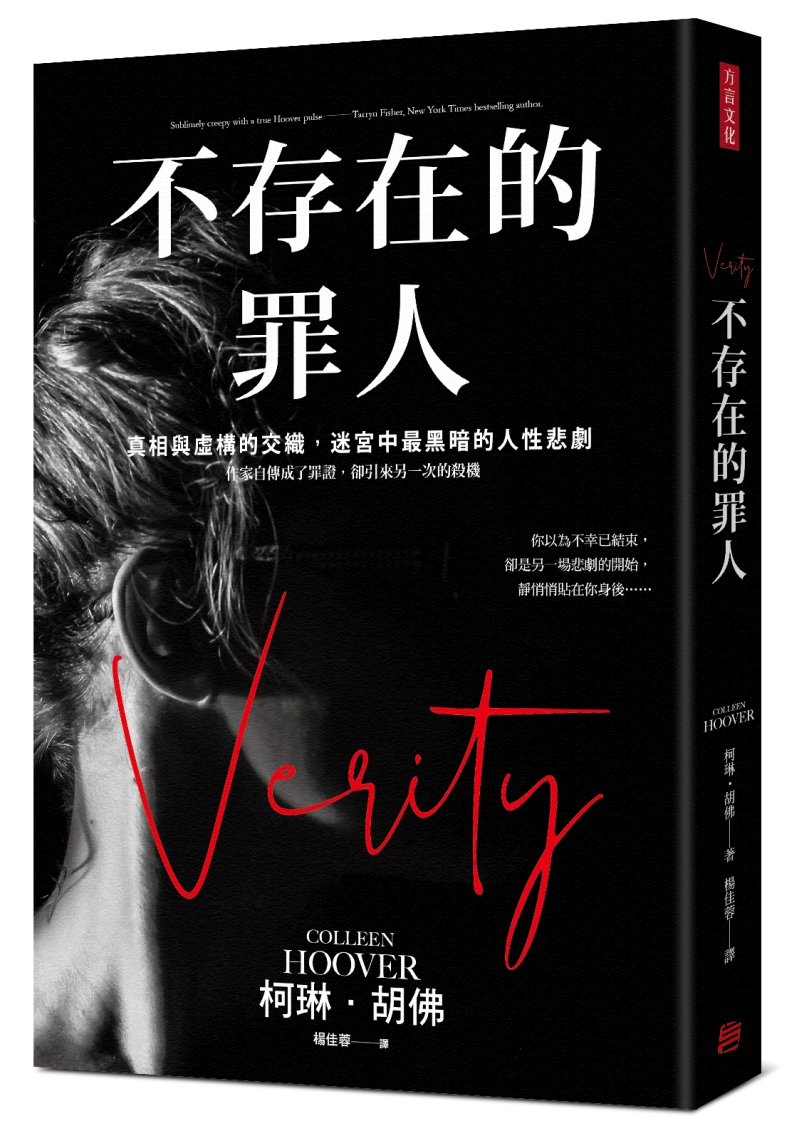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不存在的罪人:真相與虛構的交織,迷宮中最黑暗的人性悲劇》 Verity
作者:Colleen Hoover
出版:方言文化
日期:2021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