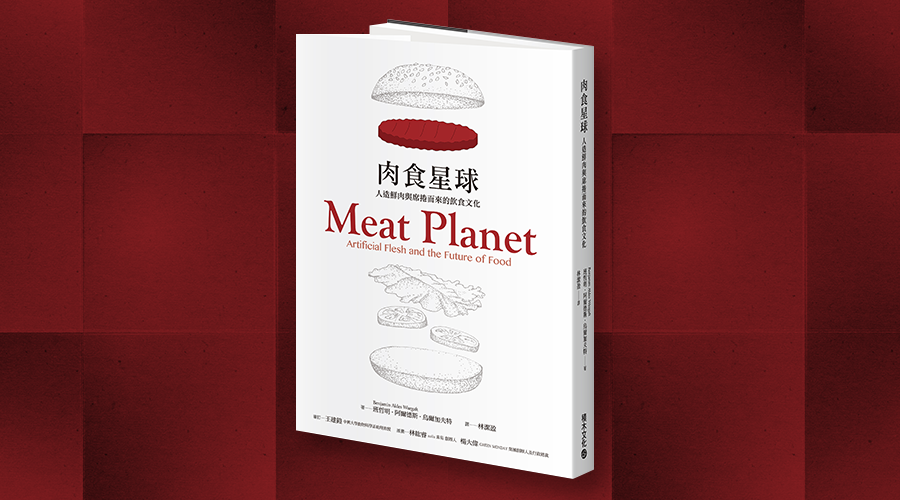
文|Benjamin Aldes Wurgaft
譯|林潔盈
蛋白質是千變萬化的。
英文中蛋白質protein一字來自希臘文的protos,有「 第一」的意思,它就如海神波賽頓(Poseidon)的長子普羅透斯(Proteus)一樣多變。當我們談到「肉類」定義的問題,以及肉類在人類飲食中的角色轉變時,這種多變性也許是我們需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因為這牽涉到很長的一段時間,可以從有紀錄的人類歷史一直往前延伸到蒙昧時期。
如果培養肉這麼熱烈地受到採用,讓人類的創造者夢想得以實現,而且它實際上也開始取代傳統的畜牧業,那麼地球上的動物生物量將在這個過程中發生變化。動物生物量中,絕大部分是由在人類食物系統中生活與死亡的馴養動物所組成。地理學家瓦克拉夫.史米爾(Vaclav Smil)估計,截至一九○○年,地球上大約有十三億大型馴養動物。到二○○○年,馴養動物的活體重量增加了約三·五倍。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史米爾想像「智慧外星訪客」得出結論,根據特定一種生物的絕對豐富度,「太陽系第三行星上的生命由牛主宰」。如果培養肉突然取代了傳統肉類,數十億群居的脊椎動物將變得不再必要,牠們前途未卜,就如用來餵養與飼養牠們的土地,以及照顧與加工所消耗的水一樣,更不用說整個行業與其從業人員了。工業化畜牧業造成的痛苦會結束,取而代之的與其說是突然的解脫,還不如說是個問號。
目前地球上直接或間接用於生產肉類、乳製品與蛋的大約75%農業用地,同樣也會變成一連串的問號。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曾將動物園稱為人獸間已然消逝之緊密關聯的墓誌銘。我們的飼養場與屠宰場,以一種非常不同的方式,同樣也是失去關係的墓誌銘,而且這種關係可能是無法挽回的。
然而,儘管培養肉確實新奇,它卻是衍生自一套更古老、早就存在的關於肉類的觀念與實踐之中。這是一組相互關聯的食肉歷史,現代西方慣於使用meat(肉)一字表示確鑿的真相、基本的事實或當前最突出的議題,如果我們認識到肉類已經發生過許多次變化,而且變化的原因有很多,此一用字習慣就顯得有些古怪。
英文單字meat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於,雖然這個字在當代的使用方式看來隨意,通常還是帶有一種穩定的意涵,然而從它的歷史來看,這個字的用法卻是不斷地改變。《牛津英語詞典》對這個字的第一個意義來自公元九○○年,即在古英語中用「meat」指稱相對於「drink」(飲品)的固體食物(我們可以在法語的肉「viande」一字觀察到類似的變化)。在古英語的拼寫中,meat原本作mete,來自原日耳曼字根mati,與同一語系的許多其他單字有關係,例如古薩克森語的meti、挪威語的matr、或哥德語中單純指稱食物的mats。大約在一三○○年,meat一字開始用來指稱動物的肉,與其他固體食物做出區別。在此之前,在一○六六年諾曼人征服英格蘭之後,取自法語和古英語的分裂術語成形,不過這對當代英語人士來說是非常熟悉的,以至於我們很少注意到它。

舉例來說,古英語描述肉的方式是meat of cow(牛的肉),法語則用boeuf或beef指稱牛肉(現代英語中羊肉mutton、小牛肉veal與豬肉pork等字全都源自法語)。華特.史考特(Walter Scott)爵士在一八二五年出版的小說《訂了婚的姑娘》對這種差異提出了解釋,認為英國人通常直接把整隻動物拿去烤,而說法語的諾曼人則多了一個層次,會把肉從屠宰的牲畜身上取下。英國人忍不住要把肉的動物特質牢記於心。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另一個與肉的定義較無關,而是與肉食性和經濟思維之間的古老關係有關的詞源學連繫:古英語中的ceap有cattle(牛、牲口)的意思,現代英語的cheap(便宜)源自於此。ceap也有「財產」之意,這讓人想起直接交換經濟,以及動物普遍用作價值單位的年代。cattle一字也與chattel(動產)有關,在過去曾用以指稱任何財產,並不僅僅是四條腿的那種。因此,二十一世紀早期的地球,從生物量的角度來看,是受到活生生的動產所支配的。
在現代的用法中,「肉」這個字幾乎沒有透露出從前作為指稱「固體食品」的術語時所具有的不確定性與彈性,不過在一些詞語中,例如nutmeat(堅果核仁)與sweetmeat(蜜餞)等詞,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那種古老意義的迴響。這個在過去意指堅實與可食性的字眼,現在意指被屠宰動物的肌肉與脂肪,不包括動物的內臟。牲畜屠宰後的內臟在英文中稱為o˜al,源自德語的ab-fall:屠宰過程中脫落的東西。現代的羅馬人將動物內臟稱為quinto quarto,直譯為「第五個四分之一」,這個稱呼來自步入現代之前的肉類分割制度,肉類會按品質分成第一到第四個四分之一,依序供應給貴族、神職人員、中產階級與軍人,剩下被剔除掉的部分歸為第五個四分之一,才給農民食用。
到底什麼是肉?
在現代歐洲與北美的歷史上,「肉」這個詞的語義轉變,與我們對這個詞越來越狹隘的理解有關,但是它過去所具有的潛在意涵,並不會因為不再使用而就此消逝。細胞培養食品計畫可能意味著回歸到肉這個字的早期意涵:任何種類的固體食物,不一定是從屍體上切下來的。至少,那些推崇「替代」蛋白質的科學家、企業家與行動主義者就非常希望能重新擴大這個字的意義——不侷限於培養肉,通常也包括植物性的肉類替代品,以及食用昆蟲。
令人驚異的是,第一塊出了名的培養肉竟然是漢堡肉。波斯特的實驗室曾考慮製作香腸,這顯然是更符合荷蘭飲食習慣的肉品形式,而且在其他歐洲國家的脈絡中,也與手工製作的概念聯繫在一起(雖然香腸與漢堡其實是親戚),儘管如此,漢堡肉所具有的國際性吸引力還是贏得勝利。對現代肉品來說,漢堡肉是非常適當的體現,它不但讓人聯想到豐盛的概念,也與工業生產、統一性、速度、靈活性等概念有關,而且也經常讓人想到汽車與得來速服務。牛肉常讓人聯想到英國,漢堡則讓人聯想到美國,而且更是美國依然豐足的象徵。專門為漢堡肉設計的麵包,讓人能在忙碌時可以用手吃這種三明治:速食肉。培養肉有許多帶有諷刺意味的點,其中之一是,即使它改變了我們對肉的看法,讓肉品變得更多樣,但相較於我們過去各種食肉方式,它仍然是建立在人類定義與消耗肉品的狹隘意識之上。
培養肉在人類食用的大部分肉品都像漢堡肉的時候問世,人類在這個時期的肉類消耗無論在動物來源或是食用形式上,都是相對同質的。培養肉是食肉歷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偏離歷史的軌跡。然而,如果退幾步來看看人類食肉行為的完整時間軸,我們只能藉由猜測過去一百年內確實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來解釋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的肉(也就是培養肉的基礎)。
這些變化有質的變化,也有量的變化,都來自工業化與城市化。它們始於十九世紀中期的英國與北美,透過從畜牧方法到冷藏車廂等新形式形體與務實基礎建設來發展,最終實現了這些基礎設施的全球化,並在過程中變得益形精細,改變了全世界的肉品。《經濟學人》雜誌使用「大麥克指數」評估麥當勞大麥克漢堡在世界各地的價格,藉此比較貨幣的購買力,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一九八六年引進大麥克指數時,漢堡這種食品已經廣為流傳,這個動作才有意義。自一九六○到二○一○年間,全球肉品消耗成長了一倍多,在一些快速發展的國家,例如中國,更是翻了好幾倍。
然而,這只是肉品現代化的最新一波浪潮,這個過程幾乎改變了關於肉類的一切,從誰吃肉到吃多少,再到他們認為什麼才算是肉等等。

誰來決定什麼是肉?
另一種提問的方法,是去看主角。當培養肉創造出來後,誰對肉的概念會進入生物反應器,誰對肉的概念會出來?在我實地考察時,幾乎所有參與創造與推廣培養肉的行為者都是西方人,其中大部分來自歐洲或北美,年齡幾乎都在六十歲以下,而且大多不到四十歲。這些人口組成細節很重要,它們影響到這些行為者認為是肉類來源的動物類型,以及他們曾接觸到的肉品類型。年紀較大的食客,可能出生在二十世紀中期肉類生產工業化的轉折之前(這種轉折建立在十九世紀的基礎上,其中許多是在北美中西部建立起來的),他們在孩童時期接觸到的肉品種類可能就不一樣。同樣地,儘管所謂的西方飲食已經全球化,非西方國家的食客對肉品在生活中的角色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培養肉計畫回應了肉類歷史上的一個特定時刻,從人類歷史的角度來看,
這個時刻恰好是獨一無二的。除了幾個明顯的例外,培養肉運動的想像性資源一直都被西方工業化世界的肉食版本所框定與限制。雖然本章的範圍很廣,貫穿了肉類的歷史,但它的重點是歐洲與北美的肉類歷史,因為這些地方發展出現代後工業化的肉食版本,而這也是目前正在全球各地蓬勃發展的肉食版本。
碰巧的是,目前已知第一塊製作出來並提供給受眾的培養肉,外觀完全不像漢堡,也與任何傳統上能刺激食慾的肉品沒有相似之處。這是二○○三年三月在法國南特(Nantes)展出的一塊青蛙細胞「肉片」,為澳洲藝術家奧隆.凱茨與艾奧娜特.祖爾創作完成的藝術作品《非具形烹飪》(Disembodied Cuisine)的一部分。這塊「蛙排」是爪蟾細胞的組織,它先用蘋果白蘭地醃製一晚,再用蜂蜜與大蒜炒熟。煎蛙腿是很有名的法國菜,但是在法國以外的西方國家很少被認為可以吃。
據說這道美食起源於中世紀,當時法國修道士設法讓教會將青蛙定義為「魚」,讓他們在教會限制他們食用陸生動物來源蛋白質的同時,能多吃一點動物性蛋白質。雖然凱茨與祖爾的明確目標是質疑公眾對生物技術的態度,他們的表演還有另一個間接效應,即質疑現代食客如何定義肉類的限制,以及這些限制如何隨著地理與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由於我們即將吃下法國有史以來第一塊以組織培養做出來的肉排,」凱茨與祖爾曾寫道:「我們決定採用蛙肉,以此表達許多法國人對改造食品的厭惡,而這種厭惡與一些非法國人對吃蛙腿這個概念的反應相似。」
他們的賭注是,一個人吃錯動物時產生的厭惡感,可能類似於一個人吃下先進生技產品的厭惡感。也許他們的暗示是,這其實是同一種厭惡感。凱茨在當地蛙肉商的攤位上貼出活動告示。他在活動結束以後曾說:「有四個人把肉吐出來了。我非常高興。」

就那些渴望對「肉」有一個生理學上精確定義的人來說,哈羅德.麥基(Harold McGee)在他那本頗具影響論的《食物與廚藝》(On Food and Cooking)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定義。正如麥基所言,肉就是肌肉,肌肉組織含有細胞或纖維構成的協調性結構,每個細胞或每根纖維都可能和一根人類的髮絲一樣細,而且充滿一條條的原纖維。48原纖維本身由在神經系統觸發收縮作用時會相互滑動的肌動蛋白與肌凝蛋白組成,這種收縮作用會縮短肌肉整體協調性結構的長度。
肌肉纖維有兩種類型:白肌纖維幫助動物快速或突然移動,紅肌纖維幫助動物在更長時間內用力。移動速度較快的動物,例如兔類動物(兔、野兔、鼠兔),往往有更多的白肌纖維。需要在較長時間內持續用力的動物,例如鯨魚,往往在需要的地方有更多的紅肌纖維。白肌纖維的燃料儲存在纖維本身的肝糖(葡萄糖的一種形式),紅肌纖維的燃料是脂肪,它含有一種能將脂肪轉化為能量的生化機制。這種機制包括細胞色素(在新陳代謝與呼吸中很重要的化合物,由與蛋白質結合的血紅素分子組成)以及肌紅素(一種能與氧和鐵結合的蛋白質),肌肉的顏色就是來自肌紅素。肌肉纖維不含脂肪,但是脂肪細胞群通常會出現在肌肉纖維與周圍結締組織之間。值得注意的是,瘦肉大約有75%的水份、20%的蛋白質與3∼5%的脂肪。脂肪能大幅增添肉的風味。肌肉周圍的結締組織(在切割肉時可以看到的銀色「薄片」)有兩個主要功能:首先,它建立起肌肉的結構;其次,它能將肌肉固定在骨頭上。在吃的時候,肌肉由哪些特定類型的細胞構成自然很重要;然而,結構也很重要。誠如麥基所言:「肉的品質——質地、顏色與味道——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肌肉纖維、結締組織與脂肪細胞的排列與相對比例。」就口感而言,肉是有「紋理」的,「我們一般都是逆紋切,如此才能順著紋理咀嚼。」
對這種將肉的定義縮減為肌肉的做法,確實存在著合理的反對意見。畢竟,這種定義源自並支持著一種文化上的特定區別,即「理想的」肉品部位與作為下水被丟棄的不理想部位。這種將肉的定義簡化為功能解剖部位的做法,忽略了肉的其他層面,例如動物吃的草會影響到脂肪的風味,從而改變肉的味道。然而,麥基的定義就培養肉而言是有用的,這既是因為它描述了肉品產業希望大量生產的肉的形式,也因為它符合科學家試圖在實驗室中生產的肉的形式。
截至寫作本文之際,肌肉結構的確切特質讓希望製造出培養肉的科學家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雖然有些形式的肉品用了絞肉,例如漢堡肉或香腸,在味道與口感上對結構的依賴性較小,不過在吃牛排時,所吃到的味道其實有賴於肉的「紋理」。當然,更複雜的結構可能很快就能實踐。培養肉利用了再生醫學(regenerative medicine)中持續發展與改進的技術,在再生醫學的領域中,科學家試圖培養出特定的功能性組織,欲用於人類醫學移植。功能性肌肉結構早已利用體外技術製作出來了。毋庸置疑的是,資金流向醫學研究比流向培養肉要快得多、多得多(就如瀑布與廚房水龍頭漏水之間的差異),但是更複雜的培養肉形式,如牛排,最終可能是再生醫學進步的間接結果。
窮人的肉
肉類的生理特質有助於醫學組織工程師對培養肉的想像,不過肉的象徵意義是多重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與其他學者在其中發現到性別,也發現了父權制;它是人類對非人類動物的權力與統治的象徵,它是自然資源受到組織與提取過程的結果,它是現代化的標誌,它是富裕的標誌,它是英雄的食物。相對地,誠如人類學家喬許.柏森(Josh Berson)所言,肉食也可能與經濟不穩定關係聯繫在一起,因為對世界各地的城市貧民來說,最便宜的肉食往往比健康食品更容易獲得。
試著再次想想漢堡:可以在車子裡吃,在工作休息時間吃,或是在街上邊走邊吃。漢堡與流動性之間的關聯始於美國戰後嬰兒潮富裕時期的漢堡攤與得來速,但是漢堡也被加以調整,以適應經濟不景氣時期不穩定生活的需求。雖然肉食觀察家對肉食與富裕之間的關係持許多不同看法,但這種關係的確切性質仍有爭議,西歐與北美的政策專家尤其對此爭論不休。現代化理論家與國際發展專家常常認為,世界各地的社會在進行「營養轉型」的過程中,肉類往往扮演著核心角色。隨著開發中國家變得越來越富裕,居民預計會購買並食用更多的肉類。關於這個現象的一個術語是「收入彈性」:對特定消耗品的需求量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雖然肉類具有收入彈性的觀點並未提出驅動人們對肉的慾望的基本機制,但基本上與認為想要吃肉是自然的、甚至是本能的這個觀念是一致的。
儘管「肉是肌肉」的定義有其吸引力,但不是所有的肉都一樣。正如人類學家黛博拉.格威茲(Deborah Gewertz)與弗雷德里克.埃靈頓(Frederick Errington)在他們的著作《廉價的肉》(Cheap Meat)中顯示的,特定的肉品部位可能具有政治意義;該書研究的是「下腹側肉」,這是紐西蘭與澳洲消費者看不上的肥羊肚肉,太平洋島民卻樂於食用。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這個部位是居民對理想生活願景的中心,不過他們可能也很清楚,更富裕的白人食客早已拒絕吃這種肉。在這個南太平洋的案例中,下腹側肉起了一種象徵性作用,捕捉到肉品在富裕與相對平行、安全與不穩定之間的轉換方式。下腹側肉還代表種族、經濟與飲食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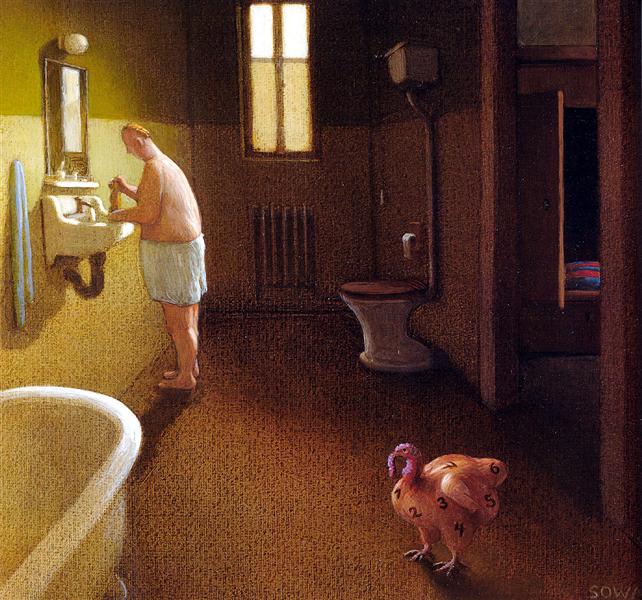
肉品的政治意義還體現在其他方面,特別是在城市化與工業化,或市場經濟邁向自由化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劇烈轉變,迫使政府對肉類的生產或分銷進行監管時。在十八世紀中葉,哲學家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與物理學家讓.勒朗.達朗貝爾(Jean Le Rond d’Alembert)的《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與工藝詳解辭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曾有這樣的說法:「屠宰肉是除了麵包以外最常見的食物。」這個說法證明了一種意識,即肉類並不是一種普通的食物,而是人類所期望的食物,如果肉類變得難以取得,可能會產生政治後果——這讓法國政府有理由確保肉類供應,讓所有階級的人都能取得。在法國、美國與其他地方,政府對於確保肉類供應與可獲得性的興趣最終還是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開始確保肉類供應適度有益健康,並藉由政府力量補貼為動物生產飼料的穀物生產者以及肉品產業本身,這樣的作為都有助於降低消費者取得肉類的成本。
食肉的天性
二○一三年波斯特漢堡演示時播放的宣傳片中,出現了一個在想像培養肉時特別關鍵的要素:人類對吃肉的渴望以及人類吃肉的行為都是天性。這就是說,人類雖然是雜食動物,卻對吃肉這件事特別有親切感,這種「對肉的渴望」,並沒有類似對穀物、蔬菜或菇菌的渴望得以相較。58這個概念往往會藉由因果關係或純粹聯想,與人類的演化聯繫起來,也就是說,肉食是人族(我們所屬物種與親緣關係最接近的已滅絕祖先所屬的演化樹的成員)可能從巧人、直立人再到智人的演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思考肉食一事,有時意味著對深層演化時間尺度的思考。它很容易就把我們引到早期人類學家所珍視的那種「不受時間影響的」語體,這些專業人士「否定同代性」(如人類學家約翰尼斯.法比安[Johannes Fabian]所言),因為對他們來說,當代的「原始」民族通常代表了歐洲人發展的過去。
在已開發世界的流行文化中,人們對肉類的喜愛自古以來根深蒂固,常常與狩獵關聯在一起。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幾年,這種說法的一個版本在「原始人飲食法」(paleo diet)中清楚可見,這種飲食法強調我們應該仿效智人祖先在舊石器時代的飲食——換言之,就是在生理上的現代人出現後、新石器革命發生前的那段時期的飲食,也就是在人類朝往農業定居的過渡期開始之前的飲食(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指由技術變革所界定的紀錄時期)。大部分原始人飲食法會要人吃下大量瘦肉,以及水果和蔬菜,飲食中包含非常少或是根本不包含精製麵粉、糖或其他工業食品。原始人飲食法的推廣者聲稱,這樣的飲食法能阻止當代文明的疾病模式,其中包括心臟病與癌症。
儘管有營養學家、人類學家、古人類學家和其他人士認為所謂的原始人飲食法並不可取,也有科學家對這種透過回歸想像中的過去讓自己變得更健康的努力嗤之以鼻,原始人飲食法仍在流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從正確的角度看,原始人飲食法與培養肉似乎可以是彼此的鏡像,兩者都是以現代工業化食品系統的「病態」為前提。前者凝視過往,在過去找到更好的肉品,以為能藉此保證當代成年人的健康,逃離麵粉與糖帶來的影響。後者著眼未來,同樣也發現了更好的肉品,將它想像成有助於環境穩定、保護非人類動物、當然也能增進人類健康之物。
(本文為《肉食星球:人造鮮肉與席捲而來的飲食文化》部分書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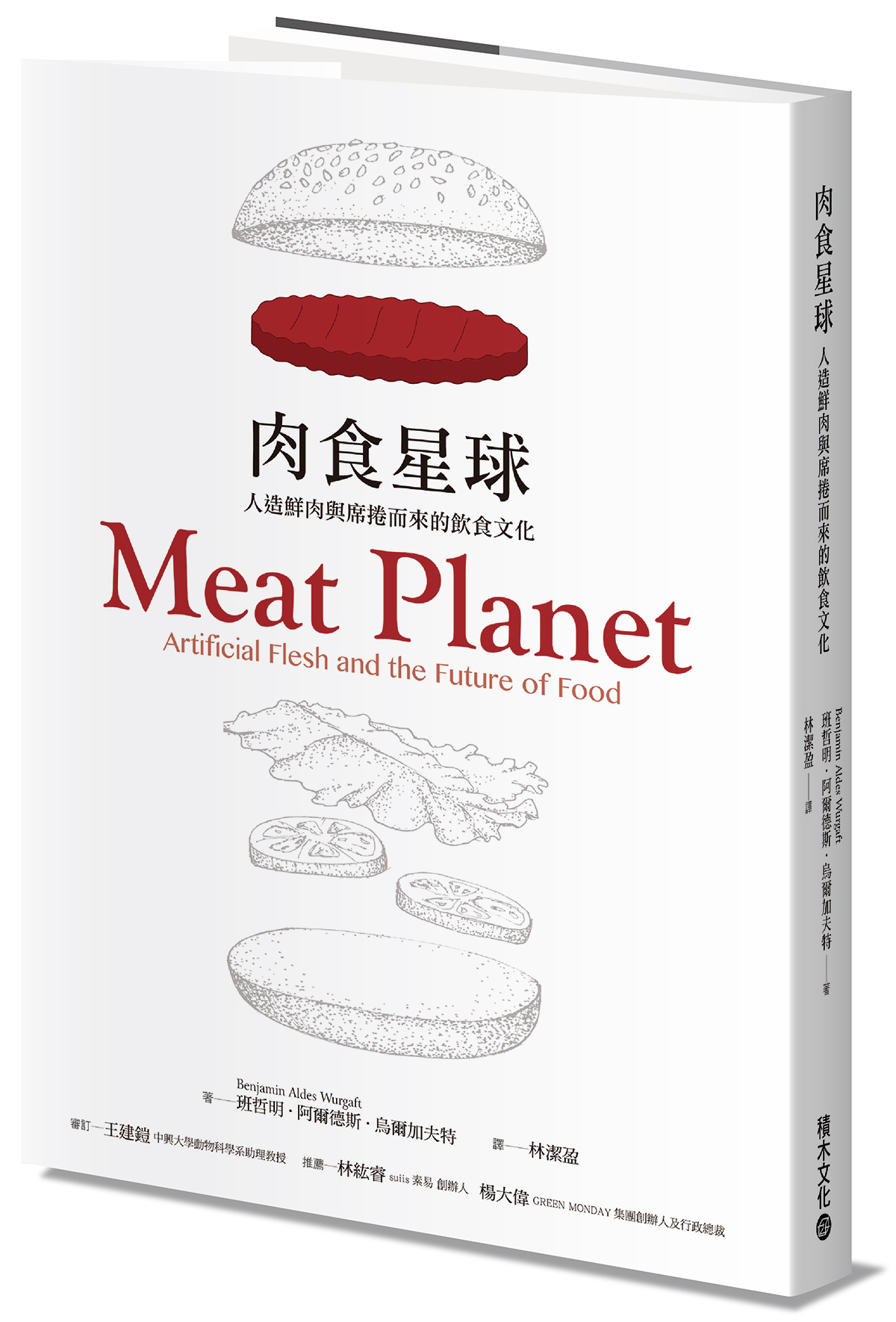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肉食星球:人造鮮肉與席捲而來的飲食文化》 Meat Planet: Artificial Flesh and the Future of Food
作者:班哲明・阿爾德斯・烏爾加夫特(Benjamin Aldes Wurgaft)
出版:積木
日期:2021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