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承認這出現在人身上、男女兩性兼具的情況。」─湯瑪斯.布朗,《通俗謬誤》(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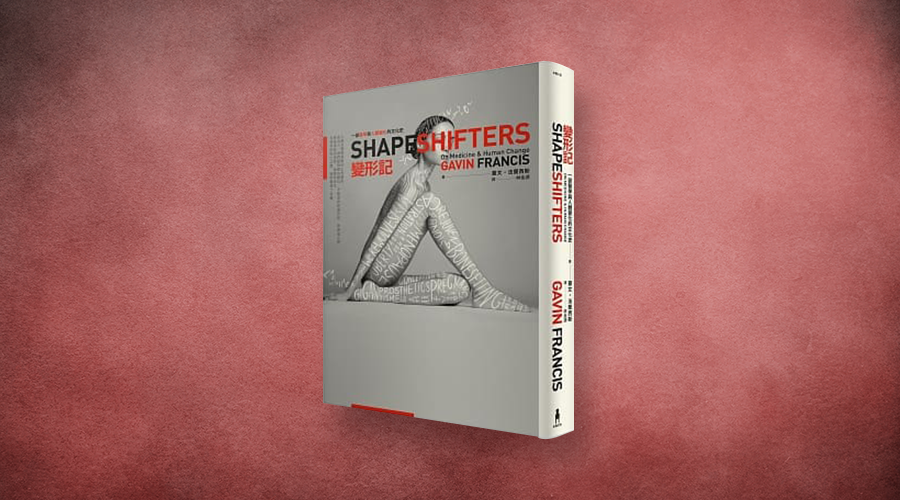
文|Gavin Francis
譯|林金源
我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就讀醫學院時,曾在愛丁堡一所維多利亞風格、名為「病童醫院」的院內接受小兒科訓練。但此後的接生訓練,可說是在公園對面短短幾步路程的現代產科醫院部門完成的。
我在那裡不得不學會如何接生,以及瞭解照料新生命在頭幾分鐘內的諸多風險。當我獲認可有資格協助接生時,下一個訓練階段就是跟著新生兒到鄰近的新生兒單位。
這裡的住院嬰兒往往患有致命的疾病,而且體重嚴重不足。不過,某天來了一個不尋常的住院者,一個重達九磅、十分健康的新生兒。這孩子出生後不久,它的父母驚叫,詢問這是男孩或女孩。
助產士倒抽一口氣:「我不知道!」這個嬰兒擁有模稜兩可的生殖器,小小的陰莖和陰道。他或她長得健壯,而且好哺育,沒有造成這種性別不明的代謝或荷爾蒙上的問題。
孩子待在醫院的唯一理由是要弄清楚,是否「她」其實是「他」,或者「他」其實是「她」。區分性別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甚至就表現在我們套在嬰兒手腕的名條上。
這個名條通常會採用粉紅或藍色色標,但上述那名新生兒戴著白色名條。孩子的父母既焦慮又困惑,當主治的新生兒學家開始談到血液檢驗、掃描和性腺切片檢查時,他們又更緊張了。
當天稍晚,我穿過公園,走回病童醫院的圖書館,在教科書裡查詢「性別分化障礙」。
「出生時,外生殖器的模稜兩可會帶給父母極大苦惱。」我讀到,「謹慎的說明至關重要。」據估計,每兩千名嬰兒中就有一個會顯現某種程度的生殖器模稜兩可,至於檢測則是「完整的診斷評估需要專家鑑定,因為必須考量到個人的長期功能性角色,以及準確的性別。」
書本繼續解釋,絕大多數生殖器模稜兩可的嬰兒可分為兩大類。雌雄間性的嬰兒結果可能基因為女性—擁有兩個X染色體,但陰蒂膨大成小陰莖的尺寸,肇因是荷爾蒙疾病,造成還在子宮內時高乎尋常的睪固酮類荷爾蒙(雄性素)濃度。
但也有基因上是男性的—擁有X與Y染色體,但其發育中的生殖器顯然對睪固酮不全然敏感,或是無法產生足量的荷爾蒙去形成身體的分化。身為人類,我們的預設形體是女性,如果XY胎兒感測不到血液中的雄性素,那麼就會發育出短而末端封閉的陰道,有陰蒂,而非陰莖。
教科書還包含第三類,亦即「真正陰陽人」—出生時具備睪丸和卵巢組織、小小的陰莖以及子宮與陰道的嬰兒。要出現陰陽人必須有極度不可能的事同時發生,而且有幾種可能的發生方式。
其中最可能的情況是,一個帶Y染色體的「男性」精子,及一個帶X染色體的「女性」精子,各使一個剛分裂的卵受精,這兩個受精卵而後又融合在一起。
「真正陰陽人」的身體組織是男性與女性細胞的棋盤式嵌合,醫學行話稱作「mosaics—鑲嵌」。鑲嵌現象在一九三○年代就已被發現,但世人直到一九五○年代後期才瞭解這種現象會導致雌雄同體。
那本教科書以清楚但冷漠的方式說道,「基因上為男性、具備能發揮作用的睪丸,但有女性化的外生殖器者,最好當作女孩來養育。」我不知道他們何以能這麼確定。
將這些血液檢驗和掃描全數進行分類需要花費幾天時間,這對父母在這期間為顧及中立,稱那孩子為Sam。名字縱使可以模稜兩可,但語言按性別區分的深刻本質,又意味沒有人能想出該使用哪個代名詞。
「它」顯得非常麻木不仁,但「他」或「她」卻可能又不正確。Sam完全不以為意,順利哺育增重。
當所有檢測結果兜合在一起,暗示了Sam 具備罕見的「真正」雌雄同體性,是男性與女性細胞的鑲嵌產生雙性的組合。
除了陰莖和陰道,Sam 也有子宮,以及一條出自左側卵巢的輸卵管,但右側是埋入的睪丸和一條輸精管,這條導管會在成年期負責將精子從睪丸輸送至尿道。
在一九九○年代的愛丁堡,大眾不太能感受到性別模糊這件事,而且似乎也未出現將Sam 當作既非男孩、也非女孩來養育—用綠色或紅色,而非用粉紅或藍色服裝來打扮—的可能性。
英語的本質似乎要求有所抉擇。「她是女生。」當我們說明檢驗結果,這孩子的母親終於下定決心,「Sam 是Samantha。」至於她的陰莖該麼辦,則有待日後決定。
她光禿的小頭立刻被以花卉圖案的頭帶裝飾,搖床邊裝滿粉紅色卡片、鑲褶邊的毯子和心形氣球。
Sam 是茁壯成長的活生生例證,證明男女性別不是只關乎X和Y染色體,然而現代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醫學,時常在性別不明與雌雄同體當中掙扎。
二十世紀大部分期間,正統醫學都堅守著我的小兒科教科書清楚闡述的界限—沒有男性生殖器(因為發展異常,或意外導致生殖器闕如)的男孩可直接當成女孩養育。但越來越被注意到的是,這樣的男孩有許多會在青春期表現出對配予自己的性別的不適感。
早期的荷爾蒙暴露似乎會影響日後身分的決定。同樣引起注意的還有,因為擴大的陰蒂而被當為男孩養育的XX嬰兒,據報告,有高度意願更想被視為女性。一項始自二○○五年的研究就估算這個比例為百分之十二,而被當作女孩養育、後來鑑定為男性的XY嬰兒,比例則為較低的百分之五。
現代醫學如今才開始設法解決性別認同流動的概念,但早在幾千年前,希臘哲學和神話就已經探索了這些概念。柏拉圖的《饗宴》就談到劇作家阿里斯多芬尼斯對於誠摯討論愛情的貢獻。
他說,最初,人的性別有三種,而非兩種:雄性、雌性和雌雄同體。每種性別的人都有四隻手、四隻腳、兩套生殖器,以及望向不同方向的兩張臉。
這些完整的男性來自太陽,完整的女性來自大地,而男性與女性器官共存的人則來自月亮。這三種力量強大的原初人類開始對諸神造成了威脅,於是,宙斯將他們一個個從中劈成兩半,「就像用一根頭髮分開一顆蛋」。
他們的數量雖然變成兩倍,但每一個都注定要不停地尋覓他或她的另一半。那些曾是雌雄同體的人成了異性戀者,雖利於生育,但有通姦的傾向。
曾是完整女性的人變成女同性戀,而完整的男性則變成男同性戀(「男孩和青年中最優秀者,因為他們最具男子氣質」)。
阿里斯多芬尼斯雖是喜劇作家,似乎也預期到他的想法會招致嘲弄。「這是我的愛的論文,」他在《饗宴》中說道,「儘管與你的不同,但我必須懇求你莫嘲諷揶揄。」
從遠古世界一直到文藝復興時期,醫學和其他著作中有大量例子都認為男人與女人並非那麼對立,而是有共通的基本特性,能彼此對換。
從亞里斯多德和蓋倫的解剖學,到湯瑪斯.布朗的推測,在科學史大部分時期裡,男女之間的性別轉換不僅被認為是可能的,而且還不時預期如此。而這種流動性是約莫在兩、三百年前,隨著啟蒙時代理性主義的逐漸僵化才消失。

另一則關於先知提瑞西阿斯的希臘神話,則證實了一種對性別彈性的著迷。孩提時的提瑞西阿斯某次在森林裡散步時,見到了交配中的蛇—這是雌雄同體的象徵與厄運的兆頭。
他沒有匆忙逃離厄運,「他擊打牠們的背部。」母蛇被殺,而提瑞西阿斯也立即變身為女人。
由於周期性地脫皮,蛇象徵著變形。換上新皮的提瑞西阿斯變成了底比斯的娼妓,後來成為人母。七年後,她再度遇見交配中的蛇,這回她擊殺公蛇,立即恢復為男性形體。
後來奧維德以一個淫猥的故事接續了這個提瑞西阿斯的故事。那故事說道,宙斯和妻子希拉在爭論男人或女人最能享受性愛。
身為古時唯一的變性人,提瑞西阿斯受召進行裁決,並作證說,性愛的愉悅若是以十分計,女人可享十分之九,而男人只享十分之一。有鑑於西方文化中大約僅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會在異性性交中達到高潮,這個奇特的故事道出的或許更是男性焦慮,而非關性的事實。
塔里克告訴我,他從小就知道自己應該生為女孩。他既非異性戀,也不是同性戀,而且不記得曾對性事感興趣。男孩時期的他喜歡芭比娃娃更勝過機動人,還曾經因為偷穿姊姊的衣服而被罵。他在外人眼中一向是性情冷靜、勤奮好學的孩子,但他對性別認同的焦慮在青春期持續累積。
後來,他成為學者,我們在三、四年前認識時,他剛開始休研究長假。隨休假而來的空閒讓他首度有機會考慮改變自己的性別認同。「你是第一個聽我說這件事的人,」他告訴我,「我沒辦法繼續過這種生活。」
打從我就讀醫學院開始,神經發展研究已有所進展,蓄積了能量,反對直接將沒有陰莖的男孩當成女孩養育的建議,反之亦然。性別分化的要素深植在大腦與荷爾蒙當中—如今無疑認為社會化只占性別認同感的一部分。
對雙胞胎的研究顯示,同卵雙胞胎不滿意出生性別的發生率高過異卵雙胞胎,這表示至少有一部分是基因因素。
其他的研究發現,導致男孩睪固酮製造量減少的染色體疾病,有可能會造成他們更想由男變女。
性別變異在不久之前仍被視為一種異常行為。一九五二年首度發行的美國精神醫學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就將性別變異列在「性別偏差」的直率標題下。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二版在一九六八年發行時仍保留同樣的分類,不過當時研究美國人性行為的《金賽報告》,已經拓寬了對於性多樣化的認識。
一九八○年的第三版手冊創造了新的「性別認同障礙」類型,也延續到一九九四年的第四版。二○一三年的第五版已將「障礙」改換為「焦慮」—暗示一種受苦、苦惱的心理狀態。
這個用語也遭到批評,因為它排除了對個人選擇採納的性別感到自在的人。目前建議適用的是「差異」這個更中性的用語。
塔里克深感焦慮,每天早上醒來,內心陡然一沉,知道自己又得面對裝成男人的另一天。他感到沮喪,睡不安穩,難以藉著一夜好眠重振精神。
他的身體令他厭惡,尤其是胸毛和鬍鬚、下巴輪廓、陰莖和陰囊。他根本無法碰觸自己的生殖器,而且覺得在黑暗中迅速清洗比較容易。
英、美兩國的醫療指導方針都要求,在進行性別重分配手術之前,受者需要完全生活在「採納的性別角色」中長達十二個月、或更久的時間。「『活在某個角色中』,我恨這種說法。」
當我們開始討論變性事宜時,塔里克這麼告訴我。
「對我來說,這就是真實的生活啊。」塔里克在當地某家性別認同診所的支持下踏出了困難的一步。
他告知自己的大學同事、父母和兄弟姊妹,開始過著當「特麗莎」的生活。提瑞西阿斯在擊殺蛇的時候變換了性別—在該診所的協助下,我利用處方藥展開一個可與提瑞西阿斯相提並論的變形,但過程緩慢許多。
第一種藥物是Finasteride,用以抑制體內最強效的睪固酮產生。這種藥是用來縮小攝護腺,而小劑量使用有助於延緩雄性禿。
Finasteride 僅有部分功效,不是十分有效的療法,幾個月後改注射Leuprorelin,起初每月施打,後來等到她的身體習慣後,再每隔三個月注射一次。
Leuprorelin 會抑制腦下垂體製造刺激生殖腺的荷爾蒙,並且讓睪丸萎縮—這可能會造成皮膚發紅、性慾暴跌,以及骨頭變弱。
在確定使用 Leuprorelin 幾週後,我們開始進行雌激素治療。雌激素會讓身體變得女性化,促進乳房發育,但有可能造成血栓及提高中風、心臟病發作和乳癌的風險。
這整個過程歷時兩年,特麗莎變性的最後階段將會是最困難的:手術移除睪丸和部分陰莖,然後利用陰莖皮膚創造端口封閉的陰道。身體的轉變分為兩階段進行,特麗莎每次術後的恢復期都需要好幾個月。
身體本身的癒合力可能會反抗它的新形體。初期,變性女子必須每天使用擴張器,讓新造的陰道保持打開的狀態,並且定時用抗菌液灌洗。部分陰囊皮膚會摺疊與縫合起來,讓該部位外貌看似陰唇。
等到特麗莎的身體傷口癒合,欣快感也就取代了她的煩躁不安。她重返大學崗位,繼續過著變性之前平靜的學術研究生活。她告訴我,現在她的學術工作表現得比先前更出色。雌激素影響的不只是身體外形和體毛分布,「我的大腦喜歡這些荷爾蒙。」
另一位變性女子在開始雌激素治療不久後這麼告訴我,「感覺就像遺失的齒輪已經回復定位。」
特麗莎對於性事或找伴侶依然興趣缺缺。她仍得面對巨大的挑戰,像是同事的揶揄和非難、父母的失望和懷疑、街頭的騷擾、必須不間斷接受荷爾蒙治療,以及與胸毛和臉毛無止境的抗戰。但她現在可以安穩入睡,醒來後也不再恐懼。
即便三十年前,要從塔里克變成特麗莎也是不太可能的,當時進行變性手術的機會遠比現在難取得,而且手術所能提供的處置也相當基本。雖然使變性成真的科學和手術是相當晚近的現象,但古典醫學的性別分化概念早就預示到了這件事。
這些概念設想男性身體的體溫高於女性身體,以及母親子宮的溫度會決定胎兒發育出男性或女性性器官。根據古希臘醫師蓋倫的說法,兩性的性器官基本上是相同的,陰囊是內外翻轉的子宮,而陰莖是凸出的陰道。
要將女人變成男人只需要加熱骨盆器官,便能「釋放」而變得外凸。這些看法就許多方面而言雖顯荒謬,但確實讓性別有了存在於某種幅度中的可能性,以及我們都懷有變形的潛力。
這種想法從古典時代持續到中世紀,直至文藝復興時期後。十六世紀法國哲學家蒙田和同時代的外科醫師帕雷(Ambroise Paré)都曾提及養豬女瑪麗的故事:她用力跳過水溝去追趕豬隻,結果發現自己的陰道「凸出」成了陰莖,讓她變成了男人。此次變形得到主教的證實,瑪麗重新受洗成為「吉爾曼」,並獲得受封為國王朝臣的榮譽。
看來吉爾曼因為他的新形體而受歡迎,因為他的轉變顯然是上帝出手干預,而非自己的抉擇。吉爾曼有可能是XY男性,他的陰莖並非突然出現,而是連月漸進發生。他可能罹患了削弱睪固酮轉換成最具效能形式的荷爾蒙疾病,因此在子宮中形成女性生殖器。
這個過程在作家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的小說《中性》(Middlesex)裡的女主角/男主角有充分的描述:青春期的荷爾蒙暴增造成陰莖和鬍鬚的發育、睪丸的下降以及嗓音變低沉。這種特殊傳遺疾病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基因封閉的社群中相對常見,罹患此病者被稱作huevedoces,意思是「十二歲長出睪丸」。
蒙田則說了另一個變性故事,關於一個名叫瑪麗的人開始過著男人的生活。瑪麗成為遠方村莊的織工,愛上一個女人,並且和她結婚,與她度過了「四、五個月〔令他妻子〕滿意的生活。」
但後來某個來自他家鄉的人認出他,並且呈報當局。當局將他當作女人進行審判,結果瑪麗被處以絞刑,罪名是「利用不正當手段彌補她的性別缺陷」。
在當時的法國社會,上帝干預是可允許的,但這個瑪麗的變性則被視為個人肆意的抉擇。
一九三一年,德國醫師菲利克斯.亞伯拉罕(Felix Abraham)發表了對某種新手術的描述,該手術由柏林的格爾班特醫師(Dr Gohrbandt)操刀,對象是兩位性別焦慮者。
第一個是身為男童時就再三嘗試切除陰莖的 Dora R。亞伯拉罕醫師描述第二位患者Toni E是「同性戀」和「異裝癖」,只有穿著女裝時才感覺自在。Toni E 在五十二歲時接受手術,亞伯拉罕還說她等到她的妻子過世後才進行。
格爾班特的「陰道成形術」涉及創造出一條穿越骨盆肌肉、從會陰上至腹部襯裡的通道。這個新腔室接著裝入海綿橡膠,覆蓋的皮膚則移植自大腿。亞伯拉罕以概述藉由手術讓變性更容易的例子結束他的案例報告:
你大可提出反對這種手術的理由,說這是某種帶著輕佻性質的昂貴手術,因為一段時間過後,病患可能會回來找醫師,提出更大的新要求。這種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我們難以決定是否要進行上述的手術,但我們不應輕忽病患,以及他們的心理狀態有可能導致患者自殘和危及性命的併發症。我們從其他案例得知,如果醫師不實現他們的願望,異裝癖者〔原文如此〕的確會嚴重自殘。
繼格爾班特簡單的陰道成形術後,直到一九五○年代,摩洛哥的喬杰.布洛(Georges Burou)醫師才開始利用反翻的陰莖皮膚來創造陰道—比較乾淨俐落,從癒合的觀點而言,是更成功的陰道成形方法。
據說一九六○、七○年代期間,有數以百計的變性女子進出布魯的診所。
「我沒有將男人變性成女人,」他在一九七三年這麼說,「我是將男性生殖器變成有女性外觀的生殖器。剩下的事全都在病人腦子裡。」
布洛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正確的。我們現在知道,腦中有一些構成荷爾蒙與情緒調節系統的構造,展現出了性別之間的差異。
來自荷蘭的驗屍研究發現,變性女子的下視丘和天生的女性一樣,都具有類似的神經元特性。該項研究並未釐清這些相似處是發生在以手術變性之前或之後(亦即是否為天生,或者是行為或荷爾蒙改變的結果)。
但不管是哪一種,在變性女子的「頭腦」中,可證明她們為女人。
關於性別、性慾和發展中的腦仍存在許多未知之事。越來越清楚的是,在子宮中有一些關鍵時刻決定了我們成長驗明為男性、女性,或是介於兩者之間,以及腦中神經元構造開始反映出這些不同狀態。
身分的表達不可否認深受個人背景與文化的影響,還有一個明顯事實也難以質疑,那便是身分的要素乃透過不同的社交互動不停改變。
未來幾年,我們將更加理解涉及性別身分表達的許多決定性因素,以及看見手術技術的進步。
許多被認為不可能的變性要素,目前也逐漸看似可以達成—子宮移植在技術上已是可行的事,二○一四年有一位接受子宮移植者完成生產。目前尚無成功接受子宮移植的變性女子,不過已有許多人表達接受手術的意願,往後數年內如果沒有案例宣布,將是出人意料的事。
身為醫師,我的任務是減輕患者痛苦和增進健康,而我對於性別重置(或者「確認」,許多變性男女偏好這個說法)的關注,主要在意它是否能減輕求診病人的苦惱,幫助他們過好自己的生活。
性別變異映照出了社會中的性別兩極化,這種兩極化斷然無情地要求我們做選擇。如今已知強迫進行這種抉擇可能會有害,而且有科學證據的背書—允許身分要素能保持流動性能讓大家都受益。
瑪姬.尼爾森(Maggie Nelson)在她的《亞哥號船員》(The Argonauts)書中引述,她的伴侶非常厭煩認為性別表達模糊者必然正在前往男女截然二分的其中一端的想法(「我沒有要去任何地方」),並且指出我們都處在不停的轉變中,而此事不分性別:「在內心中,我們是陪伴彼此歷經變形的兩個人類動物,為彼此做寬鬆的見證。換句話說,我們逐漸變老。」
有一群運動聲勢逐漸高漲的人認為,性別重置手術對他們而言可能是個錯誤—醫學專業對於荷爾蒙與手術變性所設下的核查和障礙雖然嚴苛,但對他們而言還是不夠。以女人身分生活了二十年後,伊蘭.安東尼(Elan Anthony)進行了去性別轉換(detransition),像提瑞西阿斯那樣又回頭當男人。
他稱他的旅程為「第三條變性路」。
「我無法與人形成連結,最終開始接受治療,想弄清楚為何我無法擁有關係,以及我的身體為何如此緊繃。」他在《衛報》的訪談中說道。「我終於明白,一大部分原因跟我試圖以女性形象呈現自我有關,而這對我的身體是不自然的事。」
他在男孩時期曾遭受霸凌,感覺自己處於嚴明的男性階級底層。他透過治療慢慢瞭解到,他在童年時期的女性身分認同反映的是想要逃避的無意識需求。
伊蘭面對的其中一個最大障礙,是來自變性者社群的批評,「處在目前這麼贊成變性的心理學圈子裡,身為少之又少的批評者是很辛苦的。」他說,「然而現在似乎有更多人暢談去變性轉換,也有更多臨床醫師有興趣尋找處理性別焦慮的替代方案。」
詩人艾略特(T. S. Eliot)在《荒原》中寫到困在兩種生活之間的痛苦,因此飽受折磨,卻又無法完全被其中一種接納。
對此,艾略特選擇的象徵人物是提瑞西阿斯,「在兩種生活之間跳動」。
經歷從一個性別到另一性別的轉換需要勇氣和決心,然而要在極端化的文化中占據雌雄同體的模糊空間也是如此。在自然界,占據兩個性別之間的空間不僅可能,而且普遍。
來自科學、醫學和性別流動或模糊者的證言都在在指出,提瑞西阿斯兩種人生之間的距離毋需如此巨大,而其選擇有時也毋需這般嚴峻。
(本文為《變形記:一部醫學與人體變化的文化史》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變形記:一部醫學與人體變化的文化史》 Shapeshifters: On Medicine & Human Change
作者:Gavin Francis
出版:木馬文化
日期:2020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