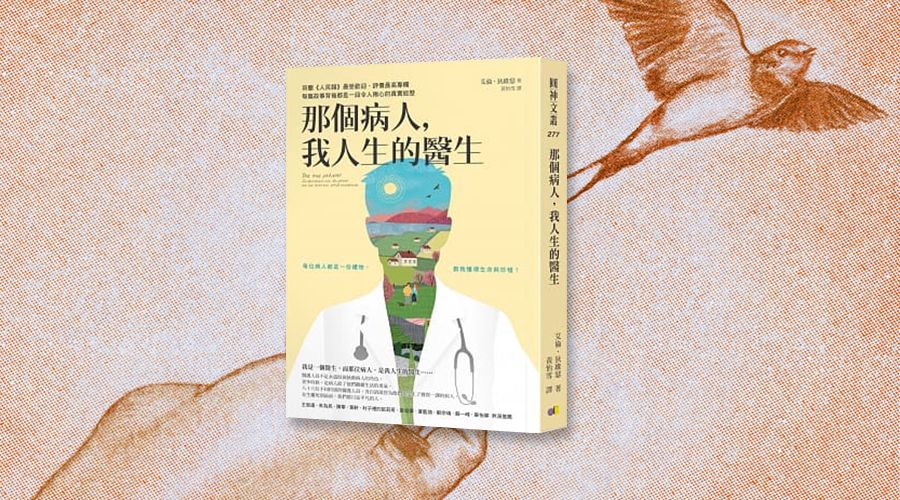
文|Ellen de Visser
譯|黃怡雪
某個星期二晚上
—漢斯.范古多弗,小兒科醫生
這世上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要決定你自己孩子的生死。
那天是星期二晚上,婦科醫生打電話要我到產房去和一對年輕夫妻談談。那位太太才剛懷孕二十五週,但孩子已經快出生了。這麼早出生的孩子情況通常很不樂觀。懷孕還不足二十四週時,治療通常是無效的,我們通常會建議等到滿二十六週再進行,但這中間的兩週就會形成灰色地帶。那天的情況也是這樣,在大半夜裡,坐在某個即將臨盆的女性床邊,她老公也陪在旁邊,我開始說明如果他們的孩子能活下來,結果可能會如何,包括產生任何缺陷或永久性損害的風險。
那對夫妻跟我說起他們的生涯規畫,他們正打算到國外工作。他們並不知道一個可能有缺陷的孩子該如何融入他們設想的藍圖,也很擔心他們的小孩可能會因此受苦。最後他們決定,等孩子出生之後,不要進行任何治療。我對這類的討論早已不陌生,我還可以說,大多數的父母都會央求我們盡一切所能,讓他們的孩子活下來。所以那對夫妻的反應讓我有點訝異,事實上這世上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要決定你自己孩子的生死,但我還是得尊重他們的意願,如同所有小兒科醫生和新生兒科醫生都曾宣誓過的。他們的孩子是個小女孩,在隔天一大早出生,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讓她盡可能不要受苦,最後她在幾個小時後過世了。
那時我心想,應該再也不會見到這對夫妻了。但是一年後,我又接到同一位婦科醫生打來的電話,又有新生兒的父母特別想跟我談談。我馬上就認出他們了:是同一對夫妻。他們告訴我,經過仔細考慮後,他們最後沒有出國。那位太太再度懷孕,而且現在又快臨盆了,才剛二十四週,還比之前早了一週。這個孩子是個男孩。
關於孩子的存活機會,我跟他們說了同一番話,但是這次他們做了不一樣的決定:希望我們盡一切所能搶救孩子的生命。但最後我們還是失敗了—小男孩還是沒能活下來。在我的執業過程中,始終忘不了關於這對夫妻的記憶。我們總會盡可能讓病人(在這個例子中是父母)參與醫療決策,這當然很重要,就像有人常說,如果人們可以決定自己的治療方法,就會選擇對他們來說最好的方式,現在我才明白這真是天大的幻想。這對夫妻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面臨如此煎熬的兩難、不斷倒數的緊迫時間,沒有朋友或家人可以幫忙。以後見之明來說,也許他們做了錯誤的選擇,後來我再看到他們的時候,還是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們的心痛。我知道自己並不被允許去改變別人的想法,因為我必須保持客觀,但是跟這對夫妻相處的經驗,卻迫使我必須更清楚地傳達訊息給病人。
當然,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那個小女孩的命運可能會如何。早產兒當中有一半的人永遠都沒辦法離開加護病房。女孩的存活率往往比男孩來得高,這點讓這個例子看來更是悲劇。如果那個星期二晚上我有站在他們的立場想,也可能會做出不同的選擇。賭看看某個新生兒會不會有機會活下來,不是很值得嗎?最後那個小女孩或許還是不會活下來,但她卻從一開始就被剝奪了努力的機會。

愛滋病
—史文.丹納,內科醫生
這件事讓我領悟到,最重要的並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它們對病人的意義。
護士要我路過去看看他,所以那天下午我毫不懷疑地就走進了他的病房,他只有一個人。幾年前他感染了後來被稱為愛滋病的新型神祕疾病,他的免疫系統崩潰了,導致眼睛和腦部產生嚴重的感染。現在他還得了皰疹和腸道感染,目前只有還在實驗中的藥物可以治療。我已經和藥商安排好了他的治療,所以他才會住進我服務的病房。
我一到他的床邊,他就問了我一個毫無預警的問題,讓我嚇了一大跳。他說現在已經很相信我了,所以他才會覺得可以自在地要求我,幫忙結束他的痛苦。他說:「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因為這個病的關係,我已經難過得快死了。」我困惑地回答他:「但是我們正打算嘗試一種新藥,可能可以消除你的腸道感染。」他要我坐下來好好看看他,他說:「我幾乎已經看不見了,也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月,就連皮膚也裂開了。如果不吃強效止痛藥我根本就撐不下去,現在我還拉肚子得很厲害,根本就沒辦法忍住,整個房間裡臭氣熏天,我再也沒辦法接受有人會來探病了。最糟糕的是,你們根本什麼也不能做。無論如何,這個病都會要了我的命,永遠都會有新的症狀、新的感染產生,甚至還可能出現癌症。每天我都得放棄生活的一小部分。」
那年頭,病人試圖對治療過程下指導棋這件事,簡直是前所未聞。我們這一行有某種嚴格的階層結構—醫生知道怎樣的治療方式對他們的病人最好。的確,我們無法對抗這種致命的新型疾病,但我們已經盡力減輕它對身體的影響,一個接著一個,而現在突然之間,卻出現了一個聰明的傢伙,不希望我繼續做想做的治療,其實他說得沒錯:我只看見眼前的樹木,卻看不到背後的森林,我一直在個別對付他身上出現的症狀,卻忽略了全貌,整體來說,他的人生變得有多絕望。我必須停止再幫他思考,我根本就不知道像他這樣的病人正在經歷的狀況。
我答應了他的請求。那是我第一次執行安樂死,他平靜而安詳地過世了。當時安樂死法還沒被引進荷蘭,所以還得進行許多繁瑣費時的手續,但是所有必須注意的規定都已經準備就緒,我也確認過它們都有被遵守。
從那時候起,我就一直致力於與病人進行有意義地討論,不再只是單向傳遞資訊,我也會深入探究他們對自己的病情有什麼感受。每當我建議一種新的治療方法,我總會一併說明好處與壞處。這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因為病人對醫生的期待是要保持中立和全面,永遠都要以對病人最有利的方式為優先。但是醫生也需要顧及自己的權益,尤其是當治療和研究重疊的時候,就像早期愛滋病剛被發現時一樣。我們會不斷測試新的方法,希望盡可能讓病人成為研究的一部分,當然也會發表研究結果—最好還是在最高等級的期刊裡。這件事幫助我永遠把這點牢記在心。
三十年過去了,這個病現在也有藥可以醫了。多虧愛滋病患者協會和網路的緣故,一般人對於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知識已經有極大的成長,因此病人的消息往往還比診所裡的家庭醫生更靈通。但是研究資料並不代表一切。現在我會把和這個病人之間的交流,這個我治療過的第一號愛滋病患,當作我的轉捩點。這件事讓我領悟到,最重要的並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它們對病人的意義。從那時候,這個重要的領悟就一直牢記在我心裡。
(本文為《那個病人,我人生的醫生》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那個病人,我人生的醫生》Die ene patiënt: Zorgverleners over de patiënt die hun leven voor altijd veranderde
作者:Ellen de Visser
出版:圓神
日期:2020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