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Peter E. Gordon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被公認為現代社會學的奠基者,與許多同時代的學者齊名,例如德國的齊梅爾(Georg Simmel)、英國的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法國的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和美國的杜波依斯(Du Bois)。韋伯在讀完《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後曾與杜波依斯通信,表達希望把這本書翻譯成德語,並提到:「我非常確信,『膚色界線』是未來時代最主要的問題,無論在這裡或是在世界各地。」
我們很難界定韋伯的學術領域,在他出版最著名的作品時「社會學」這個字還很新,而考量到他對人類思想具有深刻地影響,將他歸類在單一領域似乎也過於狹隘。他的好奇心和學習能力無窮無盡,他自信地書寫了中世紀歐洲的貿易法和印度教思想、研究了古代王權與現代官僚制度,甚至寫過一篇關於音樂社會學的論文。然而,他終其一生都害怕自己是個外行的半吊子,當同事問他為什麼把自己逼得這麼緊時,他只冷冷地回答:「我想知道自己的能耐有多少。」
在韋伯所有社會學著作中,「把工作視為個人使命」的思想不斷反覆出現,而他最知名的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核心主題正是談論一種使命感(或天職)。這本書經常被引用,但也經常被誤解,從韋伯那個時代就常有人指責他提倡「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新教促成」,但他從未說過這樣的話。
韋伯的論點要微妙許多。儘管現代資本主義最早興起於近代早期的北歐,但當時的基督宗教文化背景不同,過去對經濟活動抱持不信任態度,並把追求財富視為一種罪惡。在整個中世紀,教會也對借貸施加限制,經常把這些工作交給猶太人和外邦人,這導致了特定的刻板印象並延續到今天。就連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助長這種古老的偏見,認為金融活動等同貪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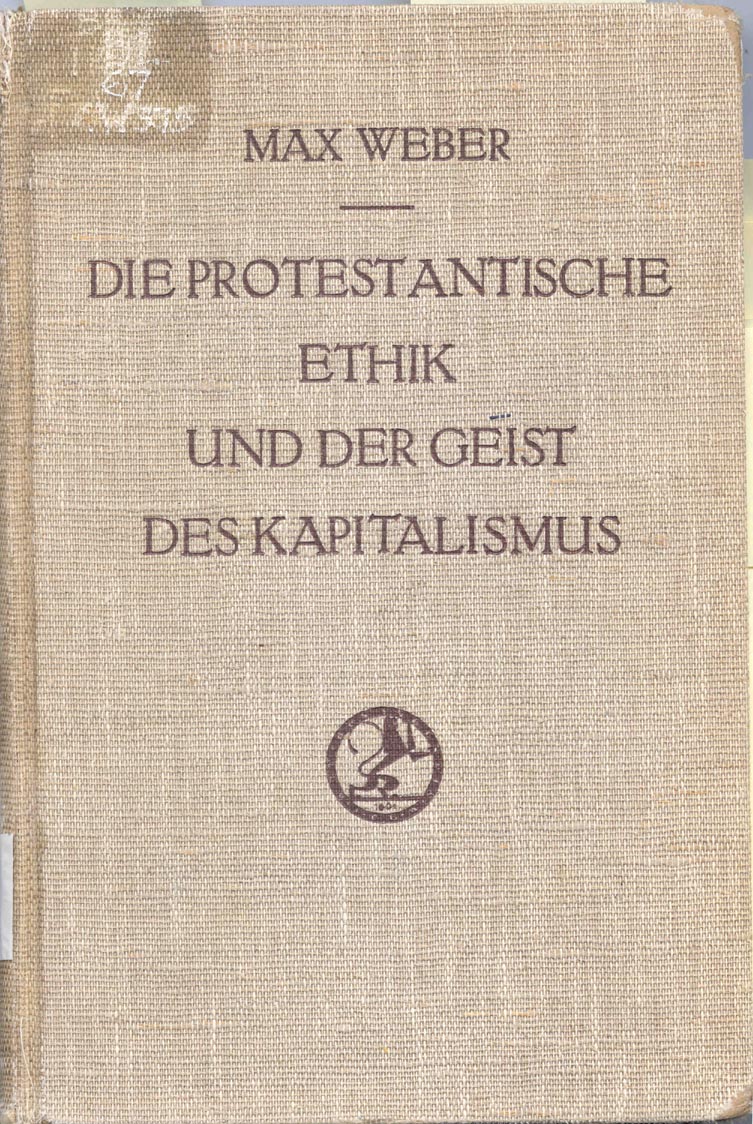
韋伯則提出了問題:在這樣的基督教信仰模式下,企業家的習性是如何形成?到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資本主義貿易是如何在歐洲蓬勃發展,使荷蘭共和國和英國及其北美殖民地繁榮壯大,並對現代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根本上的改變?韋伯的回答很有獨創性,他認為資本主義不只是一套制度或交易體系,還是一種由許多態度與傾向構成、獨一無二(也許是前所未有)的行為或文化風格。北歐國家之所以有異乎尋常的力量,部分是由於商人有條不紊的思考能力與克制精神。他們雖然掙得大量財富,但也避掉物質享樂,帶著一種責任感引領他們走向更偉大的成就。
但要如何解釋這種奇怪的行為呢?韋伯提出,資本主義的「世俗禁欲主義」可能源於新教的教義。喀爾文主義的宿命論把神的恩寵變成不可知的東西,一種賜予選民的禮物。這麼做的結果把神的主權提升到超越一切可能的高度,但對信徒來說這是心理上的重大打擊,因為人的行為被完全剝奪了意義。事實證明,官方的教義難以承受,因此喀爾文派的傳教士做出了微妙的修改:讓世俗的成功變成上帝選民的證明。
無論是路德或天主教,他們都接受天職或「呼召」的概念,也就是一個人被上帝撿選成為祭司。然而,喀爾文主義把呼召的概念應用在基督宗教過去譴責的世俗追求上。當然,撿選仍然無法確定,因為信徒無法透過工作得到救贖。但是,上帝與世界之間重新建立了一種聯繫:如果一個人以虔誠和克制的精神行事,那麼他在這個世界上的成就,或許意味著他就是上帝撿選的子民。
對韋伯來說,喀爾文派的微小改動產生了戲劇性的效果。新教允許信徒投身世俗的活動,而資本主義企業家可以看到他們的行為具有精神意義。正如韋伯指出,這種行為有一些不理性之處:它要求人們自願推遲滿足自己,自願為不確定的未來儲蓄與投資。但正是新教文化的宗教倫理為商業活動賦予了更高的意義。顯然,這個理論沒有因果關係,而是說明了一種「選擇性契合」(韋伯從歌德1809年的小說中借用的一個詞):資本主義和新教在歷史上獨立發展,但結合在一起時形成了特殊且強大的關係,共同了改變現代世界。
今天的美國人經常吹噓:美國公民是「新教工作倫理」的受益者,以此解釋美國資本主義的力量。但韋伯提出了一個更悲慘的觀點,在他看來宗教激發的工作倫理在很久以前就已消亡,成為推動理性化過程的犧牲品。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現在獨立運作,像機器那樣對所有的精神價值漠不關心,而「呼召」這個概念「就像曾經信仰的宗教信仰幽魂一樣,縈繞在我們的生活之中」。與此同時,那些被困在這個體系中的人只剩下一種盲目的衝動感,韋伯寫道:「清教徒想成為被呼召的人,換句話說,他們必須這麼做。」特別是在美國,對於財富追求已經「失去了形上學的意義」,更多是與「純粹自然的熱情」有關。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結語,韋伯將他那個時代的典型資本家描述為平庸之輩,就像被尼采稱為「最後一人」那樣發育不良的生物。在這個由沒有靈魂的人所組成的世界,不是基於個人的主動性,而是基於體系的必要性,韋伯寫道:「今天,這個強大的宇宙以壓倒性的強制力,不僅決定了那些直接參與商業活動的人的生活方式,也決定了每一個出生在這個體系中的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很可能一直這樣下去,直到消耗掉最後一噸化石燃料的那天。」
最後幾句話頗有先見之明。儘管韋伯沒有預料工業化造成的氣候變化災難與環境破壞,但他清楚知道資本主義在全球無限制擴張時,很難被視為社會或歷史進步的象徵。在記錄現代世界的崛起時,韋伯保持著冷靜的懷疑態度。社會學的目的並不是發現一般規律,而是理解人類行為的複雜性。這種對獨特性而非普遍性的強調,使韋伯的作品難以被歸類。
韋伯在關於政治的演講中對革命不屑一顧,並警告聽眾在未來十年內,他們應該會經歷一個黑暗和政治反應的時代。他認為現代國家只不過是一台機器、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龐大官僚實體,唯一的問題在於這個實體是由真正的領導者領導的民主,還是會滿足於一群平庸的政客所管理的「無領導民主政體」。
然而,一個真正的領導人必須在理想中融入現實。即使是最烏托邦的改革,如果他們想繼續掌權,最終也必須放棄自己的理想主義。韋伯宣稱,政治就像「在硬紙板上緩慢且艱難地鑽洞」。因此,那些感覺被政治「呼召」的個人必須在「個人信念的道德」與「責任的道德」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真正的領導者需要的不止是桀驁不馴的魅力,還需要懂得拿捏與掌握現實。韋伯警告說:「沒有比暴發戶(投機者)更具破壞性的政治權力腐敗了,他們四處吹噓為自己掌握的權力得意洋洋。」
1920年6月韋伯死於肺炎,死因可能是西班牙流感,他還來不及看到德國羽翼未豐的民主進展,但跡象並不樂觀。他譴責赦免暗殺巴伐利亞總理艾斯納的奧地利貴族阿爾科‧瓦利伯爵,而右翼學生舉行示威抗議反對他。儘管韋伯厭惡社會主義革命,但他更厭惡政治謀殺,他擔心如果公民對既定的法律慣例失去信心,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韋伯或許渴望有一位強大的領導者掌握歷史的車輪,但他以某種宿命論的眼光看待現代官僚國家的發展;預言和傳統的時代已經過去,不再是適合幻想的時代。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