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劃下第二支火柴時,燈芯點燃。光線鮮豔而變幻多端,帶我遠離此方世界的同時,周圍夜晚的黑暗倍增。」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塞文山脈的騎驢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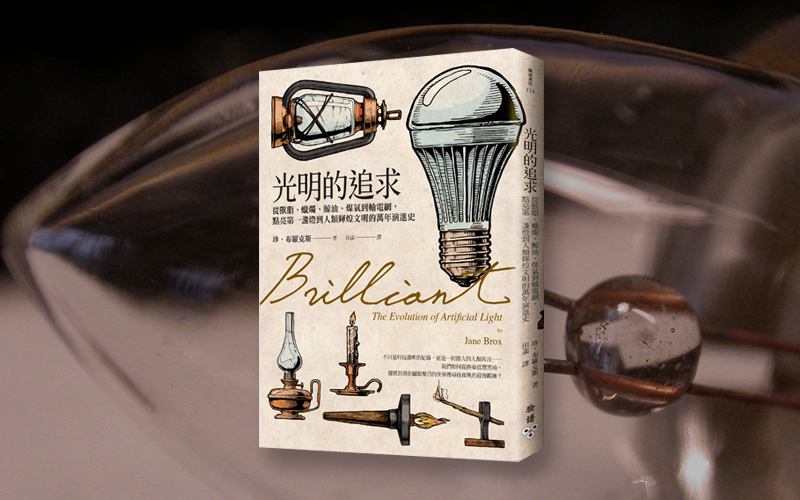
文|Jane Brox
譯|田菡
在十九世紀末,文森.梵谷在法國南部黑暗天空中看到了無窮細節。梵谷在煤氣燈的幫助之下畫出天空,他描繪了星辰和人類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星夜》(Starry Night)這幅畫中,相較於翻騰的星群和新月,亞爾村莊的燈光看起來親切而微小;而在《隆河上的星夜》(Starry Night Over the Rhône)一畫中,人類之光和星光彷彿彼此交談,一對夫婦站在畫作的底部偏中央,被亮光構成的同心圓環住,在夫婦身後遠處亞爾的路燈在河上映射出光帶,像一條條緞帶攤開在河面上。而更遠處,小鎮本身就是地平線上的亮點,不至於太亮而干擾頭頂上的星光,也不減損夜晚的龐大、有別於地上的人造光之感。星芒凸顯出的那片夜空,恰恰占據了畫布的一半。我們可以想像,梵谷那個時代的真實,是與塵世生活相對的。那是身處在夜晚的生活中,仍不忘對星星沉思、堪稱以天為家的雅趣。

對於許多人來說,光污染現在已相當普遍,妨礙了觀察夜空的機會,特別是霞光——夜空在城市、城鎮和工業區周邊映出了橙色亮光,在更高的空中會褪為紫色亮光——阻礙了我們的視野。雖然從月球、地球和宇宙塵埃中反射出來的陽光,以及通過大氣層散射的星光,都會產生一些自然的霞光,但是無處不在的家庭、商業和路燈燈光,才是霞光的大宗來源。在二十一世紀,連從空曠郊區的後院所見到的夜景,也只能少少看到幾顆昏暗的星星。已開發國家的人常見的夜空,彷彿永遠沐浴在月光的銀輝中,至少是上弦月的亮度。對於大城市的人來說,頂頭的夜空比鄉間滿月之夜前後的天空更亮。至於銀河,那橫在塵埃、星群和大氣間的星橋——奧維德(Ovid)曾形容它「擁有自己的佼佼光輝」,但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和一半歐洲人的肉眼卻看都看不到。
銀河的存在一直具有傳奇性,也有各種稱呼:「鹿躍」、「銀色河流」、「偷稻者之路」、「群鳥之途」、「白象之道」、「冬之路」、「天堂的尼羅河」……銀河在晚上引導朝聖者的路途,因此也被稱為「天河」、「聖地亞哥之道」、「羅馬之道」。但現在銀河的樣子之於人卻非常陌生,以至於當一九九四年大地震,加州洛杉磯的燈光熄滅時,「洛杉磯地區的緊急應變機構、天文台和廣播電台接到了一百通電話想詢問:是不是星星突然變亮,以及『銀色雲朵』(銀河)的出現引發了地震?」
如果你看不見銀河,應該也就分辨不出四等星。星等(magnitude)的衡量是根據地表上星星看起來的亮度來計算,最亮的星體可以是負的:天狼星為-1.5,金星是-4.5。在銀河無法現形的中度光污染的天空中,大約有三百顆二等星和三等星仍然可以見到,但所有較暗的星星——八千顆四等、五等和六等星都消失無蹤。此外,受到光污染的天空中的所有星星之於我們,都不如我們祖先所能看到的那樣明顯,因為我們生活中的人造燈光總是太過明亮,抑制了眼睛的視桿細胞:「因為夜空太亮,世界上約十分之一的人口(超過百分之四十的美國人口和六分之一的歐盟人口),不再用能夠適應夜視的眼睛來觀察天空。」

天文學家是伽利略真正的傳人,他們最深切感受到星星的消失。正是伽利略立起第一架望遠鏡、朝向夜空來觀看。他在一六一○年寫道:「當然,看到更多昔日肉眼可見的恆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絕妙的是能看到更多前所未見的星星,比我們熟知的古老星辰還多上十倍。」伽利略第一次觀星,就發現了四顆繞行木星軌道的衛星,加強了他日心宇宙(以太陽為中心的宇宙)的信念:在此我們有著細緻而優雅的論據,可以平息那些人的懷疑,因為他們的心靈即使能平靜地接受哥白尼所提出的革命性系統中的太陽,卻無法不受月亮孤伶伶繞著地球旋轉這件事而困擾……但現在我們不只有一顆星球繞著另一顆星球旋轉……還可親眼見到四顆星球環繞在木星周圍——就像月球繞地球一樣,所有的線索都描繪出一張以太陽為中心旋轉的圖像。
伽利略還觀察到,亞里斯多德所認為的完美月亮「外表卻沒有打磨得光滑,實際上到處都像地球表面一樣看起來粗糙和不平整,有巨大的隆起,也有深谷和裂隙」。而關於銀河:「在望遠鏡的幫助下,可以直接檢視銀河,所有長久以來困擾哲學家的爭議都獲得了解決,我們終於可以擺脫冗長的辯論。銀河事實上只不過是無數星團的集合體。」
在伽利略之後的幾個世紀中,隨著望遠鏡演變得更加強大和精細,愈來愈多天文學家可以看到更遠的太空,也可以看到更久遠之前的時間。他們看到了仙女座星系(Andromeda)、類星體(quasars)和黑洞。觀星的最佳位置之一是在海拔較高的加州南部,那裡的夜晚一般都很晴朗,山脈高度剛好,沒有高到讓山峰陷入在雲層或風雪中,卻能高出沿海平原密度較高的大氣層和霧氣。山峰上的空氣通常也很平靜:太平洋海流上盛行的向岸風(on-shore winds)平順地經過。這種穩定性也使星辰外觀看起來同樣很平靜,天文學家稱這樣很「好看」,因為流過地表的氣流會使光線扭曲並導致星星閃爍(地球上一般人看到的星光會閃動,但相對來說在軌道上的太空人看到的星星卻亮得很穩定)。
在加州南部山脈峰頂上所見的景況非常難得,於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這裡成為世界上一些重要天文台的所在地,第一座是建於一九○四年的威爾遜山天文台(Mount Wilson Observatory),位於洛杉磯郡聖蓋博山(San Gabriel mountains)。歷史學家羅納德.佛羅倫斯(Ronald Florence)說:「許多天文學家認為,在一個空氣寧靜、星辰清晰的美好夜晚,這可能是世界上觀察夜空的最理想的地方。」但到了一九二○年代後期,當喬治.埃勒里.海爾(George Ellery Hale)開始尋找可以建造他兩百吋望遠鏡的適當位置時,洛杉磯市區和郊區已經擴散到威爾遜山山腳,都市的燈光已經影響到黑夜中的觀測工作。因此,海爾決定將他的望遠鏡安置在離城市更遠的地方——位於有著蕨類植物植被、海拔五千六百呎的帕洛馬山(Palomar Mountain)上。帕洛馬山仍然是人們到達得了的地區,但離聖地亞哥四十五哩,距洛杉磯盆地一百哩,而根據一九三○年的人口普查,聖地亞哥的人口大概二十一萬,洛杉磯和奧蘭治的人口不到二十五萬——似乎可以避免光污染的影響。
雖然海爾和他的資助人在一九三○年已經決定好兩百吋望遠鏡的放置處,但望遠鏡的完成還需要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單單在紐約的康寧玻璃工廠(Corning glass factory)用派熱克斯玻璃(Pyrex)打造好就要花上幾年的時間,另外還要花一年的時間在退火爐(annealing oven)中慢慢冷卻,之後要以每小時二十五哩的速度乘火車穿越全國,在白天行駛,天黑後停止。離開康寧工廠的十六天後,望遠鏡抵達加州帕薩迪納(Pasadena)市的一家光學實驗室,在那裡待了十多年,讓技術人員用研磨漿料(slurries of abrasive)和紅色細粒研磨劑(polishing rouge)磨掉一萬磅的玻璃,並將鏡片塑造成拋物面。同時,工作人員改善了通往帕洛馬山頂的道路,在山上接通水電,並建造了一個半球體建築來容納海爾望遠鏡。一九四一年,日軍襲擊珍珠港,大多數參與計畫的人在戰時被徵召入伍,帕洛馬山的工事暫停了幾年。而一九四八年,望遠鏡終於被卡車載上山。雖然南加州的人口顯著增長,羅斯福新政電氣化政策也增加了家庭和街道上的照明,但帕洛馬山仍是一座從沙漠中拔地而起的遙遠山峰。牛在高山草原上吃著青草,光再亮,也無法影響到此處的天文台。
一九四九年一月,海爾望遠鏡首次亮相,著名的天文學家愛德溫.哈伯(Edwin Hubble)那時候聲稱:「兩百吋望遠鏡可以探測的空間大約是以前研究用望遠鏡的八倍……我們現在可觀察到的太空範圍已相當大,可以將其作為整個宇宙的小範圍取樣。」經過幾個月的最終調整——望遠鏡技師用手持式軟木塞拋光器和自己的拇指,拋光了鏡頭最後薄至五、六百萬分之一吋的部分——望遠鏡正式開始用來進行太空探索和研究。透過望遠鏡可辨識出星星,科學家調查它們的誕生、演進和死亡;研究了星系的運作;探尋宇宙本身的年齡。「天文學是一門漸進的科學,」佛羅倫斯寫道,「每個夜晚增加著數據;多瞥了宇宙片段幾眼;丈量了更大的範圍……在宇宙知識不斷的積累中,海爾望遠鏡功不可沒,成就了二十世紀天文學的重要歷史進展。」

但到了六○年代,光污染開始影響帕洛馬山天文台進行的暗空研究的品質——情況就如同過去五十年來世界各地的天文台受到的影響。某些地方由於光污染的緣故,幾乎難以或無法再進行暗空觀測,比如多倫多郊外的大衛.鄧拉普天文台(David Dunlap Observatory)和芝加哥郊外的葉凱士天文台(Yerkes Observatory),都轉變成歷史景點和教育中心。至於還在運作中的天文台,有相當多的天體也根本無法讓天文台的人看到。「那就像在明亮的日光下尋找筆式手電筒的小小閃光,」一位圖森(Tucson)郊外基特峰國家天文台(Kitt Peak National Observatory)的天文學家評道,「天空一增加百分之二十的亮度,代表需要多花百分之四十的時間記錄同樣微弱而遙遠的物體。同樣在操作昂貴望遠鏡的寶貴時間內,你能做到的觀察變得更少。」
有時夜晚甚至沒有足夠的黑暗時間來記錄天體。此外,水銀燈(最受歡迎的街道照明燈)不僅會遮擋星光,也影響了天文學家所拍攝的天體光譜——會把經過望遠鏡的光線分解出組成它的各色光線。天文學家大衛.科恩里奇(David Kornreich)解釋道:
當拍攝一系列像星系這樣的發光物體時,你會發現光譜並不平順,而是由多條線所組成。每條線都是有某種化學物質存在的獨特指標。透過研究這些線的強度,天文學家可以推測出觀察到的天體的化學成分和溫度……而水銀燈光在光譜的所有區段都有大量的光譜線,這些光譜線會干擾天文觀測。
到了一九八○年,當聖地亞哥的人口增長到快要兩百萬時,帕洛馬周圍的光污染已經變得非常嚴重,之後幾年天文台科學家為了阻止光害的增長,開始與周圍的城鎮合作,郡政府也試圖減少該地區不必要的照明和眩光。光污染本身可能跟現代照明一樣複雜,因為除了遍地都是個人光源,人造光種類也相當繁多——白熾燈、低壓或高壓鈉汽燈(sodium vapor)、低壓或高壓水銀燈、鹵素燈、螢光燈、LED——種類不同,影響周圍環境的方式也不同。而無論是哪種類型的燈光,每個地方的照明效果總是在變動中,因為燈的強度和光輝的清晰度會受到天氣、大氣中的灰塵和氣體,以及天空的多雲或清澈程度所影響。照明的方向和路徑也會造成不同效果,天文學家巴布.米容(Bob Mizon)寫道:「光線以小角度從水平線切往上照的路徑……會引起更多的霞光,因為光往大氣層前進的路線會經過更多的粒子和水滴,因而散射出去。」光最終照到什麼樣的物體表面也很重要,潮濕或乾燥、光滑或粗糙、暗或亮都會影響光線的反射率。
帕洛馬天文台的科學家和各級政府官員試圖制定分區照明條例來減少天文台所受到的光害。他們對裝飾性燈光(比如廣告看板燈和戶外銷售區域的照明)規定了嚴格的遮擋要求,人造光得朝下照射。他們還訂立晚上十一點過後禁止非必要照明,並規定在天文台半徑十五哩範圍內禁止裝飾性照明。加州河濱郡(Riverside county)還用更高效的鈉汽燈取代了原本的水銀燈路燈,因為鈉汽燈不會干擾天體的光譜。
而即使傾南加州官方和民間之力,試圖要控制光污染,帕洛馬天文台的觀測視野還是逐漸受到光害影響。來自鄰近城市的水銀燈光已經太過燦爛耀眼,天文學家再也無法觀察到天體某些區段的光譜。一位天文學家在一九九九年指出:「當我們透過山脈間的空隙就可以直接看到城市的燈光,代表城市的光線甚至未經天空反射就直接射入了望遠鏡。許多觀測人員已經放棄了對西南方天空的觀察,因為這個方位的光污染已經太過嚴重。」
理查德.普雷斯頓(Richard Preston)指出,光污染模糊了我們對外太空的理解,也等於模糊了我們對時間的理解,因為望向遠方「相當於望向過去的時間」:
宇宙正如我們所見,可以想像成一層層以地球為中心的同心圓,也是一層層倒回去的時間。最接近地球的這層包含著與我們時間和空間最接近的星系影像。較遠處的是較遙遠星系(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之前才存在的星系)圖像。更遠的是早期宇宙的那層,從那裡到達望遠鏡鏡頭的光子幾乎和宇宙本身一樣古老。類星體則是明亮的極小光點,看起來環繞著地球四面,閃耀著來自遠古時期的時間。在類星體之外,可觀測的宇宙有一道水平線盡頭,可以想像為最外層的內壁,水平線是我們回望過去時間的極限,也代表著初始時期的影像。
雖然第一個被送上太空的哈伯太空望遠鏡(Hubble Space Telescope)位置已凌駕於大氣層造成的扭曲和光污染影響之上,傳回地球的圖像比之前的觀測都來得清晰和深入,但太空望遠鏡非常昂貴且不穩定,不能完全取代人類在地表上對暗天的觀察和思考——無論是在條件難得的帕洛馬山,科學家人數過多,只好在排隊等待使用望遠鏡前,打發時間玩撞球的景況;或是業餘天文學家在偏遠牧場以木頭和鏡子自製成的望遠鏡細數星辰;還是在農莊的後門某個孩子的舉頭仰望。
也或許,目前已失去的夜空蘊含的意莪,比我們所能知道的還有著更深遠的影響。「於是人類誕生,」奧維德在《變形記》(Metamorphoses)中寫道:
無論人類是來自更善美的世界的造物主所播下的天賜種子;或者是方從至高天孕育出的新生大地中,取來含有天空殘餘的碎片;普羅米修斯將之與雨水混合,以全能神的形象塑造出人類,當其他動物匍匐在地,普羅米修斯給人上仰的面孔,令他們保持直立,朝向天際,仰望星辰。因此,先前未經雕琢且無形的土地,賦予了人類前所未有的形象。
(本文為《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點亮第一盞燈到人類輝煌文明的萬年演進史》部分書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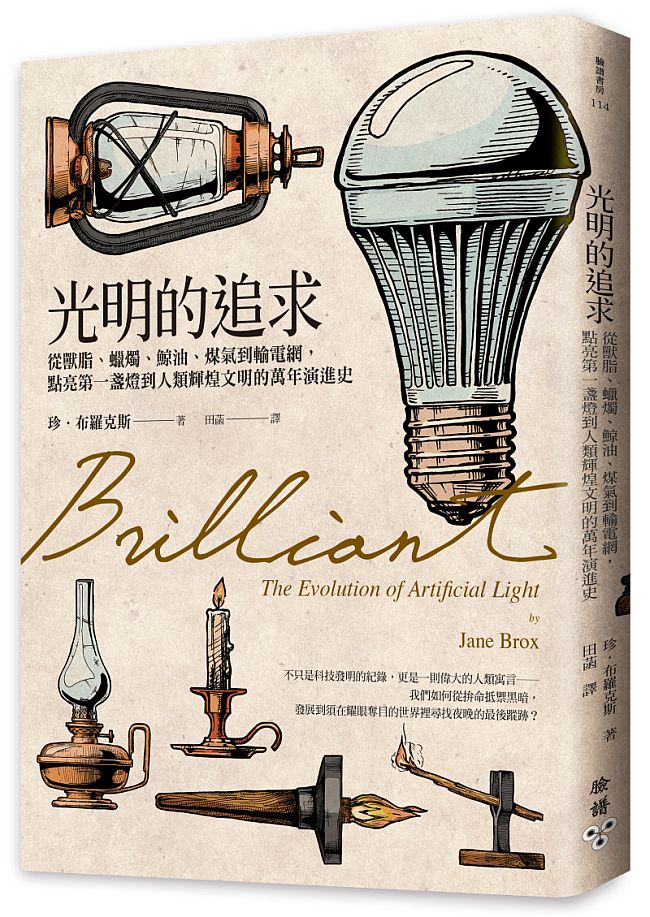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光明的追求: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點亮第一盞燈到人類輝煌文明的萬年演進史》 Brilliant: The Evolution of Artificial Light
作者:Jane Brox
譯者:田菡
出版:臉譜
日期:2020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