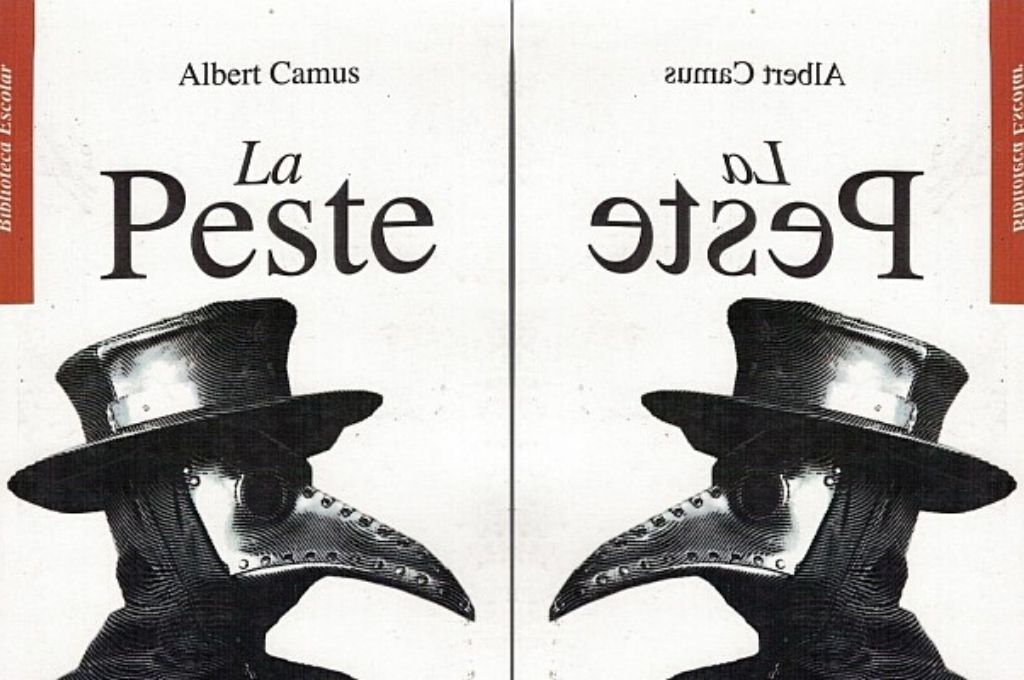
疫災裡重讀卡繆的《鼠疫》(1947)與《異鄉人》(1942),小說與現實的情境兩相對照,虛構的荒謬黯然淡了下去。非常時期所見的種種,一再刷新我們對於人情事理的認知,現實的荒謬不知搧了我們幾記耳光。
卡繆的《鼠疫》於1942年開始書寫,是部寓言小說,位列在作家所稱「反抗系列」中。而反抗的對象,小說表層為鼠疫,真正的指向則是一切惡。此之謂「瘟疫作為隱喻」。小說結構佈局平實,語言清晰直接。主角/敘事者是站在前線的醫師李厄,其以誠實的見證人自居,輔以訪客塔盧的筆記,為讀者記錄疫災下的城市奧蘭。除了市民態度的階段轉變,數名主要人物面對鼠疫的抉擇,是故事的重點。
塔盧發起衛生工作隊、熱衷寫作的公務員葛朗加入協助、外地記者藍柏亟欲逃出城外,教士潘尼祿則認為疫病是「罪有應得的懲罰」⋯⋯疫災帶來封鎖、消沈、發狂、死亡、失語、淡漠,卡繆既提出警醒,也始終堅持「同情」與「理解」,堅持即使在放逐與分離之下,「人類值得讚美的地方比應受鄙夷的地方更多」。今日人們再讀《鼠疫》,我想最重要的價值便在於這點體認。
創作時間更早的《異鄉人》,也譯作《局外人》,凸出的是事不關己的、自外於自身生命的旁觀者身分。這個翻譯也好,但我更喜歡《異鄉人》,似將隔岸的、旁觀的、冷靜、陌生、淡漠、荒謬等概念更完整地包覆起來了。
小說故事分兩部,第一部鋪陳母親的喪禮、同事及女友、常去的餐廳、鄰居與狗。平淡日子裡,還有愉悅的海灘跟陽光。但陽光似乎太灼熱,以至於當審判長要求莫梭(Meursault)說明犯罪動機時,他衝口而出──「那全是太陽惹的禍」。
《局外人》之名令人聯想薩特說的「他人即地獄」,「局外人」也可以是你生命的統治者。因為人人天生有眼,每個人都是觀看者,也註定曝露在他人目光之下。而目光或眼神裡滿溢歧義。放到今天更是如此,也許我們都有被觀看的渴望,所以有「注目禮」這種東西。然而當需要喘息時,竟不被放過。
眼光充斥的人際裡,咒詛般實現了「人生舞台」四字。舞台上,人人都是扯線公仔,表演你被分派的角色。上頭好戲連台,舞台下自然就有觀眾。法院裡的陪審員、旁聽席上的人們難道不是觀眾嗎?話語遭到剝奪的莫梭,只能放任他人的詮釋累加在自身頭上,雖生猶死。
第一部在槍聲裡落幕,第二部寫莫梭的審訊。第一次開庭前需先「候場」,警察輕鬆遞菸問會不會「怯場」,這段描述充滿了表演性。莫梭是怎麼回的呢──「我答說不會,不僅不會,反而對親眼目睹案件受審的過程很感興趣。我一生中還沒有這樣的機會。」而這場審判攸關生死──莫梭自身的生死。莫梭這句話很有意思,可以說是他一以貫之的態度,常常是自己的旁觀者。而因為擺脫一己的視角,因此思考上也總是冷靜、淡定,甚至超然。
這樣的人,不被理解,不被接受。最荒謬的部分在於審訊過程,作為被告、當事人的莫梭,沒有太多發表意見的機會。他不斷被代言、被詮釋。檢察官「深入」探討到他的靈魂,生活中的大小事件被列為審判的要件,例如母親喪禮上的情緒反應、對鄰人的幫助等等。而世上本沒有所謂「客觀檢視」。因為你「異於常人」,因此在常見的、一般的詮釋下,你就大逆不道、十惡不赦起來了。檢察官是個優秀的「說故事的人」,被告莫梭在他口中「沒有一點人性」,只有一顆「欠缺一切普世價值的匱乏心靈」。這裡讓人想起《鼠疫》裡的一段話,正適合作為檢察官、陪審員實為「殺人者」的說明:
「世上的惡幾乎都來自於無知,而善意假如未加以闡明,也可能和惡行一樣造成重大傷害。人性其實是善多於惡,但問題不在於此,而是人們有或多或少的無知,這才是我們所謂的善與惡,至於最無可救藥的惡則是無知到自以為無所不知並自認為有權力殺人。殺人者的靈魂是盲目的,假如未能盡可能地洞澈,就沒有真正的善也沒有美好的愛。」──《鼠疫》,頁119。
他們自以為能簡單斷定一人的善惡,憑藉制度賦予的權力,附會他們自身的信念,殺人於自以為正義。這令人顫慄的描寫,不妨與現實對讀、不妨作為自我警醒。小說裡的群眾厭惡、唾棄莫梭,或許有人憐憫他,然而在「理解」之前,種種情緒可能是多餘的。

莫梭固然常站在旁觀位置看待自己,卻也在是次審判中,被動地騰空位置,從主角席位驅離到觀眾席上,如他所說──觀看一場審判。啞然旁觀辯護律師、審判長、檢察官、陪審員,仲裁他的生命。我們在這裡看見,或許生活裡種種習以為常、社會人情的皺褶之間,就是荒謬與它們的產地。
莫梭殺了人,罪與罰的斟酌,必須被討論。那麼,至為龐大又無孔不入的成/偏見,難道只因為行之有年,或佔到了「大多數」的便宜,就可以對它「恆久忍耐有恩慈」嗎?再回到小說。無論是《鼠疫》或《異鄉人》,都有讓人沈吟再三的宗教人物/情節。獄裡的莫梭拒見牧師,更不願稱對方「神父」,而我認為作者在竭力批判之餘,不能說沒有猶豫。
「我本想要他別再追根究柢,告訴他這一點其實不怎麼重要,但他打斷我,站直了身子問我信不信上帝。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憤概地坐回椅子上,對我說這是不可能的,每個人都相信上帝的存在,即使是那些背棄祂的人。這是他的信念,如果有天他對此產生了疑慮,那他的人生將失去意義。『您想要讓我的人生失去意義嗎?』他叫道。在我看來這與我無關,我也照實告訴他。話才說完,他已經把耶穌推到我眼前,有些失去理智地對我喊道:『我是個基督徒,我請求祂原諒你所犯的過錯。你怎能不信祂曾為你受難?』我明白他對我不再以禮相待,不過我也受夠了。」──《異鄉人》,頁83-84。
這一段引文是莫梭與預審法官的對話。預審法官似乎認為宗教是眾人之事,而我以為政治才是。隱喻地讀,人的「信念」到底是自己的,還是必須與人合夥、以便眾志成城的呢?如果你所相信的事物、觀念不被認可,你是否也感到被冒犯或失去方向?
小說以第一人稱寫下,主角莫梭就是敘述者「我」,方便讀者接近莫梭、共情莫梭。這個主動與被動成為旁觀者、局外人的「我」,矯情地說,某些時刻也疊影著真實讀者的「我」。比起《鼠疫》,我更喜歡《異鄉人》。《鼠疫》有他急著要說的信念,有時道理的講述(telling)淹沒了展示(showing),感染力的強度不及《異鄉人》。也許因為反抗是急迫的,只能當機立斷;而荒謬的揭露則需要一幕一幕攤開,給你看。
與荒謬短兵相接令人疲憊至極,然而看見荒謬並為之命名,是我們拒絕成為齒輪的首要策略。結尾以《鼠疫》這段描寫作結。相對現實,書裡所述僅能稱為輕描淡寫:
「報紙理所當然會遵守上級的命令,不計一切代價地保持樂觀。根據報載,眼下情勢的最大特色就是居民所表現出來『沉著冷靜的感人典範』。不過在一座封閉的城市裡不會有永遠的祕密,因此對於所謂的『典範』,大家都心知肚明。若想確切了解報上所說的沉著冷靜,只要進入政府籌組的檢疫單位或隔離營就行了。」──《鼠疫》,頁200。
我想,所有被奉為典範的,被牌匾化的,是不是都是一種扭曲、壓榨甚至殘害。把不要的邊邊角角,裡頭的矛盾狼狽都像渣滓那樣榨出來,丟到檯面下的廢料收集箱。但那都是所有平扁的標籤或光環、被迫裱框封固起來的形象背後最真實的內容。這很非人。要大眾用推崇讚美來築牆,層層深鎖無法遁逃。如此才方便當局使用。活生生的人所具有的情緒與思慮,全都被消失。比起抽象的所謂數據,我們應當看見並且尊重的,是一個具體的人。這也是《鼠疫》或說卡繆所堅持的。
文中引用書籍,出處如下:
① 卡繆(Albert Camus)著,張一喬譯:《異鄉人》(L'Étranger)(臺北:麥田出版,2009年9月)。
② 卡繆(Albert Camus)著,顏湘如譯:《鼠疫》(La Peste)(臺北:麥田出版,2012年4月)。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