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放任自己被恐懼淹沒,連心煩意亂的權利都沒有。
病理學家這一行沒有驚慌的容身之處。
我們必須抽離情緒,探求真相。
為了替這個社會效命,我們有時候得要凍結某些部分的人性。
──理查.薛賀德,英國傳奇法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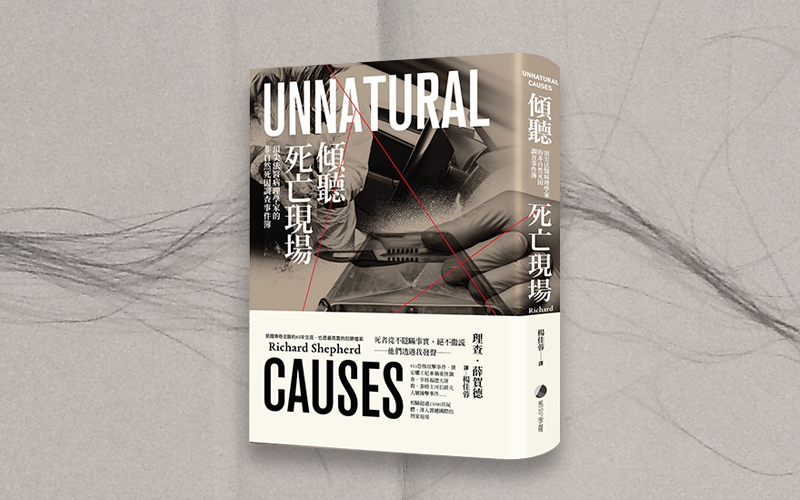
文|理查.薛賀德(Richard Shepherd)
譯|楊佳蓉
在烤箱預熱的空檔,我拿好幾把刀子輪流從不同角度捅進星期日午餐要吃的牛排,被家人逮個正著。那又怎樣?我可以從傷口推測兇刀的尺寸和形狀,與人體質感最類似的肉塊莫過於牛肩。反正烤箱還沒熱好,我有什麼理由不做點小實驗呢?
「爸爸,你的意思是你把我們的午餐當成人類?」安娜放下刀叉。「被殺掉的人?」
「說什麼呢,這當然不是人肉啊。」我爽快地切開牛排。
「你們看!我的肉上面都是刀痕。」克里斯補上一句。
還以為能得到家中另一名雄性生物的支持。我隔著餐桌狠狠瞪著他,可惜為時已晚,大家都放下了手中餐具。
我們忙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我每天傍晚拼命準時回家,從保母手中接下孩子,煮晚餐給大家吃。現在珍忙著去醫院實習。根本沒空搞什麼家庭工作日誌,每個禮拜能騰出一點時間討論就很了不起了。
某天我們出門時,屋子起火了,沒到夷為平地的程度,但我們不搬家不行。起火原因不是電線走火,或是某個激進的被告縱火,因為我提出對他不利的證據(警方懷疑是如此),不然就是我的錯。我們一直沒有找到真相,可是珍偏好第三個選項。
我們到朋友家暫住、到外面租屋;我們吵著要找哪裡的工班,究竟是要賣掉燒了一半的空殼重新購屋,還是原地重建。我努力不去直視燒毀的屋子,它的結構還在,只是內部裝潢燒得焦黑,沒剩多少家當,猶如我們婚姻的縮影。即便我能理解輾轉搬遷的困境與壓力,婚姻並沒有因此改善。
假期是天大的恩典。把孩子跟狗兒塞進車裡,緩緩往北開去。我們抵達曼島,岳父母已經準備好豐盛的食物、愛、派對、到海邊玩耍用的毛巾、替孩子舉辦的下午茶會、晚間的威士忌汽水。奧斯丁跟梅姬恰似漫畫戲劇中迷人又誇張的角色,他熱愛享樂,她的衣櫃裡塞滿了浮誇的衣裙。這對夫妻結交的朋友可以把這棟屋子擠爆,說不定連這座島都容納不下。
珍跟我在度假期間暫時休戰,她和善的雙親分擔了我們的負荷,使得我倆之間的緊繃氣氛煙消雲散。我只被梅姬逮到一次拿她的菜刀插進牛排肉裡,她沒有發火,只覺得好奇。在假期的尾聲,我們煥然一新,曬黑的孩子坐在後座,一桶又一桶貝殼塞在夾腳拖鞋堆中,狗兒甩著沾滿沙子的尾巴。回到倫敦的我們跟放假前咬牙切齒的模樣大不相同。
我們大概花了兩天恢復原樣。還沒披回忙碌的家長和醫生的外皮,那些張力已經捲土重來。我們不再大吵大鬧,各自默默地生悶氣,原因我已經記不得了。或許是出自補償心態吧,我送給珍一套新禮服和歌劇《托斯卡》的戲票。我真的很想看這一部戲,相信今晚會過得很愉快,因為某個同事形容《托斯卡》是「美妙的鑑識歌劇」。
以我們的標準來看,這一晚可說是無比奢華,值得期待。唯一的老鼠屎是我必須待命,還無法跟別人換班。好啦,保母已經抵達,我們在臥室裡準備出門,這時電話響了,珍盯著我接起。
「是我,潘。」沒有半句廢話、多餘情緒的潘,負責掌控我們這盤散沙的潘。她打來只為了一件事。珍凝視著我的臉,瞇細雙眼。
「好。」潘習慣如此開頭。「有個案子要你到現場。很驚悚的案子。全家人在床鋪上遭到射殺,案發時間大概是昨晚,不過到今天下午才被人發現。父親勉強撿回小命。正在醫院搶救。」
聽起來我該立刻趕到現場去。我的表情一定是說明了一切,珍看到了,轉過身。可愛的新衣還掛在牆上,她沒有拿起禮服準備穿上,而是傷心地打開櫃子,要把它收起。
「在哪?」我問。
「我再跟你說,不過你今晚不用過去。」
我倒抽一口氣。我總是以最快速度趕赴現場。
「你買新衣服跟戲票給珍,不可能現在突然取消一切。」
潘什麼都知道。
「可是──」
「現在你衝去兇殺案現場的話,她這輩子不會再跟你說半句話!案子不急。」
這句話能讓任何一名鑑識病理學家心臟狂跳。跟警方辦案效率、家屬的需求不同,我們飛奔前往犯罪現場是為了屍體的新鮮度,體溫下降、肌肉僵硬的程度越輕微,我們就越能推測出準確的死亡時段。
我說:「潘,我現在就過去吧,因為──」
「我已經說了,你今晚不用過去。如果你擔心的是死亡時間,不用多想,警方早就知道了。父親留下遺書,也有鄰居在凌晨一點左右聽到砰砰聲響。總之是昨晚的事情,警方今天下午開始調查。有三具屍體要處理,還有一堆大小事,你明天再去就好了。」
「可是──」
「死者不會亂跑,父親在醫院裡,時間不是問題。」
時間就是問題!
「明天早上八點過去就好,已經安排好了。」
「可是──」
「理查。你想跟我吵嗎?」
不想。沒有人敢反駁潘。
於是我們出門看歌劇,珍穿上那套禮服,和我度過愉快的夜晚,只是死在床上的那一家人陪著我們鑽進戲院。我努力不去想他們,卻還是無法控制。該從那一具屍體開始?父親的傷勢有多重?他是殺了家人然後打算自殺,卻在最後一刻手軟?還是說子彈威力不足?會不會是某個蒙面瘋子逼他射殺妻小、寫下遺書──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父親能逃過一劫?
我沒有直接前往現場,但顯然珍看穿了我一心只想著工作,是潘阻止了我。離開戲院時,珍幾乎不發一語。我們回到家,等到保母告辭,這才開始吵。嗯,是珍單方面的對我吼叫。面對她的憤怒,我變得非常、非常安靜,像是縮在巢穴裡、等待盤旋的老鷹離開的小動物。不知道為什麼,我似乎是毀了這個美好的夜晚。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你每次都閉嘴生悶氣!我心情不好!你為什麼不能有點表示?安慰我一下?」
呃。因為……
「理查,所以你才選擇跟屍體為伍嗎?」
等等。
「因為它們不會注意到你完全跟它們切割開來嗎?」
說得好!
只要狀況不妙,我就能在瞬間抽離情緒,珍認為這是因為我母親早逝,但我懷疑真正的原因是我父親的火爆性子。他創造了充滿愛情的安穩世界,我完全依賴著他生存。然而這個世界不斷被他爆發的情緒摧折。長期下來導致我幾乎無法允許自己釋放情緒。
當然了,有時候我還是能感受到憤怒、悲傷、失望,只是我不會展現出來,而是躲進沉默的殼裡。我極少與人爭辯,從沒大吼大叫過。好吧,大概在那陣子有過一次。多年後,我女兒在她的婚禮上說她只看過我失控一次(新西裝、小鬼頭、洗澡、水槍)。我不覺得過意不去。事實上,我很高興自己還是有失控的時刻。
浪漫的歌劇之夜不如我預想的成功,因此我思考是否該直接前往命案現場,不過看了珍一眼,我從她的表情判斷此舉極有可能導致離婚,於是我忍住衝動。可是呢,隔天星期六早上我六點半就醒了,準備就緒,出門去驗屍。珍沒有起床,至少看起來還沒醒。
我照著潘的指示在八點抵達現場,這天想必會非常漫長。那間屋子裡外還有許多員警忙得團團轉,但意外的沒看到幾個記者。或許他們已經採訪完離開了。如此聳動的命案──死者還不只一人──絕對會登上媒體版面。根據我的經驗,對記者來說,案情越是駭人聽聞就越有看頭。就算到了今日,開膛手傑克的惡行仍舊有辦法成為頭條新聞。只是某些姦殺案件的細節似乎會模糊一些──與尊重死者無關,單純只是因為情報被壓下來了。
踏入案發凶宅,儘管員警忙進忙出,說個不停,屋內瀰漫著我熟知的死寂。在我眼中,這戶人家原本應該要迎來毫無變化的星期六早晨。
屋內擺設井井有條,毫無兇案現場常見的混亂景象:沒有啤酒或伏特加空瓶,沒有髒兮兮的地毯,沒有荒廢的廚房,沒有濺滿鮮血的浴室。這一家人會煮飯,會好好吃飯,能照顧好自己跟彼此。
十多歲女兒的臥室乾淨又漂亮,作業都完成了,擺在書包旁邊。她的衣服折得很整齊。她躺在床上,身穿亮面睡衣,一顆子彈直接穿過她的腦袋。
隔壁是她哥哥的房間,他也是躺著,額心中彈,槍口大概只有六吋遠。顯然他是在熟睡時喪命,沒有掙扎扭打或是其他反抗的跡象。
他們的母親,躺在主臥室大床上的右側。這名黑髮的美貌女子雙手祈禱似地擱在右邊臉頰下,如此的祥和。子彈砸過她的左額,一縷乾涸的血絲滑過她的側臉。
「絕對是老爸下的手。」犯罪現場調查員說道。
「他傷得多重?」我問。
調查員幾乎在這待了整夜,面如死灰,滿頭亂髮。
「看來是死不了。」
究竟這名父親是真的想死,還是刻意將傷勢控制在這個程度?對家人開的三槍毫無猶豫,他也是對自己的腦袋開槍嗎?如果是的話,他很難保證自己能逃過死劫。太奇怪了。
我跟攝影師討論該拍攝哪些細節,提出我的需求。我看了母親和兩個孩子的屍體最後一眼,跟驗屍官辦公室的人員達成共識,讓員警把慘死的三人送去停屍間。
屍體離開了,現場的指紋也早已採集完畢,我可以在屋內四處遊走,仔細研究。當年還沒有DNA證據這玩意兒,鑑識科學也不如今日進步,在犯罪現場的隨興作為換到今天想必會遭到各界譴責。我們確實很小心,盡量不碰屍體以外的物品,但若是採集到某個病理學家的指紋,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送犯罪現場調查員一瓶威士忌。
母子三人的驗屍非常簡單,畢竟他們生前都很健康,只是腦門上中了一槍。然而這個案子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那棟屋子──安靜整齊的擺設,突兀的屍體──一直留在我心中。那股黑暗跟著我回家,關上家門時,我仍舊難以擺脫它。接近傍晚了,孩子在屋裡亂跑。看到他們紅潤的燦爛笑顏,如此的鮮活,我開心得無以復加。
我走向埋首書堆的珍,環抱住她,向她道歉,承認我太沉溺於工作,在家裡太過冷淡疏離。我知道這世界上沒有比我方才檢驗過的三具屍體,還要冰冷遙遠的事物。我在她耳邊低語承諾會更加努力,成為更加關愛、坦率,更有情緒變化的丈夫。
後來我得知該名射殺妻小的父親並沒有對著自己的頭部開槍,他沒有性命之憂。一出院,他馬上被送進精神科病房。事後在別的案子合作的警官向我透露他的辯護團隊可以輕易說服大家,說他精神失常,就算被控殺人罪也能以此為由減刑。
殺人罪的刑責往往比謀殺罪還輕,辯護律師們自然偏好往這個方向判決。當年精神失常是常見的擋箭牌。二○一○年的刑法改革限制了減責原則的定義,僅適用於明定的疾病。在改革前的幾十年間,辯護方可以隨意掛起精神失常的旗幟,我個人認為這招被濫用的機率很高。不過呢,我和任何人都沒想到這名父親不是瘋子的可能性。要完全喪失心神才有辦法射殺自己的家人,不是嗎?
我以為這個案子就到此為止,但是在鑑識醫學這一行,就算你的患者早就死透了,案件總有辦法起死回生。幾個月後,我被找去替這個案子出庭作證。沒想到他遭到起訴,還不是殺人罪,而是謀殺罪。那名警官私下跟我說兇手跟精神病院的女患者交往,他向情人表白其實他只是裝瘋,過去的家庭生活令他難以忍受。他射殺妻小的理由單純只是膩了。
各位或許認為這番說詞完全證實了他腦袋不正常,可是當他的女朋友提報這件事時,院方立刻進行深入訪談,判斷他的精神狀況相當正常。他背負的罪行變成謀殺罪。兇手被判有罪,求處無期徒刑。看似和諧溫馨的四口之家崩毀的原因並非瘋狂昏惑,而是意圖明確的冷血殺機。
這個案子鞏固了我要更為珍付出的決心。我不認為任何人會指責我沒盡父親的職責,特別是我的孩子。我早上幫他們打點好一切,下班回家又旁著陪他們看書、煮飯、寫作業、玩遊戲,最後哄他們睡覺。但我絕對是個不及格的丈夫。
珍想要一個真情流露的丈夫。我以為在她漫長的學習期間,擔下大半家計跟育兒責任足以表達我的愛情。然而一想到那個剛被送進牢裡的父親,或許他表面上顧家,私底下卻悄悄籌劃殺害妻小。我領悟到即便全心投入家庭生活,一個人的心思還是有辦法徘徊在別處。我也跟他一樣嗎?我是不是在扮演好爸爸的同時,心裡只有工作?這是珍抱怨連連的原因嗎?她要求的是更多的關愛、更專注的付出嗎?
我想了很多,卻什麼都沒做。我們回歸忙碌的生活,與愛情的交流似乎無緣。總有一方隨時要應徵上工,就算兩人都在家,還有數千件大小事等著處理:孩子跟功課、工作碰到的難題、房屋修繕……
真不知道要把愛情塞在哪個角落。我該在日記裡寫下「下午五點開會。七點談情說愛」嗎?我又該有何表示?買花回家?準備燭光晚餐?很想問問其他男性,看他們是如何在婚姻生活中醞釀出溫暖、幽默、愛意,但這樣的話題不適合在同僚間提起。不可能的。我們只聊兇殺案,不談愛情。於是我繼續盲目摸索。
(本文為《傾聽死亡現場:頂尖法醫病理學家的非自然死因調查事件簿》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傾聽死亡現場:頂尖法醫病理學家的非自然死因調查事件簿》 Unnatural Causes
作者:理查.薛賀德(Richard Shepherd)
出版:馬可孛羅
日期:2020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