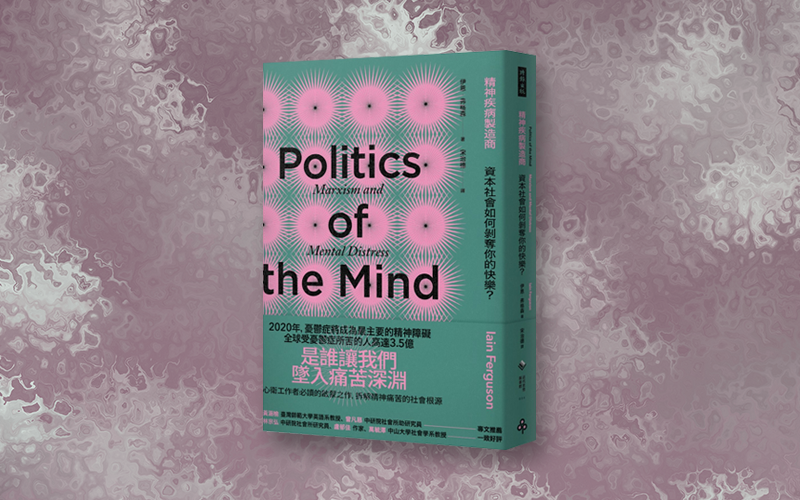
文|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譯|宋治德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十年裡,對心理健康和心理問題的主流理解,並非來自於生物精神醫學,反而是二十世紀之交創立的精神分析,其理論與實踐都出自於佛洛伊德。美國尤其如此。大多數美國精神科醫師都是受過精神分析訓練的分析師,精神分析概念亦是DSM早期版本的基礎。然而,精神分析的影響遠遠越出了諮商室。它的理論概念普遍存在於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部分要歸功於贊同佛洛伊德思想的出版品,如佛洛姆的《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它在美國和全球都成為暢銷書。
有少部分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佛洛姆和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內,繼續捍衛佛洛伊德激進的思想遺產(這部分的認定通常差異很大),但都意識到,在戰後時期具主導地位的精神分析墨守成規,沒有些許的進步。例如,在一九八○年代初期,大約有五百篇精神分析論文和書籍討論男女同志議題,其中,「只有不到六篇文章主張,同性戀應該也屬於一種令人滿足的心理結構(satisfactory psychic organisation)」。
同樣,在討論精神分析對美國戰後女性受壓迫問題的影響力時,弗里丹(Betty Freidan)寫道:
在一九四○年代結束之際,佛洛伊德思想迅速而徹底地獲得接受,但十幾年來卻都沒有人質疑,為何受過教育的美國婦女爭著要回到家中做主婦……經歷了大蕭條和二戰之後,佛洛伊德的心理學不只是一門人類行為科學,一種治療痛苦的方法。它更成為一種無所不包的美國意識型態,一種新的宗教……佛洛伊德和偽佛洛伊德的理論到處都是,就像細微的火山灰一樣。
跨性別(transgender)族群的遭遇並沒有更好。正如邁爾斯(Laura Miles)所說:
直到二十世紀中期,在大多數的性學家、醫師和運動倡議者的眼中,性別轉換行為基本上與同性戀沒有差別。表達了「變性」欲望的人,通常被當作無法正視自身同性戀傾向的同性戀者,也就是「自我否定的同性戀者」。即使變性概念與同性戀的概念後來有區分開來,但許多佛洛伊德主義者仍然堅持了上述觀念數十年。直到一九六六年本傑明(Harry Benjamin)的著作《變性現象》(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一書出版之後,變性這個詞才真正進入醫學或社會範疇,或是更廣泛作為自我身分認同。
在英國,精神分析對成人精神醫學的影響較小,但確實對其他心理健康領域產生重大的影響,諸如兒童輔導和社會工作,部分貢獻來自於一群傑出的精神分析師與其著作,包括佛洛伊德的女兒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克萊恩(Melanie Klein)、溫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和鮑比(John Bowlby)。

在臨床心理學和精神醫學中,精神分析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寵了。總的來說,臨床心理學將研究和實踐方法建立在自然科學的經驗模型之上,精神醫學越來越穩固地紮根於生物醫學。兩者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神經科學的發展。但是,精神分析思想在大學的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系、電影和媒體課程)繼續蓬勃發展,部分是透過杰奎琳.羅斯(Jacqueline Rose)和齊澤克(Slavoj Žižek)等著者的作品。更一般地說,正如弗洛什(Stephen Frosh)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繼續被精神分析思想所滲透。例如,眾人都已普遍接受,童年經驗會強烈影響成年期,而且:
精神分析的中心觀念也許還是一樣普遍:我們的行為受無意識動機所驅使,而且自己往往也不大理解。當人們問自己為什麼做某事,或指責朋友自欺欺人,或者無法看到自身行為的「真實」原因時,便會利用所謂的精神分析「論述」來理解身旁的社會環境。這證明,精神分析的假設已經以低調的方式「滲透」在文化中,因為看來是如此理所當然。
然而,在戰後的大部分時期裡,除了一些例外情況,精神分析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和一般左派所關注的核心(例外的是一九六八年以後的法國、拉丁美洲以及上文提到的文化研究學科)。較為寬容的看法是,精神分析無助於發展相關理論與作為,無法推翻資本主義。但從最嚴厲的觀點看,精神分析只是一種猜測性的世界觀、不科學的生物化約論,過分強調性形塑了個人種種的行為和精神痛苦,但它們實際上是立基於壓迫、剝削和異化的社會產物。
馬克思主義之中始終存在著一個少數流派,試圖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兩種知識傳統之間找出共通之處。這確實是某些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精神分析學說發展時期所採用的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史達林領導的黨開始清算佛洛伊德的俄國追隨者,托洛茨基卻支持他們:
宣稱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對它置之不理,那就未免過於簡單和粗暴了。當然,我們也同樣沒有義務接受佛洛伊德主義。它是一種現行假說(working hypothesis)。但我們能由它建立唯物主義心理學的推論和猜想,並以在適當的時候以實驗證明,最後也成功了。因此,我們既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宣布禁止某種方法,即使它不太可靠又試圖預測結果,而靠實驗方法得到這些結果要慢得多。
同樣,美國哲學家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在一九六○年還是革命派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社會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m)期刊的編輯,他當時撰文將佛洛伊德形容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兩位思想家之一」。他們看到:「從理性理解欲望的康莊大道。」更為晚近,馬克思主義者諸如伊格頓和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的也稱讚精神分析具顛覆性的潛力。
這些學者都承認,佛洛伊德激進主義的根源,就與黑格爾和達爾文等思想家一樣,並不在於他們所公開支持的政治立場。佛洛伊德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就像三個世紀前的霍布斯一樣,對人性抱持非常消極的和個人主義的看法,認為人們本質上是具侵略性和以自我為中心。由此看來,如果文明要繼續存在,就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抑制。然而,與此同時,他絕不是西方文明的辯護者,也多有批判,他能夠從病人身上看到壓抑,特別是性壓抑產生的巨大痛苦。這正是他理論的激進鋒利之處。

精神分析學家對於佛洛伊德思想有一致看法之處甚少,顯然眾人對他的最基本觀念有各種分歧看法。當中包括兒童發展理論:性心理經過口腔期、肛門期和生殖期逐一發展,每個階段都帶來了特定的挑戰,並在伊底帕斯情結之中得到解決(無論成功或失敗);驅力理論:最初建立在性和自我保存的驅力之上,後來他加入了死亡驅力;心靈的結構模式:由本我(無意識)、自我(有意識的我)和超我(以父母和社會形式出現的權威意見)所組成。
這些理論的每個方面,都受到連續好幾代精神分析師的挑戰或修正(佛洛伊德自己一生也都在修訂),下面將討論其中一些挑戰和爭論。
無意識
如上所述,根據佛洛伊德的中心思想,無意識精神現象確實存在,就定義上來說,它以一般人(是自己,而不是他人)不會察覺的方式形塑我們的行為,這是所有精神分析學派共同抱持的信念。正如他所有早期的重要概念一樣,佛洛伊德聲稱,他透過身為臨床醫師的經驗而獲得這一想法:聆聽情緒不安的患者說話很重要,但沒說出口的更有意義,包括沉默、口誤、遁詞、身體語言,以及最重要的──夢的內容,在在向佛洛伊德指出了無意識的存在:
我為自己立下任務,要將隱藏在人內心深處的東西攤開來……我認為這個任務實行起來異常艱鉅。從日常所見所聞來看,我們或許會深信,沒有凡人可以保守得住祕密。因為如果人緊閉嘴唇沉默不語,就會用他的指尖喋喋不休,每個毛孔都會滲出他的祕密。
佛洛伊德認為,有意識的行為是由我們通常不察覺的力量所形塑,但有許多人因此把他看成粗糙的決定論者。然而,科維爾(Joel Kovel)認為,他所描述的無意識精神活動與意識心智之間的關係,比一般認為的更為微妙與複雜:
佛洛伊德從未隨口說說,簡單地宣稱行為就是受無意識所決定。他堅持,在既有現實的之下,行為才受到無意識願望影響而產生。可以說,行為形成於意識和無意識思想(表達出客觀世界)之間的邊界──一清二楚的邊界,由於壓抑的本質作用,無意識從未返回與意識的關聯。所以,佛洛伊德的思想可看成具有「辯證法」的性質,因為它是強調不同類型經驗之間的相互作用,而非其中一種類型決定行為。而無意識需要特別注意,正因為它在日常生活之中不受關注。因此,精神分析只是要補償先前未曾關注的領域。
因此,佛洛伊德的重要貢獻並不是發現思維中的無意識區域(其他人早已提出這種觀點),而是斷定,在壓抑作用下,無意識與意識思維的關係是動態的。對於佛洛伊德來說,無意識儲藏了受到壓抑的幼年思想、願望、信念,它們被禁止或視為危險。然而,儘管受到壓抑且沒有意識到,它們仍然以上述方式以及精神官能症──諸如焦慮症、憂鬱症、恐懼症──繼續存在。精神分析治療的目的是在安心的環境中,將這些令人不安的幼年信念和記憶帶入意識中,再以成人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以佛洛伊德最常被引用的格言來說,就是:「將精神官能症的痛苦轉化為一般的不快樂」)。
如上所述,所有精神分析學派都贊同無意識的概念。也就是說,從精神分析的政治性方面而言,美國戰後具主導地位、較為媚俗的精神分析,會特別強調心理的理性部分──自我,而不是包含無意識面向的本我。對比之下,從一九三○年代法蘭克福學派到更激進的精神分析方法(基於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岡的思想),則更加強調無意識當中有許多「事實」,包含資本主義大多透過家庭制度壓抑我們最基本的需求和情感。
性慾
無論是在佛洛伊德的時代還是今天,最常有的批評,就是「他把一切都化約為性」。例如,加拿大馬克思主義者蘇珊.羅森塔爾(Susan Rosenthal)將佛洛伊德形容為「把心靈化約為生殖器的江湖郎中」。正如佛洛伊德自己在《一個自傳式的研究》(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中所觀察到的:
很少有研究像精神分析一樣產生廣大的分歧意見,莫衷一是,或者引發眾人勃然大怒,原因就在於它的結論:性功能在生命開始時便啟動,即使在幼年期,透過重要跡象,我們也能看出它的存在。
這個結論所引起各種憤慨和怒氣,並不限於體面的資產階級。蘇聯語言學家沃洛希諾夫(V N Voloshinov)在一九二七年於俄國出版的《佛洛伊德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批判》(Freudianism: a Marxist Critique)著作中亦持類似觀點,認為:
佛洛伊德主義「意識型態上的基本主題」是一個人的命運,他生命的全部內容和創造性活動──如果他是藝術家,那就是他的藝術活動;如果他是科學家,那就是他的科學活動;如果他是政治家,那就是他的政治綱領和方法等等──這些完全且只由他的性本能所決定。其他面向都只是性的龐大主旋律的和聲。
討論這些批評時,首先要注意的是,佛洛伊德這些有關幼年性慾的看法,應該是基於在諮商室內的討論和分析慢慢形成的,並非刻意達成:
這些童年時期的經歷,總是與性興奮及其反應有關,我發現得面對幼年期性慾這個事實──又是人們最懷有偏見的議題,卻又新奇且充滿矛盾。人們認為兒童「無辜天真」,沒有性的慾望,直到青春期的麻煩年紀才開始與「感官」的惡魔鬥爭。但我們不能忽視兒童身上偶爾出現的性活動,也不可把它看成退化或過早墮落的徵兆,或天生怪胎的特質。
眾所周知,佛洛伊德最初認為,他的患者所描述的個別性經驗,實際上都是亂倫、強姦或性虐待所導致的結果。但他拋棄了這種「誘姦理論」,轉而認為,那些患者的說法大多是基於幻想。他的轉向引起重大爭議,成為批評者的主要焦點,麥森(Jeffrey Masson)就指責佛洛伊德虛偽和怯懦,拋棄誘姦理論是為了避免被體面的維也納上流社會排擠。就連佛洛伊德的同事費倫齊(Sándor Ferenczi)也在晚年改變看法,認為佛洛伊德早期的女性患者可能確實是遭強姦或虐待的受害者。
根據「全國兒童受虐防治協會」(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的數據,目前已知的性虐待盛行率,大約每二十名兒童中就有一名經歷過某種性虐待。研究證據也指出,遭性虐待的兒童往後生活可能出現思覺失調症。幾十年來,精神分析師有可能會告訴受虐女性(與少數男性受虐者),她們自稱的被強姦經歷,實際上從未發生過。分析師的這種做法也應該成為重大的關注議題。佛洛伊德還有許多具爭議的觀點,就像他聲稱「陰道高潮」優於「陰蒂高潮」,再加上精神分析在一九五○年代變得媚俗、主導美國文化,所以毫不意外地,早期許多女性運動者將他視為敵人,認為他的思想成為壓迫女性的主要源頭。
針對這些批評,佛洛伊德的左翼辯護者有兩種回應。首先他們認為,佛洛伊德從未否認童年性虐待的事實或影響。李爾說:
值得注意的是,佛洛伊德從未改變想法否認兒童受虐存在,也沒有否認它會造成持久的心理傷害。他拋棄的想法是:患者躺在診療椅上所講到性誘姦故事──無論多麼真誠──總是完全真實呈現實際發生的事件。
其次,正如一些批評者所說的,如果佛洛伊德拋棄誘姦理論的主要考量是為了保住聲譽,那麼他維護的方式也太沒道理了。畢竟拋棄了誘姦理論後,要解釋人的發展和病徵,性慾占據的核心位置就會更大而非更小:
拋棄誘姦理論後,佛洛伊德得到了學術發展的重要機會。他因此能夠擴展對性的解釋。既然他一些患者生動地描述了性遭遇,但實際上從未發生過,那麼他就有理由認為,性在想像力中更為活躍,更值得探索和理解其運作方式。想像力似乎能夠賦予一個人性生活,即使他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性生活。
同樣,弗羅什指出:「拋棄誘姦理論正是精神分析的創始時刻。新觀念取而代之,也就是患者的幻想,這可說是精神病理學的關鍵要素。」

這裡有一點很重要,佛洛伊德絕對沒有將人的行為化約為動物或生物本能(儘管他從未否認性驅力的生物學基礎),他提出的見解非常不同,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茱麗葉.米契爾(Juliet Mitchell)的話說:「一種人本的性慾理論,其中心是人的想像力。」正如李爾所說,對於佛洛伊德來說,性慾是使我們成為人的一種身心模式。在他的《性學三論》(一九○五年首次出版)中,他開始討論戀物癖,並認為「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性驅力,只有它能對我們產生那麼大的興趣」。為什麼?因為戀物癖證明,人與動物不同,性對象(有性吸引力的人或事)與性目的(趨力所推動的行為)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正如李爾所說:
可以這樣設想:一隻雀鳥碰巧在女士的鞋子裡築巢。過程中,鳥兒會對鞋子表現出高度的關注。但是這隻鳥不會把鞋當成一個戀物。為什麼?鳥缺乏想像力嗎?從重要的意義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人與其他動物不同,其性慾在本質上是富有想像力的,也就是在本質上,人會接收各式各樣的想像力。因此,各種各樣的活動都能有性慾的面向,即使與生殖無關;另一個結論是,當人最終完成生殖時,就會再繁殖富有想像力的動物。
這讓我們想到馬克思相關的評論,他談到「人性」和「動物本性」的差異,以及想像力的巨大潛能:
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至少蜜蜂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人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
因此,毫不奇怪,比起同時代的大多數人,佛洛伊德對於「正常性慾」的元素反而比較有彈性。而且,有一些猛烈批評佛洛伊德的「狂熱分子」,還會壓迫他們眼中「偏離」正常的人(尤其是同性戀)。他在一九○五年《性學三論》中寫道:
我們必須學會不帶憤怒,自然談論所謂的性慾倒錯,比方說,人的性功能已擴大範圍,不限於身體部位或選擇的性對象。在不同的種族和時代裡,所謂的正常性生活界線並不明確,這一點應該足以使狂熱分子的熱情冷卻下來。
一九七○年代,一些重要的女性主義者,諸如英國的茱麗葉.米契爾和美國的契斯勒(Phylis Chesler),都認為性慾是流動的,雙性戀是常態而不是異常。她們發現,在精神分析思想的架構下,「現實是動態的,當中沒有本質上的性別差異」,因此本身沒有壓迫性,它是「女性的最佳希望,避免自己被化約成本質論者的專業術語」。
同樣地,在一九七○年代,美國少數精神分析師能夠回到佛洛伊德一九○五年的觀點,從DSM中刪除被歸類為精神疾病的同性戀,作為他們支持同志運動的基礎。正如赫爾佐格(Dagmar Herzog)指出的,從那時起精神分析師對同性戀的態度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
到了一九九○年代,我們已有無數的工作坊、委員會,社會上也有許多相關倡議、研討會論文、出版品以及期刊。這一切顯示了,精神分析師這個社群渴望向男女同志學習來改造自己。更多出櫃的男女同志也成為了精神分析師。
這種態度和專業實務的徹底轉變,顯然很受歡迎。當然,這不表示我們可以忽視過去幾十年媚俗版的精神分析對多元性別族群的壓迫,那段「恐怖歷史」不容掩蓋。
然而,歷史也表明,精神分析觀念與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等其他世界觀一樣,並不是存在於社會或政治的隔絕狀態之中。它們受到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和意識型態所形塑。因此,毫不意外,精神分析中的主要傳統──個人派和媚俗派──通常反映了社會中更為普遍的主流思想。
不過,同樣真實的是,尤其是在社會變革和動盪時期,出現更多人以更激進的角度解讀這些觀念。例如,美國精神醫學會在一九七三年改變做法,不再將同性戀歸類為精神疾病,這並非偶然,而是由於此前幾年同志運動興起,他們為同志權利果敢發聲,成功地挑戰了醫學會的觀念,不再將同志的性慾視為病態。無獨有偶,在本章下一部分,我們將看看激進左翼其他派別的例子,他們試圖將精神分析思想當作一種鬥爭方法,以反對壓迫和剝削。
(本文為《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 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
作者: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出版:時報出版
日期:2019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