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裡,帕姆的問題隨著時間,慢慢開始改變。不是為何觀護所的管理員那麼做,而是為何我們那麼做?一個更大的真相,在帕姆的問題背後,隱約可見:為什麼我們要傷害那些最脆弱的人?我們是什麼?我們是誰?
那項追求,在某程度上是要挽救一個救不回的男孩。

文|狄諤斯(Dexter Dias,英國人權律師)
譯|陳義仁
這幾乎正是亞倫(Dylan Aaron)的友人在 2010 年面臨的兩難。亞倫當時十七歲,而他最終掉進約翰坑湖(John Pit pond),那是英格蘭西北部威根都會區附近的一處景點。湖水漆黑而危險,水面下潛藏蘆葦等植物。這些植物會跟軟泥一起困絆任何泳者的腿部。那裡死過一些人,當地稱之為「深坑」。
亞倫他家跟同為當地人的麥奎爾(McGrail)一家長期不和。經過一連串紛爭,種種事件最終累積成 2010 年 5 月那場決定命運的衝突。凌晨三點,跟朋友玩了一晚的亞倫回到家,看到家裡的車子被一塊石板砸碎了擋風玻璃。他知道是誰幹的,而他猜對了。
麥奎爾跟弟弟在「深坑」夜釣。亞倫一走近,雙方就打了起來,兩人一起從陡峭的池岸滾向水邊。就在這時候,年長十歲的麥奎爾將亞倫丟進湖裡。他說:「淹死你這小混蛋。」亞倫拚命把頭露出水面,同時大喊:「救命,我踢不動了!」麥奎爾說:「讓他去死。就算他出得來,我也會殺了他。」
情急之下,亞倫那些朋友試著下水救人。一開始,麥奎爾阻止他們,但其中一人還是跳了下去。一切都太遲了。亞倫的頭、還有他伸出的手臂,全都沒入「深坑」,他就在水裡死了。
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個原因是,為了指出湖泊看似安全卻能致命──人們很容易溺死在這種地方,無論景觀優美與否。然而,第二個原因則是,即便面臨明顯危險,亞倫其中一位朋友還是試圖救他。更令人激動的是,那位朋友試著去救亞倫,即便約翰坑湖在三年前發生過另一起事故。該事故死了一個人,而且受到全英國關注。
在安東尼人生改變的那天,他只不過是做了一件他做過幾十次的事:走去當地的商店。到了商店,他能聞到有人在烹煮家禽。誘人的氣味飄進他鼻子,然後直衝他的大腦。他很餓,非常餓。然而,儘管熱氣逼人,他的雙腳還是繼續追著一個念頭……那就是可口可樂。他才十一歲。他父親說過,他可以去買一罐可口可樂。要是除了可口可樂,還能拿點雞肉來吃該有多好?
活著真好。在貝南過日子不容易,他們艱苦度過。安東尼的母親盡了力了。然而,如今活著真好。有時候父親會打他,但那會讓他更堅強。安東尼想要變得堅強。
有時候當你跟他說話,他會瞇起那杏仁形狀的雙眼來看著你,一副持槍歹徒的表情。他後來會說出他在我們初見時的真正想法。「當時我在想,這個人是誰?他的法語講得比我還要爛。」
那是真的,我的法語那時候生鏽了。
「你為什麼會來這裡?」他認真問我。
坦白說,我不曉得要從何講起。我說,有個男孩死在英格蘭一座少年觀護所裡,而我試著要去瞭解發生什麼事,因此我需要跟很多不同的人談論很多不同的事。他聽了很驚訝,驚訝的不是我既發散又不精確的調查,而是那起死亡事件發生的地點。他對英國的認識只有超級足球聯賽。
「人們在英格蘭弄死小孩?」他說,一臉難以置信。
「C'est compliqué(這很複雜),」我說,而且馬上感到懊悔。要在離家這麼遠的地方承認此事,我覺得很羞愧。但在事實上,是的,我們的確弄死小孩。我該說出來的。
「但是,為什麼你們這麼做?」他問。
我試著說明我是那家人的律師,但不確定我能讓他理解律師是在做什麼。在西非的烈日底下,我愈說愈弄不懂律師到底是什麼。在那一刻裡,我們似乎都離家很遠。「我正努力查明他為什麼會死,」我說。
「為了誰?」安東尼問。
這是任何律師都該問的問題。答案就是:complqué(很複雜)。
人生就像法律,並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我想要知道,」最終我這麼說。
後來,就在我們快要分別的時候,他告訴我:「我們第一次見面那天,我正要離開。然後我想,『好吧,給他一個機會。』」
這有趣了。沒人給過安東尼什麼好機會。我在筆記本裡寫下:機會。什麼時候我們給彼此機會?
2007年5月3日,萊昂(Jordon Lyon)跟他八歲的繼妹貝瑟妮一起出門,前往「深坑」水邊去捉蝌蚪。然而,湖岸險陡,貝瑟妮失足滑進黏膩的湖水和淤泥。兩名垂釣客能夠解救那女孩,但是萊昂想都沒想,就跳下水去救貝瑟妮。萊昂被湖水吸得更進去。他不見了。
接獲報案後,兩名輔警騎著腳踏車趕了過去,抵達現場的時候,萊昂已經沒入水裡幾分鐘了。兩人接下來的作為,引發各大報所謂的「全國公憤」。他們的作為受到保守黨領袖卡麥隆(David Cameron)強烈批評,卡麥隆說,這種情況「非常荒唐」。兩位輔警並未下水去救十歲大的萊昂。
隨著這場爭議加劇,有位內政部發言人出言迴護那兩位飽受中傷的輔警。她說:「準則建議輔警不要在未經訓練下,進入危及生命的情況。」那就是官方立場。輔警沒有受過訓練,所以沒有義務幫忙。
然而,這個官方立場並未回答最根本的問題:他們沒有受過什麼訓練?他們或許沒有受過正規警訓去救人,但他們沒有被生活訓練過嗎?我們有嗎?你會怎麼做?正如萊昂的繼父甘德頓所言:「你不用受訓就能跳下去救一個溺水孩子。」確實,該地區警察聯合會的主席承認,「每天都有人跳進河流和湖泊救人,因為那是對的事。」
萊昂溺水事件令人不禁想問,我們對於他人的義務包含些什麼。
我們該為周圍的人做些什麼,而我們演化而來的心智,對此又有什麼影響?這是英國司法最著名案例的核心問題,此案即為「多諾霍訴史蒂文森案」(Donoghue v Stevenson),許多人不懂法律的人也都聽過,這個案例大大推進現代的疏失責任法(law of negligence),案情如下:佩斯利鎮的威梅多餐館,售出一瓶內有蝸牛的薑汁啤酒。該案一路上訴到負責終審的上議院,這時阿特金勳爵(Lord Atkin)將最關鍵問題以最簡形式提出(他經常如此):「誰是我的鄰舍呢?」
阿特金的表述方式,令人想起一個更古老的問題。該問題廣受引述,卻罕受理解,但聽過的人甚至更多,那就是:「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
為了瞭解你是否看守你兄弟、又如何看守你兄弟,我們要去見見你另一個演化來的自我,另一個典型:「感痛者」。
◆奴隸海岸—不歸門

安東尼走進迦納的那間商店。貝南
那間店比棚屋好一點,擁有磚牆和鐵皮屋頂。店主告訴他,後屋有幾件仿冒的足球衫。雖然不是正牌貨,但在這個痴迷英超足球的國家裡,這對於一名十一歲男孩是難以抗拒的。
安東尼的經歷很複雜。他的家族屬於埃維族(Ewe),該族是一個橫跨迦納東部、多哥南部和東邊鄰國貝南的種族。安東尼的父親是迦納人,安東尼就出生在那裡。然而,他母親的家族有部分是貝南人,當安東尼的父親拋棄家庭,她就帶著安東尼和他三個妹妹回到貝南。
在貝南,人們通常會說當地語言,還有法語。自從法國人於十七世紀末在那裡建立奴隸堡壘,貝南跟法國的關係就一直糾纏不清。該地區是在十九世紀正式成為法國保護地。
貝南本身為西非中部的一片長條形土地,南北延伸四百英里,就像一根鼓起的手指,從貝南灣往北指向撒哈拉沙漠,貝南灣即是前法屬殖民地達荷美(Dahomey)在1960年獨立、1975年改名貝南的名稱由來。貝南的位置靠近非洲大陸的肘部,西非就在這裡直角突入大西洋。而且,雖然貝南的海岸線很短,僅有七十五英里,但海洋卻在當地歷史扮演重要角色。貝南的沿海地區為「奴隸海岸」的一部分,那條惡名昭彰的海岸曾是大西洋奴隸貿易的中心。正如那首舊時水手號子所警告的:「當心、當心貝南灣,進去的很多,出來的很少。」
這句話就像從前地圖師的警語:「此處有龍」。為了致敬所有被擄離家園、運往美洲的奴隸,沿海城市威達(Ouidah)的海灘上,建了一座紀念拱門—就在慢慢碎開的大西洋波浪之前,矗立著這座「不歸門」,紀念死於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數百萬人。
在經濟上,貝南嚴重落後,而且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列為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該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相當於南蘇丹和盧安達。極度貧窮影響了貝南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導致許多社會弊病,包括營養不良、死於瘧疾和腹瀉之類的一些可預防疾病,也導致某種現代的奴隸制。
不過,安東尼的父親說他想讓這男孩回迦納。他會出錢讓兒子上學,他會給兒子一個未來,讓他將來能自立生活。「我會想念我媽和妹妹們,」安東尼告訴我:「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想學習,我想上學。」於是,安東尼被送回迦納跟父親一起生活。現在,父親派他去那間擁有鐵皮屋頂的商店。
安東尼走過那門,再也不歸。
(本文為《十種人性:我們與善、與惡的距離各有多遠?》部分書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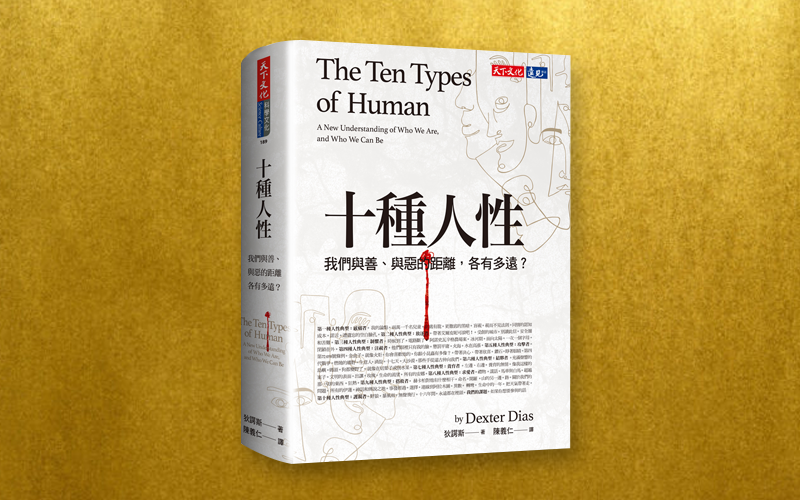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十種人性:我們與善、與惡的距離各有多遠?》 The Ten Types of Human: A New Understanding of Who We Are, and Who We Can Be
作者:狄諤斯(Dexter Dias)
出版:天下文化
日期:2019
圖片credit:Arnaud Helinck@flickr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