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幻小說作為預言世界的先聲,不僅是探究人與科技的共生樣貌,浮世繪式描述當中的新奇燦爛,它更具備一種探索性質,於虛構境況實驗人的喜悅、懼怕或脆弱,觀察人類最後會變成何種樣貌,近代兩本著名的科幻小說便探究了同個問題,而他們各自有不同的答案:人類最後會因為什麼緣故滅亡?歐威爾在他著名的《1984》中塑造了極權政府掌權的未來,老大哥管制了資訊透明與階層流動,我們困囿於極具壓迫的外力統治,人們終被自己所懼怕的所毀滅;相反的,赫胥黎則在《美麗新世界》中敘述人們使用索麻逃避粗糙現實,麻醉後生理進入天堂,在淫樂之中真理變得喪失了價值,再無人想要探求更高層次的意義,人們終將被自己所喜愛的所毀滅。
哪一個末日景象更靠近我們?波茲曼指著電視說,是後者。
補充自1984年的書展演講稿,美國傳播學者波茲曼(Neil Postman)寫就的《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批判了當時美國本土電視的氾濫現象,千萬盒子進駐家戶之後,毫無間斷的新聞、資訊、圖像質變了閱聽習慣,同時也改變世代對於世界的理解。他試圖證成赫胥黎的自娛途徑已讓人們對真正重要者棄若敝屣,轉而擁抱螢幕裏縈繞不散的娛樂幽魂,轉譯成多種形式,從脫口秀、貓咪賣萌到網紅開箱,這種瘧疾使人強制發笑,再也擺不出憂愁神情如沈思者的莊嚴,以及寂寞。
延續了麥克魯漢的「媒體即信息」,波茲曼非是單純關注我們看待的內容與載體,更是注意在看的過程中媒體如何形塑思維的隱微驅力。「所有溝通媒體都會都會重新改造文化-從繪畫到象形文字,從字母到電視系統。每種媒體都像語言本身,也就會思考、表達或感受提出新的定位,進而造就獨特的論述模式。」波茲曼用了帶有文學意旨的隱喻來形容媒體,在直接顯露單純訊息以外,它更具備了神諭般漫漶的暗示作用。以字母以至於書寫的發明為例,相較於即時消散的對話,書寫具有超越時空、得以容許多重意義進駐的特質,一種不對任何人說,卻又和所有人交談的載體。於是口語與書面語逐漸分化,背後蘊藏著對象、接收、判讀種種相異的理解途徑,也連帶打造了各自思域,經過時間槓桿放大之後,建構出來的廣袤足堪包覆世界本身。
所以在媒體即隱喻之後,接連探討的便是:媒體所建構的世界要如何傳遞知識?在媒體支配文化的過程中有什麼盲點。波茲曼相信真理傳遞會受到傳播媒介的限制,在轉傳過程中必然導致失真,「這正能說明真理是一種文化偏見,每種文化都設想有某種符號形式最能可靠地傳達真理」比方說古希臘時代崇尚修辭術,不只是種表演形式,更包含了組織證據與邏輯辯證,當時代人把這種口頭講述形式當成真理交流的正宗途徑,但時至今日,人們很難想像法庭上僅用言語修辭、感性訴說而不訴諸任何書面文字就完成判決,我們會上網打字說,那個法官是恐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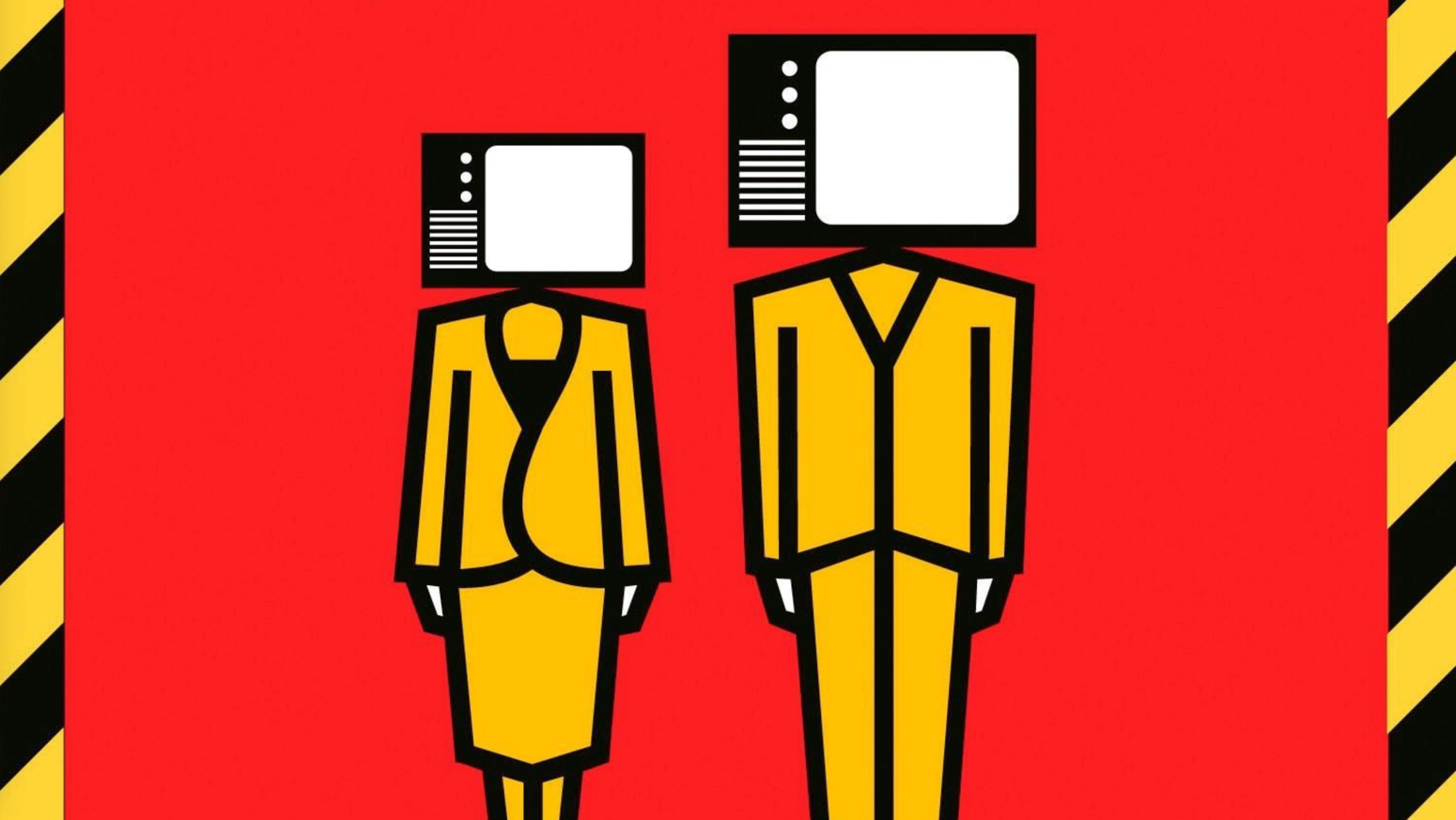
現代人真正相信的真理是什麼?與其這樣問,還不如問「現代人真正相信的媒體(隱喻)是什麼?」來得更加精確,並不難猜,被我們奉上神壇的便是數字,能被書面呈現探究並即時在螢幕中化約萬事萬物的各種績效排行與科學實證,但凡能夠量化者被認定最能滿足真理樣貌。這些習以為常的日常觀點,波茲曼提醒我們,一切都跟媒體有關,跟那背後的喁喁細語有關。
依憑著如斯假說,波茲曼回溯了十七世紀英國人民首次到美洲拓荒的歷史,簡述崇尚智性的「印刷式思想」如何發展,又是如何被電視所帶來的劇烈衝擊而沒落。當時跨海拓荒者很多是新教徒,為了讀懂聖經而普遍擁有閱讀能力,由英國輸入了許多文學作品,隨著印刷廠的設立,從報紙到小冊子、對話刊物的出版,讓閱讀在拓荒時期的美洲頗為盛行,成為一種非貴族的活動,並未因智識傳播限制而培養出社會上端的文藝貴族。此種環境影響了人們在論述方面的習慣:他們普遍慣以書面文字來塑造自己的談話風格,同時也慣於接收此種經過整理反思、理性色彩較強的話語形式。
有件現在看來很荒謬的事能夠反映這個特質:1854年,林肯與參議員道格拉斯(Stephan A. Douglas)展開一場政治辯論,道格拉斯先講述了三個小時,結束時已經下午五點,隨後林肯表示,他建議群眾先回家吃飯,因為他可能也要講另外三個小時,聽眾同意了在飯後回來,最後這場辯論總共花了七個小時。現今我們很難想像七小時的政治辯論(當然可能跟現在的政治人物也有關係),更何況當時雙方答辯時都使用了構句複雜的陳述並間雜了艱澀法律名詞。波茲曼認為這顯示了印刷媒體控制了論述特質,因閱讀本身是嚴肅理性的思辨過程,需要反思、推理、邏輯、客觀,而聽者同樣具備這些能力才讓辯論得以進行-印刷式思想讓當時的知識生活與公共事務完全融入了民眾的社交範疇。
然而電報的發明打破了空間疆域的限制,與報紙聯合造成新一波的媒體傳播影響。一群無關緊要、不著邊際的對話湧入,諸如「阿德雷德公主染上感冒」、「緬因州的小官員家中遭竊」。資訊價值翻轉,不若以往是以偏好嚴謹理性,關注在政治社會和行動中所發揮的作用,反是端看訊息是否新鮮有趣、能否商品化。短小報導被切割導致去語境化,只留存好笑好玩的浮泛表面,訊息迅速累積讓輸入多於輸出,讓「知道」的意義愈加貶值,不再是認識真相內涵、背景脈絡以及其終極意義,知道就只是被動的接收與流過,人像個空洞容器。資訊的零散與破碎化進一步得益於攝影發展,影像成了理想的新聞素材,更加真實,而且不必耗費字句解釋,在角落隨意塞一張照片,圖像中心式的思考讓眼見為憑成為了準則。隨後電視興起,上述種種現象遂變本加厲,波茲曼舉了當時美國的例子,無論是政治辯論、新聞報導、教育節目都能概括用娛樂化來解釋:所有職業在乎的只剩下如何表演、如何展演讓自己的樣貌被人所喜歡。
當然,距今三十餘年的論述仍有修正空間,像是開頭所提歐威爾式的恐懼並不完全是威權式壓迫,裏頭也有如《新語》般變形的語言拆解暴力,與媒體及隱喻的說法暗合。又或者是,娛樂至死只能是個極具戲劇性的噱頭,根源也可能是慾望至死或是賺錢至死,他提出了中介現象,卻未必是理論終點。就算如此,在當時新穎電視已成為傳統代名詞時,他所點出的種種病徵(或許無法說是病,因為我們甚至不知道這是否不正常?是不是件壞事?)仍然瘋狂上演著:Youtube無間斷的網紅生活放送、開箱置入業配無可避免的與消費主義合流、app裏不停重播舞動肢體的細碎片段......在這樣的結構性現象之中,人們該在何處棲身、用怎麼樣的姿態理解這一切,或許才是重要的。
「讓書中人物感到痛苦的,並不是他們用發笑來取代思考,而是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發笑,還有為什麼自己不再思考。」波茲曼最後一句如此寫道。
書籍資訊:
書名:《娛樂至死》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作者:Neil Postman
出版:貓頭鷹
日期:1985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