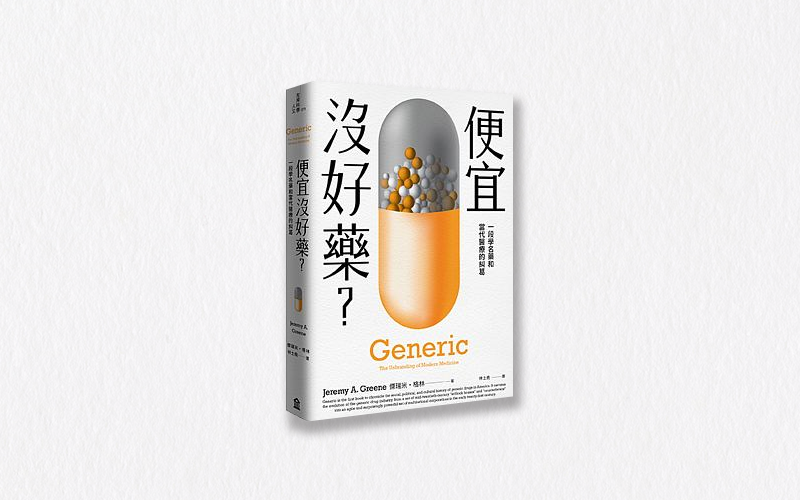
文|傑瑞米・葛林(Jeremy A. Greene)
譯|林士堯
學名藥是便宜而古老的替代藥物,讓人對昂貴的原廠藥、新藥與相關專利的價值產生質疑。如果受專利保護的新藥的安全性、藥效與適口性確實優於學名藥,那就是真創新。不過,如果它們沒有重大突破,只是把類似的藥賣得更貴,那就是假創新或「模仿藥」(me-too drugs)。過去半世紀以來,當「模仿藥」象徵著生物醫學進展的假承諾時,替代學名藥(generic alternatives,譯註:指化學成分與原廠藥不同而藥效近似的學名藥,若成分和原廠相同則稱為同等學名藥〔generic equivalent〕;下段敘述的多種他汀類學名藥即為力清之的替代學名藥)則成為懷疑論者的試金石,為他們檢驗藥物創新的真價值。
舉例來說,降膽固醇藥物力清之(Livalo,學名為pitivastatin)在二○○九年獲得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它是他汀類(statins)降膽固醇藥物的第八位成員;在力清之發表時,市面上已經有三種他汀類學名藥(lovastatin、simvastatin、pravastatin)與一種專利即將到期的他汀類原廠藥(atorvastatin)。既然有數種平價的學名藥可用,新藥的潛在價值就讓人困惑。輿論質疑,如果它們基本上都是他汀類藥物,為什麼還需要更多的模仿藥?
從歷史觀點來看,對模仿藥的批評在某些層面上和學名藥有關。美國處方藥專案小組在一九六八年公開定義模仿藥時,他們用這個名詞質疑了原廠藥的價值,如果已經有了同樣療效、只是比較舊的學名藥,為什麼還要新的原廠藥?專案小組的報告指出,「更多的模仿藥是讓藥物治療變好,還是單純變大,這從未受過客觀檢驗。」模仿藥和學名藥一樣,它也挑戰了仿造與創新的關係。在發明「模仿」藥的過程中,仿造是創新具生產力藥物的必要步驟,抑或只是浪費?
模仿藥也為學名藥替代的提倡者製造了新問題。人們認定同類藥物之間多少存在著可替代性(例如某種他汀類藥物能替換另一種,或某種抗過敏藥跟別種一樣好),這就是先前章節討論過的學名藥替代原則的有力延伸。推廣同療效替代(譯註:如前所述,以同樣療效分類而化學結構不同的藥物進行替代)的成功與否,在不同機構、不同地點與藥物種類之間有著重大差異。例如,抗過敏藥或胃酸逆流藥物在同分類之間可相互替換,而心血管用藥或抗癌藥物是否如此,爭議就大得多。
二十世紀末,在幾位利益關係人將學名藥的替代原則從化學相等藥物延伸到化學相似藥物後,學名藥與模仿藥的命運就開始以更具挑戰性的新方式相連。模仿藥的同治療替代引發了一個重要議題,那就是生物醫學知識與客體之間的連結該要多緊密或多寬鬆。要決定某個學名藥能否替換模仿藥,需要怎樣的相等性證明與替代原則?藥物在什麼情況下即使不同,也能算是夠好?
分子操作
瑪西亞.安卓(Marcia Angell)在她二○○四年的暢銷書《藥廠黑幕》(裡嚴厲批評,美國藥物產業把大多數的研發資源都投入了模仿藥的生產。《消費者報告》則在隔年揭露,每四個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的新藥中,就有三個是模仿藥,不是突破性藥物。許多當代觀察家(其中幾位還受業界資助)都同意必須做出改變,來區分真創新與假創新。即使一向支持製藥產業的塔夫斯藥物發展研究中心(Tuft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也建議,應該從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層級開始改變;也就是說,一個新藥只有比現行療法更好,或至少比得上同類別的相似藥物,它才能獲准上市。
大約半世紀前,同樣的主張就已出現。一九六一年,在埃斯蒂斯.凱弗維爾提出他命運多舛的參議院第一五五二號藥物產業反壟斷法案時,模仿藥政治便躍上新聞頭條。凱弗維爾總結了歷時十四個月的聽證會結果,提議修訂藥物智慧財產權法,規定新藥專利必須經過食品藥物管理局或衛生教育福利部相關單位的認定,屬於「真創新」而不是單純的「分子改良」(molecular modification),才能獲得許可。凱弗維爾解釋,「我們的藥物聽證會顯示,許多美國藥物專利的核發是依據輕微的分子改良;在醫學專業的驗證下,這些藥物和現行藥物之間並沒有藥效差異。」真創新混雜在大量增加的假創新中,變得罕見而難以察覺。
幾位來自學術界的藥理學家在凱弗維爾小組委員會上做證,許多所謂的神奇新藥和現行藥物之間,其實只存在微不足道的形式與功能差異。儘管這種過剩會讓「眼花撩亂的消費者產生一種擁有眾多選擇的愉悅感」,模仿藥在總體上帶來的卻是累贅與困惑。
然而,凱弗維爾發現學者很難把他們的負面批評轉譯為正面言論。莫德爾不只批評藥物有眾多選擇是「沒意義」的事,他也否定「輕微的分子改良」有機會產生顯著的藥效改變。莫德爾的同事,也就是《藥理學治療基礎》的共同作者路易.古德曼(Louis Goodman)警告,任何法律試圖落實「近似的同類化學物必須證明比現行藥物的藥效更好,才能取得專利許可」,最後都會變得不切實際,也無法強制執行。雖然堅持新藥的藥效證明是完全可行的,但在輕微的分子改良中要求比較藥效是行不通的。
古德曼質疑,「首先,『分子改良』的定義是什麼?多輕微算得上輕微?」他認為,只根據藥效不足以評估藥物。
如果近似的化學物沒有更好的藥效,但是在氣味、口味與外觀美感上都更能讓病患接受呢?如果輕微的化學改良沒有改善藥效,卻能讓物理化學性質更穩定,更容易加入嬰兒配方奶粉,有更快(或更慢)的腸道吸收,在血液中的停留時間更長,讓每日服用劑量可以減少呢?專家小組要怎麼處理實用性與彈性的問題,即使它們和藥效之間沒什麼明確關係?
美國戰後重要的科學政策制定者凡納爾.布希(Vannevar Bush,後來擔任默克董事長)也在凱弗維爾委員會上發揚了這個觀點,「我從來就不知道分子改良的意思是什麼,我也不覺得有任何人懂。」
其他在凱弗維爾委員會上作證的專家則反對模仿藥與真創新之間的對立,因為某些形式的模仿仍然是創新的必要元素。馬里蘭大學藥理學家J.C.克蘭茲(J. C. Krantz)指出,「分子操作是取之不盡的新藥泉源」。分子形式的模仿是藥物發展的必要過程,它確保「醫師會運用他們的醫術與判斷,從逐漸擴大的藥物供應中選出最適合病患的藥物。」對克蘭茲來說,分子模仿並不可恥,「正在發言的我就是一位分子操作者。十年前,我們在乙醚分子中加入氟,消除它爆炸傷害的危險,拯救了許多生命,也開啟全身麻醉的新時代。不只如此,我又進一步操作這些分子,製造出六氟乙醚。這種麻醉藥,不,應該說致痙攣藥,它替代了電痙攣療法,成為治療精神病患的新選擇。有了這個藥,許多精神病患便能康復出院。」
藥學組織也呼應了克蘭茲為分子改良宣稱的臨床意義。當凱弗維爾質疑藥物市場上的分子改良過剩時,美國藥學會理事長威廉.愛坡做出了反擊,「參議員先生,我認為藥師也寧願庫存更少的藥品,但今天有些美國人是依賴這些分子改良藥物才能活命的。」不過,從專利局、食品藥物管理局到衛生教育福利部,似乎沒有任何聯邦機構想定義與監管「分子層次的擬似」,或區分重要與不重要的藥物創新。甘迺迪政府新任命的衛生教育福利部部長亞伯拉罕.魯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同意凱弗維爾的看法,模仿藥確實在藥物市場上造成了某些浪費;然而他也表明,區分重要與不重要的創新並不是衛生教育福利部的權責範圍。當任職於禮來藥廠的製藥商協會理事長尤金.畢斯利(Eugene Beesley)現身凱弗維爾委員會時,這些提案已經接近停擺。畢斯利認為,定義聯邦的藥效標準已經夠難了,還要再設定一個標準來比較藥效,這「完全不切實際」。
自此之後,模仿藥的批判幾乎完全從衛生政策的論述中消失,直到詹森總統於一九六六年破格任命詹姆斯.哥達為食品藥物管理局局長之後才再度出現。哥達是第一位從局外進任的局長,他誓言整頓食品藥物管理局與製藥產業之間過於融洽的關係。此外,哥達也是六○年代後期的知名人物,曾登上《君子》等雜誌的專題報導與電視新聞節目,擁有充分的機會向大眾傳達他的論點;他認為,相對於現行藥物,多數新藥不過是暗淡的「異構物陰影」(isomer shadows)。
在一九六七年末一場全國廣播公司《今日秀》的經典訪談中,哥達主張業界應該「放下手邊的『模仿』研究」,專心投入在「真正的新藥上。」哥達闡述了製藥行銷騙局的表層結構(superstructure),它建築在模仿研究的基礎結構(substructure)之上,「模仿研究被迫製造出新產品與現行產品之間不存在的差異,驅使藥物公司推出假廣告。」與前人不同,哥達聲明這是食品藥物管理局的責任。他表示,在食品藥物管理局於一九六七年會計年度核准的八十三件新藥申請中,就有六十二件是模仿藥。
哥達認為模仿和假創新與假廣告相關,他還為衛生教育福利部處方藥專案小組(在第六與第七章有更多討論,本章開頭也有提到)對公部門超支狀況的關鍵調查背書,這些都在參議員蓋洛.尼爾森的藥物產業競爭問題初步聽證會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九六九年,專案小組召集人與前衛生教育福利部副秘書長菲利普.李在美國公共電視網(PBS)的節目《處方藥:價錢與危險》(Drugs: Prices and Perils)上指出,藥物產業大部分的研發經費「並沒有投入於尋找複雜問題的新解法,例如為冠狀動脈疾病、糖尿病或關節炎研發新藥,而是用來發展…『模仿藥』,也就是對現行藥物進行輕微的分子改良。」
分別代表著食品藥物管理局與衛生教育福利部的哥達與菲利普.李,他們的言論預告了美國衛生政策對模仿主義更廣泛的批判。哥達在擔任局長期間提出質疑,「總體上,藥物供應的實質進步〔是〕很小,而藥物廣告的鉅額支出卻給人大幅進步的錯覺,這可能會讓所有開立處方的醫師以為『模仿藥』是全然不同的新藥。」相反地,同時間的挪威只有八百種藥物在市面流通,而新藥必須「〔能〕被證明比現有藥物更好,也就是更安全有效」,才能獲准上市。哥達認為,「如果我們仿效挪威,採納這種相對準則,我們就可以保留研究人力與設備,專門製造能促進醫學進步的藥物。」
和六○年代前期的官員不同(他們對模仿藥的概念避之唯恐不及),在詹森政府「大社會計畫」的新基礎架構下,食品藥物管理局與衛生教育福利部更願意處理模仿藥的議題。然而,他們在醫藥學術領域的同儕卻變得更謹慎。一九六七年春天,就在聽證會剛開始的頭幾天,蓋洛.尼爾森邀請華特.莫德爾等醫藥改革者以分子混排(molecular shuffling)這個新術語來重新討論模仿藥的問題。莫德爾的回應提醒了我們,即使莫德爾也支持尼爾森想減少非必要藥物的使用,以達到更「理性」的處方開立,學術語言對政策制定者來說時常是沒有用處的。
經過六○年代末至七○年代初的藥物產業聽證會辯論後,尼爾森發現他再也無法推動任何法案來打擊模仿藥。儘管如此,他持續進行的製藥產業行銷調查,仍確保模仿藥議題穩定存在於藥品行銷的批判語言中。一九七三年,當愛德華.甘迺迪啟動一系列新的藥物產業調查時(透過他主持的衛生小組委員會〔Health Subcommittee〕),他首先質疑的就是「為什麼業界有這麼多的研發都集中在模仿藥,而不是創新領域?」我們真的需要「五間以上的藥廠生產相同的藥嗎?」然而,愛德華的問題能以一個熟悉的論點回答,「一九四○年起,重大的製藥進步多數是透過分子改良來實現,而不是指標性的基礎研究。」換句話說,模仿並沒有和創新相牴觸,它其實是創新的關鍵。
有些醫師則以個人化醫療的邏輯來為模仿藥辯護。一種療法不能適用於所有人,這是臨床醫學的老生常談。某位精神科醫師在尼爾森聽證會上說明,模仿藥能在治療領域產生必要的變異性。當我們批評模仿藥的同時,我們也要衡量這些藥物「能提供醫師在選擇上的彈性,讓他們找出最適合病患的藥物。」如果沒有這麼多種藥效相近的藥物,醫師就少了為病患量身訂做個人化治療的自由。某位加州開業醫師在一九七六年以〈模仿藥有立足之地嗎?〉為名向《私人診療》投書,他提到,如果沒有模仿醫療,那我們擁有的就是極權醫療(totalitarian medicine);「某些極權國家只生產一種車。它的價格高得離譜,製造過程馬虎,交車時間也遙遙無期。除了消費者以外,沒有任何人在乎。」這些對模仿藥的辯護保有席勒在十年前(或克蘭茲在二十年前)的主張要點。不過,把這種同樣邏輯的攻防戰視為純粹的連續現象是錯誤的。七○年代後期,模仿藥的爭論不再著重於專利系統的全面修訂,而是逐漸連結美國醫療當中更具威脅性的、更嶄新的相似性邏輯,也就是對「同療效替代」的探索。
美國醫學會與製藥商學會強烈抵制同療效替代的概念,以各種方法來否決藥物分類能代表療效相等性的想法。當然,並不是所有藥物分類都像第一代頭孢菌素那樣能自由互換。在他們重新部署以對抗同療效替代時,國家藥學理事會在另一類神奇藥物中發現了站在他們陣營這方的經典範例,那就是乙型阻斷劑(beta-blockers)。
替代政治學的再現
八○年代末,醫學領域與業界的遊說團體開始聯手合作,共同對抗同療效替代。美國醫學會藥物部(Department of Drugs)主任約翰.巴林(John Ballin)譴責同療效替代不道德地「篡奪了醫師特有的權力」;他在製藥商協會的同儕杰拉德.莫辛哈夫(Gerald Mossinghoff)也表達了相同的立場。在許多觀察者眼中,醫藥專業領域重演勢力範圍之爭似乎在所難免。就如某份藥學期刊的敘述:
同療效互換!戰線偵查完畢,主角與對手都向前線邁進。古老的復仇女神「替代」扮妝成「互換」,它們在治療的戰場上其實是相等名詞。做為醫藥專業者,我們非常習慣向癌症宣戰,與愛滋病搏鬥,控制關節炎,以及轟炸受瘧疾感染的叢林;因此,我們會為了這一小塊健康照護的地盤頑強奮鬥,也樂意在週六夜和其他專業者打得頭破血流。
類似十年前的學名藥替代,美國醫學會、美國藥學會與製藥商協會很難達成一個讓藥師、製造商、醫師與消費者都滿意的共識。不過,從六○與七○年代開始,他們的利害關係就發生了轉變。在八○年代關於同療效替代的論戰中,左右局勢的關鍵變成了生醫藥物之間更廣泛的可互換性,例如頭孢菌素與乙型阻斷劑,以及專業領域的地盤之爭,也就是有權力決定病患治療選擇的應該是醫師?藥局?還是健康照護系統本身?
同療效替代和學名藥替代不同,後者提倡的是以同等照護為前提的成本節制邏輯,而同療效替代則讓私人與公共支付者發揮更廣泛的作用,他們能建立規範或原則,來界定什麼樣的藥物對日常臨床實務而言是「夠好的」,即使這些藥物並不相等。而正是同療效替代在概念上的曖昧性,讓反對者也很難定義自己在反對什麼。某位評論者在一九八八年指出,「治療性互換的操作型定義是這場爭議中的重大難題。學名藥互換簡單得多,它要求藥品之間的化學性質、強度、劑型與生體可用率必須相等。它的主要論證牽涉的是評估生體可用率的方法學與頻率。相反地,療效相等性的意思是什麼,藥師又需要什麼樣的資料來做出知情決定?」治療性相等不是單一概念,而是從「相同」到「不相同」的概念光譜。第一代頭孢菌素相近到足以在某種程度上互換,乙型阻斷劑就完全不行。我們不清楚其他藥物會落在光譜上的什麼位置,也不曉得有誰或什麼方法能區分哪些藥物「好到」足以互換,而哪些則否。
模仿藥是二十世紀後期衛生政策爭論的重要部分,這些爭論也延續到了二十一世紀。模仿主義這種說法通常來自業界之外的批評。確實,藥廠廣告很少會把藥物市場的新產品宣稱為年度最重要的模仿藥。然而模仿藥並不是一無是處,包括席勒與更早的克蘭茲,他們都為模仿藥辯護。諷刺的是,如果世界上沒有模仿藥(也就是如果每個藥物分類底下都只有一種藥物),我們也沒有機會利用同療效替代來節省支出。
即使是最不信任製藥產業研發程序的觀察者也得承認,模仿藥時常提供了某些好處。在許多的藥物分類裡,包括乙型阻斷劑、他汀類藥物、H2受體拮抗劑到頭孢菌素,第一代藥品不一定就是最有效或最安全的。從科技史角度,以下這個情況更為普遍:第二或第三代產品出現在新的科技領域,它們的實用度通常遠大於原初的創新。科技史學者把第二波創新者稱為「工匠」(tinkerers),也就是吸收並改造第一代的創新想法,讓它更能被廣泛接受的人。然而,科技領域也充斥著計畫性報廢(planned obsolescence)的情節,這些新一代產品的相對價值越來越難計算,因為它們的成本更高,帶來的改進卻微乎其微。模仿或許是創新的必要部分,不過,模仿也能偽裝成創新,而我們幾乎沒有區別兩者的標準。
書籍資訊
書名:《便宜沒好藥?一段學名藥和當代醫療的糾葛》 Generic: The Unbranding of Modern Medicine
作者: 傑瑞米・葛林(Jeremy A. Greene)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18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