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不再覺得非得將失落的國家歸還給父母。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接受我的書寫不必如此任重道遠。這麼看來,《另一種語言》可說是我以成年人的身份所寫的第一本書,從語言的角度來看,也是我以孩童的身份寫的第一本書。

§變形記
文|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
譯|李之年
下筆寫這些省思文前不久,我收到了在羅馬的友人、作家多明尼哥.斯塔諾恩(Domenico Starnone)寄來的電子郵件。對於我想將義大利文佔為己有的渴望,他寫道:「新語言簡直有如新生命,文法和語法重塑你這個人,你套上另一種邏輯,另一種感情。」這些文字大大撫慰了我,也似乎和我來到羅馬後,開始書寫義語的心境不謀而合。一語道盡我的渴盼、我的徬徨。讀了這句話,我才更明白這股想用新語言表達自己的衝動:想讓身為作家的自己,變形。
約莫收到這封信的同時,我在一場訪談中被問到最喜歡哪本書。當時我人在倫敦,和其他五位作家在台上。我向來覺得這個問題很煩;我說不上最愛哪本書,所以從不知該如何回答。不過這次,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說我最愛的書是奧維德的《變形記》(Metamorphosis)。這是一本傑作,是涉及一切、映照一切的詩作。二十五年前,在美國讀大學時,我初次讀到這首拉丁文長詩。這場邂逅令人難以忘懷,或許是我這輩子最痛快的閱讀經驗。為了讀懂這首詩,我必須不屈不撓地翻譯每個字。我必須全心投入這個古老又艱澀的外語。即便如此,奧維德的詩文仍是擄獲了我的心:我為之迷醉。我發現了一本優美的作品、一個仍存於世間的迷人語言。就像我說的,我相信閱讀外語作品,是最切身的閱讀。
仙女達芙妮(Daphne)化為月桂樹的那一刻,我始終記憶猶新。她正拔腿逃離阿波羅,那個被愛沖昏頭而死命追求她的神祇。她只想獨處、守貞,致力於守護森林與狩獵,如處子女神黛安娜。筋疲力盡的仙女跑不過太陽神,遂向她父親河神帕紐斯(Peneus)求救。奧維德寫道:「才剛祈禱完,沉重感便蔓延她的四肢,她柔軟的雙乳被薄樹皮裹覆,秀髮化為樹葉,手臂化為樹枝;前一刻還健步如飛的玉足成了樹根,深扎入土,動彈不得,臉龐消失,化作樹梢。」當阿波羅把手放上樹幹時,「他感到她的雙乳仍在新生樹皮底下微顫。」
變形,是一段既暴力又復興的過程,是死,也是生。何為仙女終,何為樹始,不甚清楚;這一幕之所以優美,是因為它描繪了兩個元素、兩種生命的融合。形容達芙妮和樹木的詞毗鄰並列(在拉丁文本中,frondem/crines,ramos/bracchia,cortice/pectus;樹葉/秀髮,樹枝/手臂,樹皮/雙乳)。這些詞語相鄰相似,文學意涵並置,更是強化了衝突、交纏的意境,給了我們雙重印象,令人撲朔迷離。以神秘、原始的意象,描寫同時身為兩物的意涵。身為不明、矛盾之物的意涵,具雙重身分的意涵。
尚未變形前,達芙妮都在拼命逃生。如今她停了下來,再也動不了。阿波羅碰得了她,卻無法佔有她。雖然殘酷,但變形是她的救贖。一方面,她失去了獨立性。另一方面,化為樹木的她,得以永遠在森林、在她的家生活。在這裡,她得到了另一種自由。
如先前所說,我認為我書寫義大利文,是在逃逸。我剖析我的語言變形記,發覺我是在試圖逃離什麼,試圖解放我自己。用義大利文寫作快兩年了,我覺得我已脫胎換骨,幾近重生。但這個改變、這個新的開始,代價高昂;就像達芙妮,我也發現自己受著裹縛。我無法像從前一樣行動自如,像用英文時那樣游刃有餘。如今義大利文這個新語言,有點像樹皮似的包覆我身。我仍在裡頭:重生、受困、安心、忸怩。
我為什麼要逃?有什麼在追我?誰想限制我?

最明顯的答案,是英文這個語言。但與其說是英文本身,不如說是英文對我來說所象徵的一切。英文在我這輩子代表了激烈的掙扎、磨人的衝突,讓我一直感到失敗,幾乎是我所有焦慮的根源。它象徵了一個我非得去精通、去理解的文化。我怕它讓我和父母撕破臉。英語是我過去沉重、累贅的一面。我厭倦了它。
然而,我卻與它墜入愛河。我成了英語作家,然後一夕成名。我獲了獎,但我有自知之明,自覺不配得這個獎,獎似乎頒錯人了。雖然與有榮焉,我仍是有所懷疑。我覺得自己配不上這個獎,然而,它還是改變了我的人生。從此以後,我被視為成功的作家,我也不再覺得自己是個沒人知曉、幾近無名的學徒。我的作品全來自一個我覺得看不見、到不了的地方。第一本書出版後過了一年,我卻不再默默無名。
我想,我是藉著書寫義大利文,來逃避我和英語交手的失敗,還有自身的成功。義大利文給了我一條截然不同的文學路。身為作家,我可以砍掉重練。我大可組合文字、鍛詞鍊句,也沒人會把我當專家看。用義大利文寫作,我注定要失敗,昔日的挫敗感折磨我,令我傷透了心,這次我卻不為所動。
要是提到這些日子我都在用新語言寫作,不少人會不以為然。在美國,有些人甚至建議我收手。他們説,不想讀我從外語轉譯的作品。他們不想要我改變。在義大利,雖然有許多人鼓勵我放手一試,也有許多人支持我,還是有人問我為何要用遠比英文小眾的語言來寫作。有些人說,我就這麼和英文一刀兩斷,搞不好會一敗塗地,這樣逃避,或許會弄巧成拙。他們不了解我為何要冒這個險。
這些反應我並不意外。改頭換面常被視為是種背叛、威脅,尤其是刻意求變。我是個守舊不變的母親的女兒。在美國,母親的衣食行仍盡量照舊,思考及生活方式也是,彷彿她未曾離開過印度加爾各答。她靠拒絕改變樣子、習慣、態度,來抗拒美國文化,來維持她的自我。成為美國人,或甚至像美國人,就代表輸得一塌糊塗。母親回到加爾各答時,即使離開印度將近五十年,看起來仍像個從未離鄉的當地女性,她也引以為傲。
我則和她相反。母親的反骨是拒絕改變,我的反骨則是堅持要改變自己。「有名女子⋯⋯想變成另一個人」:我以義大利文寫的第一篇故事「換衣記」,開頭就是這麼一句,其實並非偶然。我這輩子都在拼命逃離自身根源的虛無。令我受盡煎熬、我想逃離的,就是那片虛無。所以我永遠都對自己不滿意。改變,似乎是唯一的解決之道。藉由寫作,我發現了藏身在故事人物中、逃離我自己的方法。找到了一再變異的方法。
生命中唯一不變的元素,可謂變形的機制。每個人、每個國家、每段歷史時代的旅程,都是由千變萬化組成的,整座宇宙及宇宙涵蓋的一切也是。變化時而細微,時而深刻,若非萬變無窮,我們就會停滯不前。轉化的瞬間,有什麼改變了,那一瞬,便是我們所有人的支柱。無論是救贖,還是落失,這些都是我們常會銘記於心的時刻。它們讓我們的存在有條理。其餘種種,幾乎全遭遺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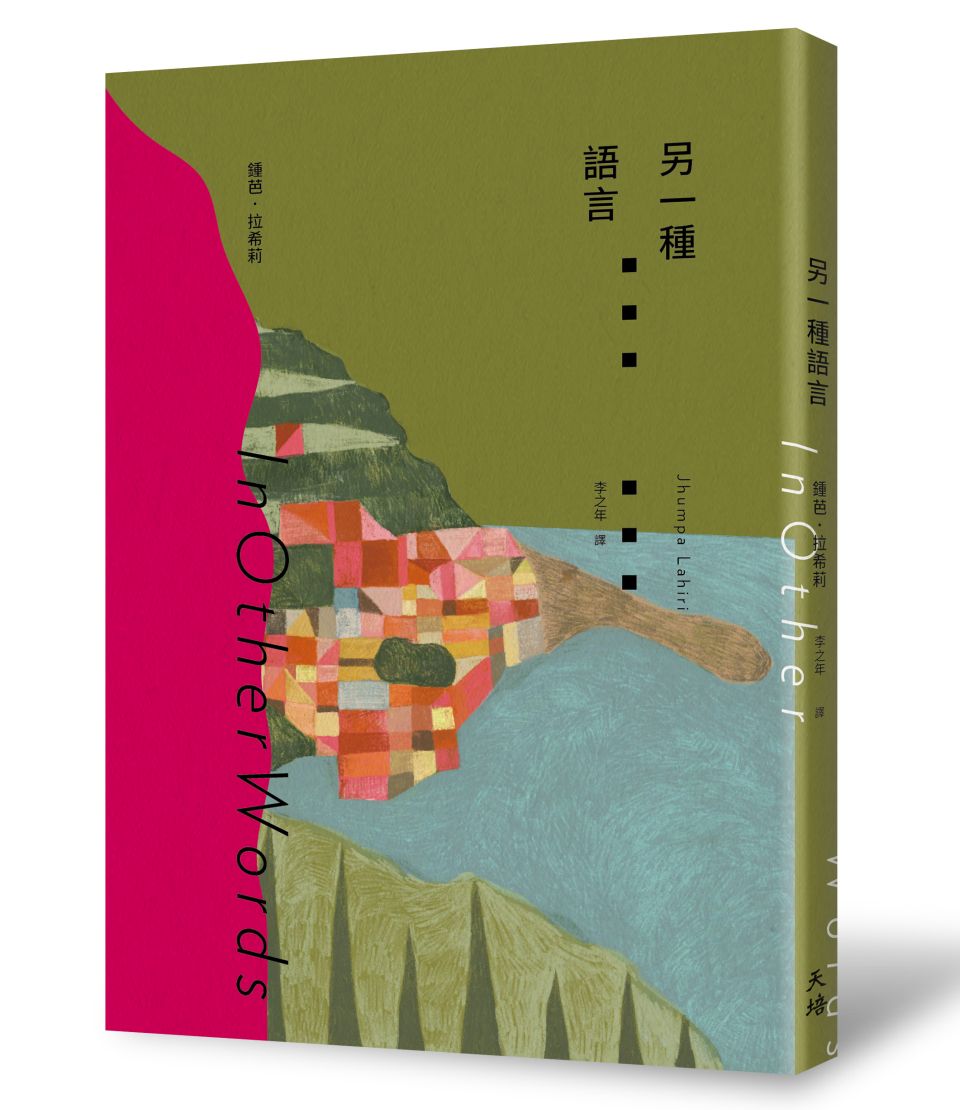
我認為藝術的力量,是喚醒我們、使我們刻骨銘心、改頭換面的力量。讀小說、看電影、聽音樂時,我們在找尋什麼?經由藝術作品,我們在找尋某種改變我們的東西,過去未察覺到的東西。我們想變形,如同奧維德的傑作使我變了形。
在動物界,變形是可期、自然的。是一段生物歷程,期間歷經各種特定階段,最後才大功告成。毛蟲變身為蝴蝶後,就再也不是毛蟲,而是隻蝴蝶。變形的影響劇烈、恆久。生物褪下舊軀殼,換上幾乎認不得的新形體。具備新的身體特徵、新的美、新的能力。
就我而言,完全變形是不可能的。我可用義大利文寫作,卻無法成為義語作家。即便我現在正用義大利文寫這句話,我身上生來書寫英語的那部分,卻持久不墜。我想起費爾南多.佩索亞(Fernando Pessoa),這位作家創造了四個版本的自己:四名截然不同的作家,正因如此,他才能突破自身侷限。
說不定,我以義語書寫的作法,就像他使的招數。成為另一個作家是不可能的,但成為兩個作家,說不定有可能。
怪的是,用義大利文寫作時,我覺得更受保護,即使也更無遮掩。新語言的確包覆著我,但有別於達芙妮,我可是永遠被覆蓋住,我幾乎沒有皮膚。雖然我沒有厚實的樹皮,但在義大利文中,我是個更強韌、更自由的作家,再度生了根,只是以不同方式生長。
書籍資訊
書名:《另一種語言》 In Other Words
作者: 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
出版:天培
日期:2018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