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來這裡是要幫助我,那你在浪費時間。但如果你來是因為你我生命的解放緊密相連,那我們便一起努力。」-莉拉‧華生
親愛的愛麗絲‧高夫曼教授,
在說任何事和介紹我們是誰與來自哪裡以前,我們先引用一位女士的話,她的話語是我們將與你談論極其重要內容的根基。這封公開信受到莉拉‧華生(Lilla Watson)的啟發,大致傳達我們對你最近出版的著作《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的疑慮。除了你的研究和作品外,我們擔憂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對種族和階級問題長期存在的問題研究,我們也身處該領域,而且普遍涉及知識生產的政治層面。我們希望你認真看待我們接下來說的話,我們也邀請你在未來以不同方式對待你的研究。
接著,容我們自我介紹。我們就讀於新學院的尤金梁學院,修讀雅斯基蘭‧迪隆(Jaskiran Dhillon)教授的民族誌和質性研究課程的學生小組。我們之中有些人年紀稍長,也有些較年輕,但我們都是移民,也都是本地人;我們主修全球研究,也不是墨守成規的學生;我們是黑人、拉美裔、白人和介於之間的混血。我們寫信給你,是由於你的著作讓我們所有人深感不安。我們寫信給你,是希望你能思索我們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和強烈指控訴求,以推動超越學術現狀。我們寫這封信,是迫切要求對你的著作給予高度評價的社會科學領域,在知識生產上進行根本性轉變。我們——下一代的學者、藝術家和組織者——以抗議形式寫出這封信,作為一場行動的號召,作為一個拒絕追隨你的腳步的集體。
我們被分配到《全員在逃》作為當週閱讀的家庭作業,利用在家或坐地鐵或課餘時間讀完。當我們第一次看到它,並不知道它是危險的文本。我們的教授雅斯基蘭‧迪隆博士只告訴我們它是「有爭議的讀物」,她選擇不為爭議點加油添醋或說出某些人討厭它的可能原因,她希望我們獨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
那個週三早晨我們在課堂上見到彼此,氛圍和往常很不一樣。空氣變得凝重,燈光也顯得刺眼。我們屏住氣息面對面坐著不發一語,沒有人想第一個站出來發表意見:關於此書的某個點、許多段落,那些讓人覺得不對勁的地方。
我們的教授提出了第一串問題:
愛麗絲‧高夫曼是誰?
你知道她為什麼寫這本書嗎?
她認為這本書能為世界帶來什麼作用?
她如何定位自己作為與主題有關的研究者?
幾分鐘後,我們討論了這些問題,但問題過於龐大,還是沒有人願意出聲。最後,有人低聲說:我不知道該不該相信她。
迪隆教授繼續問。
為什麼呢?
房間再次嚴肅起來,我們接二連三發表意見說出不舒服的原因,針對我們在書中不同段落所找到的疑問和不信任根源。
《全員在逃》意圖提供一部民族誌,「紀錄費城一個相對貧窮的黑人社區裡生活的年輕人,對於高監禁率和更隱密的治安與監控做法的經歷和理解。」然而,這種盡力理解的成果缺乏某些關鍵要素。針對費城黑人反抗和被剝削的廣大歷史背景,《全員在逃》只用八頁篇幅簡短介紹帶過。而作者反覆使用「黑鬼」一詞,並沒有明確表達她對該詞的態度、背後意圖,或者可帶來任何批判性反思的廣泛影響力。

作者的社會地位為何?
一名年輕白人女性——著名社會學家的女兒——撰寫了此書。她成長於費城最富有的地區,從常春藤盟校畢業拿到本科和研究生學位。她坦承進行「計劃」前,對於毒品戰爭和犯罪戰爭「只有模糊的認知」。
這與研究有何關聯?
教授敦促我們從不安與不信任的地方開始解決這個重要問題。我們很快地達成共識:這是一個危險的文本——而且不止單一層面如此。
高夫曼教授,我們認為,你出版的這本廣受讚譽又入手容易的著作是危險的。它洩漏了你調查對象從飽受圍剿的生命困境中奮力倖存下來的策略,即便你刻意使用了化名。《全員在逃》有直接危害到這個費城社區的可能,但你卻只把它當成「紀事」。實際上,你的書破譯了他們在艱困中發展出來的生存策略,轉譯這些黑話的結果,是讓他們更容易被警察跟國家的其他幹員掌握。而此前你在書中所說的,那些造成他們困境的物質結構,白人的優越與殖民化的資本主義,卻被一筆帶過。你把你的「發現」說成「新的」,卻幾乎忽略了關於黑人的學術討論,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早就處理過諸如「亡命者」、先關人再說的思維、以及準軍事化監控等主題了。
高夫曼教授,我們好奇你覺得你的目標受眾是誰?他們不可能是西費城的人。不是麥克、不是查克,更不是你《第六街》所寫的其他年輕人、婦女和孩童,而是那些你必定與他們保有最低限度聯繫的人。你的書更不可能是為了讓費城的黑人社區受益,或者國家裡的其他類似社區。
你是對同溫層的人寫《全員在逃》嗎?為那些白人研究者、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個偷窺視角,讓他們得以窺視那些從未見過的現實嗎?你是否曾經想過,那些人在歷史上(並持續至今)無視和犯下相同暴行打壓黑人社區,而你卻聲稱會帶來光明?
你被譽為「傑出的田野工作者和才智過人的分析家,其著作應該讓所有人閱讀,包括歐巴馬總統、國會議員和全國各地的政府官員。」高夫曼教授,這些讚美讓我們深感憂慮。《全員在逃》絕對稱不上「優良」的民族誌研究、參與式觀察和身歷其境的學問。克莉絲緹娜‧沙爾佩(Christina Sharpe)2014年針對此書的評論分析文章〈Black Life, Annotated〉便傳達過類似的觀點:
靠著它的「原汁原味」,《全員在逃》看來還可以像迷你影集或彩蛋一樣,可以開出各種副本,靠著鼓吹黑人敘事,靠著對物質性壓迫的錯誤認識,再走一段路。我已經預見這本書將被選進新生的通識閱讀書單,全美那些歷史悠久,但黑人教職員學生卻少的可憐大學學院學生,都會讀到這本書,然後把《全員在逃》的研究倫理與研究方法,如實再操作一次,這就是權力關係與實踐。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大學院校,《全員在逃》肯定會變成一本教你如何身歷其境進行「城市民族誌」的入門書。於是,希維婭‧溫德(Sylvia Wynter)所說的,黑人在敘事上的被譴責地位,就會這樣根深柢固下去。
此書不是其他學者應該效仿的對象。作為新一代民族誌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藝術知識生產者的一員,我們不能接受現在的社會科學標準,因為它們現行的結構受到新自由主義白人霸權所支配和維繫。
《全員在逃》於2014年4月4日出版,非常接近三名支持改革的黑人組織者——Alicia Garza、Patrisse Cullors和Opal Tometi——在2013年7月正式開始的「珍視黑人生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一周年。高夫曼教授,這場運動讓你有近十個月時間重新審視這本書,「珍視黑人生命」可能會激勵你停下腳步思考;去接觸在費城第六街服務的地方組織(那些在你書中完全沒有提及的組織);捫心自問這本書該如期出版還是停住,而不是擅自假設它該出版。
你是否在田野調查之外進行過額外研究,以增進你對費城歷史與政治背景的瞭解?在出版這本書的前後,你是否有和第六街的社區成員建立交流與責任承擔?你是如何獲得和維持他們的同意?你如何證明對社區的政治承諾?
高夫曼教授你是否想過,你成功的代價可能是兒童、青少年和第六街家庭的安危?你進入他們的家園、他們的社區和他們的生活。他們歡迎你,因為你只是一個躺在沙發睡覺的過客。你是白人、富人和外來者。你解密並暴露他們為了在監獄式社會的持續壓迫和虐待下生存,而被迫發明出來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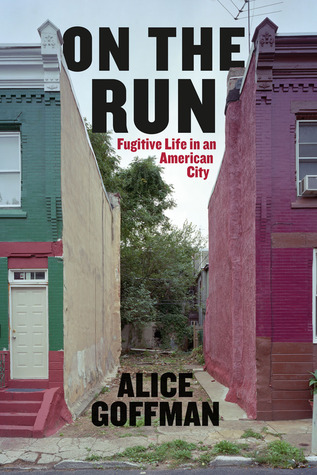
高夫曼教授,我們最後提出這個問題:你是否曾在最一開始為這本書想想?
在我們看來,簡短的回答是「沒有」。長篇大論的回答——肯定的答案——需要深入而徹底地考量,關於是否有可能制訂適合這種性質的調查,一種合乎道德、反殖民模式的民族誌。
這將需要更多的民族誌學者努力,與那些直接以反殖民主義角度處理學術問題的人進行接觸,例如克莉絲緹娜‧沙爾佩、艾米‧梅雷迪思‧考克斯(Aimee Meredith Cox)、莎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琳達‧圖希沃-史密斯(Linda Tuhiwai-Smith)、奧德拉‧辛普森(Audra Simpson)和桑迪‧格蘭德(Sandy Grande)等人。而且它需要更明確的道德和透明度規範,以及相互問責的原則,使研究有機會讓「被調查」的人和社區有益,而不僅僅是作者。
高夫曼教授,我們從你的書中瞭解到你的讀者也涉及各種知識生產模式。讀者——尤其是那些和你一樣的白人——需要密切關注上面對《全員在逃》所提到的關鍵問題,他們必須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尖銳又關鍵的自我反思問題:那些涉入或牽扯到我的研究的人,他們究竟面臨著什麼樣的危險?我自己的身份、生活經驗,以及對社區或問題的態度,將如何影響我的研究和進行的方式?無論是短期或長期,我的責任底線在哪裡,我該如何尊重他們?我該如何透過這項研究,重新銘刻統治的殖民關係?有哪些反殖民方法能更貼近我的研究?
署名
-尤金梁學院修讀雅斯基蘭‧迪隆教授民族誌和質性研究課程的學生,全球研究專案,2018年春季。
參考報導:Public Seminar
書籍資訊
《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愛麗絲‧高夫曼,2018[台灣中文版]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