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釋中產階級子弟為何從事中產階級工作,困難在於解釋別人如何成全他們; 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從事工人階級工作,困難卻是解釋他們為何自甘如此。」──保羅‧威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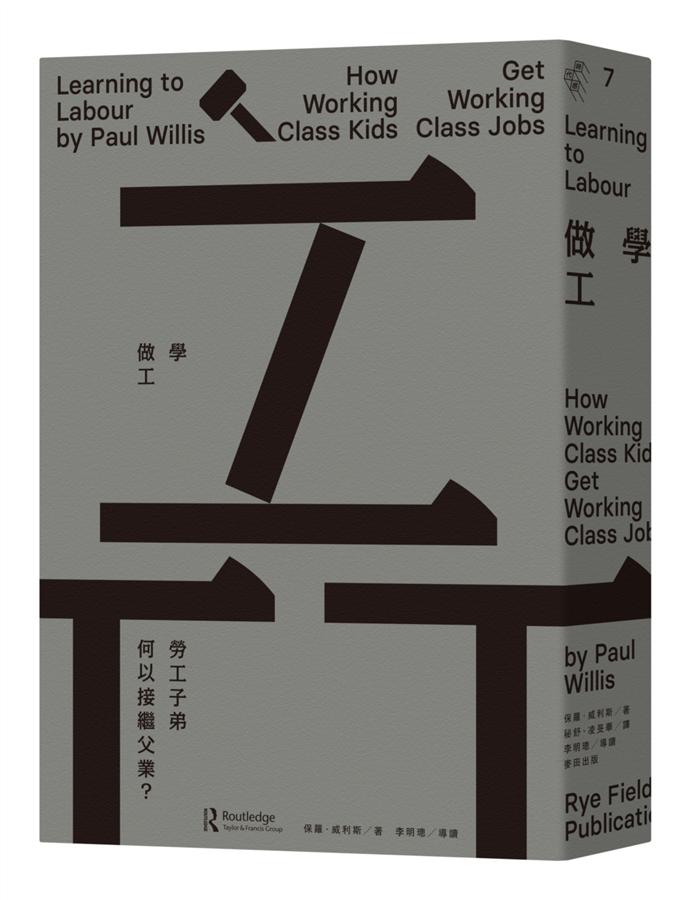
《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繁體中文版書封。
為什麼勞動階級無法向上流動?對於這個問題,存在著一種結構面向的解釋:資本主義的體制,藉由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限制了勞動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藉此維持了資產階級的優勢地位不被挑戰。同時,這樣的結構性解釋也經常同時搭配意識形態的解釋,意識形態的作用讓勞動階級「誤以為」體力勞動工作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選擇,或者認為他們別無選擇,「心甘情願地」接受這樣的「選擇」。
威利斯(Paul Willis)並不滿意這樣的解釋,在《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Learning to Labou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一書中,他關心的問題是:為什麼勞動階級的後代,會「願意」甚至是「樂意」從事勞動階級的工作?這樣一個在世代之間複製不平等,心理認知與行動上的特殊稟賦(disposition),是如何形成的?
威利斯從漢姆頓鎮(Hammer Town)的某所中學中,挑選了十二位出身勞工階級家庭的學生,觀察他們的課堂表現與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並與之安排了團體訪談與非正式訪問,同時也對學校教師與學生家長進行了深度訪談。威利斯以細緻的民族誌田野方法,運用這些訪談資料,分析了這些勞動階級的後代,是如何形塑了自身的「階級文化」,威利斯稱之為「反學校文化」。
威利斯用「反學校文化」來指涉這些他稱之為「小伙子」(the lads)的勞動階級後代,透過反抗學校規訓,所形塑出來的群體文化。例如,他們對學校的教職人員懷有敵意,除了少數的「麻辣教師」外,小伙子原則上將學校教師都視為敵人,不認為這些人是模範或學習的對象。
另外,而無論他們出於什麼原因無法適應學校規訓,反學校文化強化了小伙子對學校規訓的反抗。例如用上課不專心、放棄學習或打瞌睡等方式,刻意消極抵制課堂學習的種種行為。小伙子認定,課堂上的學習無法對他們的未來有任何幫助,師長們的「諄諄善誘」,不過是為了強化他們對權威的服從。一言以蔽之,學校唯一教給他們的,只有「管教」。
反抗學校規訓的文化,讓小伙子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人」的黑話,他們也嘲弄順從學校體制的「好學生」是「書呆子」(the ear’oles),認為自己比那些人更「屌」,這些「夠屌」的具體行為包括不穿制服,特立獨行的時髦裝扮、抽菸喝酒等「成年大人」做的事,以及拿自己的性經驗與交往經驗出來說嘴或誇大。
為了排斥學校規訓文化,小伙子用各種「活動」將空閒時間填滿,像是在外打工、抽煙喝酒、惹是生非等等,把學校的影響降到最低。所有的學校訓導都是管教,都是要小伙子們向體制低頭的權威,他們樂於違反校規,用打破規則抵抗體制。
由於出身勞工家庭,勞動階級的文化也深刻影響著他們。他們反抗管教的行為,多半不會受到太嚴厲的懲罰,而當作好玩、有趣、無傷大雅甚至是男子氣概的表現。家長對反抗管教行為的忽視(ignorance),又反過來強化了小伙子的反學校文化。
另一方面,由於普遍的家境困難。利用課餘時間打工賺取外快以維持家計,經常是小伙子共同的生活體驗。「打工」讓他們自認比乖乖牌同儕更社會化,「出過社會」更有「社會經驗」,這是學校「學不到的」事情,甚至,打工的體驗也比學校枯燥的學習更有趣。
小伙子藉由反學校文化而得到自主性。他們相信他們比學校中提早喪失自我的乖乖牌更「屌」、看不起學校老師與其代表的教育體制、為了展現男子氣概,外出打工,建立「提早出社會」的優越感與自我認同,而這樣的心理優越感與實質上的物質報酬(工資)又反過來支持他們心中的反學校文化。
這種種反抗學校規訓文化的體驗,在小伙子們的日常生活中創造出各種區分(differentiation):「社會的」與「學校的」、「勞動陽剛的」與「乖乖牌娘砲的」,結果是對於體力勞動與與男子漢氣概的崇拜,以及對勞心工作的輕視。
小伙子對於學校規訓文化的抗拒,對於勞動體驗中陽剛氣質的強調,導致了他們傾向偏好勞動工作的行動稟賦,而這樣的行動稟賦,使他們在工作的選擇上也傾向於選擇強調肌肉、體能、用勞力賺取金錢的工作,而非「坐辦公桌」的「娘娘腔」工作。
威利斯認為,這些小伙子確實「參透」(penetration)了資本主義體制的謊言,他們的反抗,其實意外揭露了學校這個資本主義「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真相:學校的規訓體制是替優勢的中產階級服務,在教學的安排上不僅較為契合中產階級的家庭教育,鼓勵從事勞心工作而非勞力工作,也反映了學校體制對職業選擇的評價標準。校園中充滿各種規訓的環境,確實就像小伙子相信的那樣,從來都不是「自主成長」的空間。
但是,小伙子透過浸潤反學校文化出來的抵抗行為,真的顛覆了資本主義的階級再生產嗎?威利斯強調,小伙子在學生時期透過「成功」抗拒學校體制所培養出來的稟賦,其實也促成了資本主義的階級再生產。將勞動區分成勞心工作與勞力工作是其一,反學校文化所培養的稟賦,也讓小伙子無形間接受了「男主外、女主內」刻板性別分工,無形間鞏固了父權體制,這些都阻礙更能抵抗資本主義體制,勞動者之間更廣泛的團結。更重要的是,他們對男子氣概陽剛氣質的崇拜,也讓「反學校文化」與工人文化銜接起來,與「很娘」且「不事生產」的勞心工作相比,小伙子更傾向於接受更需要體力與技術的廠房勞力工作。
威利斯強調,小伙子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參透」,其實只是「局部的參透」。反學校文化浸潤出來的「參透」,最後弔詭地造成階級複製的結果。局部的參透讓小伙子無法看見藍領階級工作中的階級壓迫,離開學校進入工廠的他們,用男子氣概與英雄主義來面對與處理勞動困境。集體的階級困境被化約成個體的適應問題,小伙子最終沒有真的挑戰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與社會結構,他們拿起磚頭往牆上砸,想把高牆打破,但最後的結果是牆被砌得更高、更堅固。
如果資本主義體制需要阿圖塞稱之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教會、媒體以及,該書討論的學校)以再生產階級,那麼威利斯的研究所強調的是,涉及日常生活與主觀認同的「生活體驗」(lived experience)。對於這些型塑勞動階級的文化稟賦,相當程度讓他們無法翻身,Oscar Lewis稱之為「貧窮文化」的東西,小伙子既沒有抗拒,也不是被動接受。相反,他們早在進入廠房工作之前,就已經「欣然」接受了他們「引以為傲的」反學校生活經驗。威利斯透過「生活體驗」來處理「階級文化」的主張,也呼應了Bourdieu對於「慣習」( habitus)的見解,也就是強調在整體結構中,行為者那些具體,「自然而然」習得的生活體驗,對於再生產結構的重要性。行動者的能動性(agency)與結構相生相成的具體過程,都透過文化作為一種具體生活體驗的中介得以呈現。
最後,本書成書的年代,是一個以福特主義規制勞動的年代。而時至今日,伴隨勞動體制的彈性化,會為反學校文化與廠房文化之間的穩定銜接,帶來什麼樣的衝擊與轉變?而產業型態多樣化自然也讓原本單一的「工人文化」更為歧異,面對形形色色,在不同場域中生成的「生活體驗」,威利斯所主張的「文化研究」,勢必也需要與時俱進。
威利斯在2004年所編的論文集《新時代下學會勞動》(Learning to Labour in New Times),就有許多關於當代社會的討論。雖然《學勞動》已成書超過三十年,但其所提供的理論視角語言就取向並沒有過時,也持續激盪許多新的討論議題,值得我們作為當代社會政治文化研究的參考。
(本書隸屬於MPlus與文化部合辦之第一屆青少年評論文學獎指定書單)
書籍資訊
書名:《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Learning to Labou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作者: 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
出版:麥田
日期:2018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