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奎格‧史蒂芬森(Craig E. Stephenson)
譯| 吳菲菲
佛洛伊德從未在著作中提到盧登,但他在〈論一個十七世紀附身精神官能症案例〉(A Seventeenth Century Demonological Neurosis,1923a)論文中曾用精神分析方式詮釋過一起驅魔個案。一個名叫克里斯多夫.海茲曼(Christoph Haitzmann)的巴伐利亞畫家在一六七七年來到維也納附近的瑪麗亞小教堂市(Mariazell),希望有人幫助他擺脫他與魔鬼所簽、為期九年、即將到期之兩紙契約所帶給他的幻覺和痙攣之苦。有如隆恩和盧登的案例,巴伐利亞的這個案例以死亡——海茲曼父親的死亡——以及親人轉變為可幻見的邪靈為起因。海茲曼用一系列畫作描繪了他亡父逐漸轉化為魔鬼的過程(這魔鬼長有一對乳房、手上還捧了一本打開的書)。透過驅魔儀式,海茲曼覺得自己擺脫了他與魔鬼簽定的那兩紙契約。然而,他最終並沒有重拾繪畫生涯,反而選擇了出家、走入修道院。
在佛洛伊德的詮釋中,這個案代表一個有精神官能症的人想要逃避那令他又愛又恨的父神意象——就是這意象使海茲曼無意識地抗拒失去親人和被棄的痛苦感受。佛洛伊德認為:海茲曼逃避了對生父的悼念責任,藉出賣靈魂給魔鬼來賦予自己一個新的角色、成為另一養育者的兒子和順臣,以便停留在傳統伊底帕斯情結中而無需在成人年紀為喪父感到痛苦。佛洛伊德也認為,藉兩紙契約以臣服於魔鬼父親的海茲曼採取了一種「陰性姿態」,讓他能以飽受威嚇的「兒子」身分自居達九年之久。這說法跟佛洛伊德在一九一一年論史瑞伯(Schreber)陰性策略的那篇著名論文十分相似,即使史瑞伯經歷到的心理問題是妄想症,而非關乎魔鬼的精神官能症。照佛洛伊德的看法,海茲曼的附身精神官能症(demoniacal neurosis)使他能繼續以家臣和兒子的次等身分自居並自覺受到保護,即使他必須為此付上高昂的心理代價並承受痙攣、幻覺、和創造力受阻的種種痛苦——這些痛苦在九年後終於匯為危機,把他引至以聖職為形式的另一種保護之中。
佛洛伊德在此所做的精神分析乃出自他的一個理論:人在潛抑難堪的感覺和思想時反使它們對人更為不利,因為雖無法被意識察覺,它們仍朝著意識進犯而來。佛洛伊德熟知《邪巫之槌》這本書,並在寫給同事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信中提到,他在中邪女人及歇斯底里症患者、宗教審判官(驅魔者)及分析師、魔鬼及被潛抑之情感間所見到的相似處(見佛洛伊德論文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1923b,頁41-43;以及Letters to Fliess,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七及二十四日)。他從心理利害得失(psychological economies)的角度提出一個理論:那些被用來持續迴避精神官能症的手段——如海茲曼所採用的——會對人造成重大傷害,因為潛抑(repression)會竊走自我通常容易取得的慾力(libido)。
在〈悲悼與憂鬱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1917)一文中,佛洛伊德描述喪失親人的自我如何「噬食」cannibalize)和「吸化」(incorporate)失去的對象,藉以否認對方已死的事實。他說:在有益心理的悲悼之中,自我既需內化、最終也需驅逐這被吸收的對象。患憂鬱症的自我則發現自己被這對象取代並受其掌控、以致瀕臨毀滅而毫無翻身之日。海茲曼就是如此吸化亡父而使之復活的,以致他的自我必須苦嚐惡魔的淫威達九年之久,直到他透過驅魔方式試圖擺脫病態。基於這些理由,佛洛伊德認為:海茲曼設法脫離魔鬼的擺布而進入天主教僧會雖代表了他的進步,但仍是精神官能症患者的逃避手法,因此意謂他仍未擺脫魔鬼的控制——他放棄繪畫生涯、進入與世隔絕之僧會的決定,實際上延續了他的神經質自我分裂(neurotic splitting)。他的自我在某種意義上依然為某種神靈所掌控,因為他第三度讓位給了一個存在於無意識中的崇高父親意象,並未宣示自己的空間權和坐在自己的王位上。
我想根據佛洛伊德為海茲曼個案所做的精神分析在此做些推演。我猜他會認為盧登的中邪者也採用了附身精神官能症者的策略。懺悔師穆索神父的死亡時間幾乎同於悲痛的鬼魂向瑪特修女初次顯現的時間,因此我認為:佛洛伊德會把瑪特修女心理上「詭異的」(uncanny)悲傷經驗歸因於被潛抑之幼兒情結(infantile complexes)的復起、這些情結所施展的鬼祟力量、以及無從確認真幻或善惡的判斷力(Freud,1919)。在隆恩市的妮可.歐布里案例上,佛洛伊德應會認為歐布里對親人的悲悼——也就是吸化或內化一個代父型人物(祖父)的意象——是必要和有益的,但教會的論述卻將之劃歸為邪靈附身之類。另外,由神父鬼魂變身而成的魔鬼意象附著在瑪特修女身上後,懺悔師米農神父就愈來愈有必要成為現身照顧和保護她的代父,而這便為她的疾恙帶來了佛洛伊德所說的「附帶好處」(secondary g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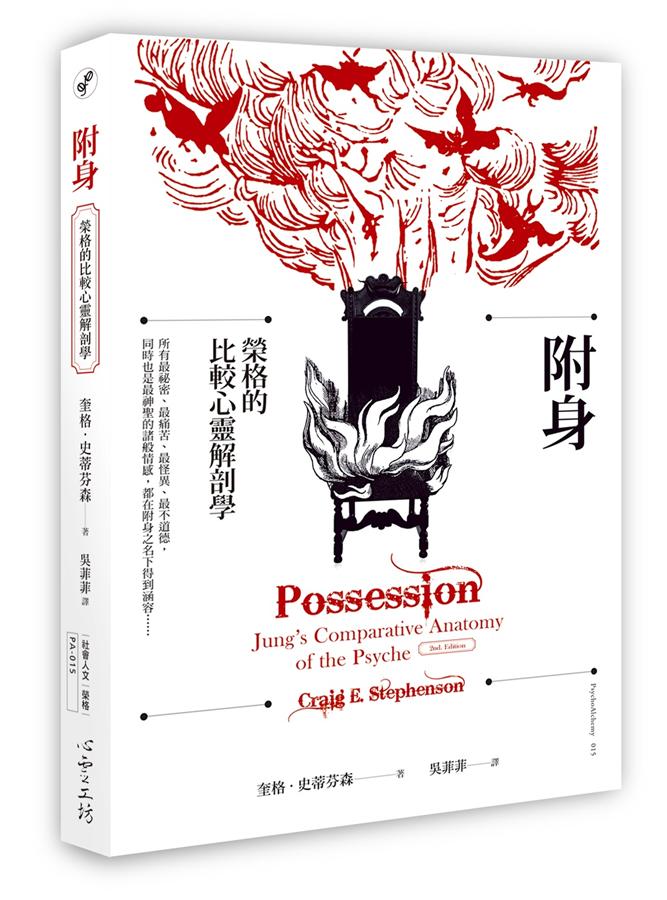
佛洛伊德從未提及盧登邪靈附身事件,不過榮格倒曾提過它們——但也僅只一次,是一九四五年他應《瑞士歷史大辭典》(Th e Schweizer Lexikon) 之出版商的要求寫「惡魔附身」(demonism)之定義時發生的:
惡魔附身(或稱中邪)係指一種奇異心態,特點在於:某些心靈內容(或所謂的心理情結)取代了自我並至少在短時間內掌控了整體人格,以致自我無法運用其自由意志。自我意識也許會出現在某些這類心態中,但在其他情況下都遭到覆蔽。惡魔附身是發生於未開化心靈中的現象,往往發生於落後情境中(《新約聖經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四節、《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三節及第五章第二節等都有很好的描述)。惡魔附身並不全是自發現象,可經人蓄意誘導而以「迷恍狀態」(trance)的形式呈現,如薩滿巫術(shamanism)、靈媒術(spiritualism)等所示於人的。從醫學角度來看,惡魔附身有一部分屬於精神官能症(psychogenic neuroses)的範疇,另有一部分屬於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的範疇。
惡魔附身也可能具有傳染性。中古世紀最著名的一起流行疫情是一六三二年發生於倫登(London,此為榮格筆誤)吳甦樂會修女的附身事件。這流行病情以經由誘導而發生的集體精神錯亂為形態,本質上具有宗教或政治目的,與發生於二十世紀的集體精神錯亂相類似。(Jung,1945c,段 1473-1474)
榮格用他的心理情結理論來解釋惡魔附身現象。對他來講,具有情感色調的心理情結是意義匯集之某種情感所寄附的一個意象,而這意象無法與自我的慣習態度相容。心理情結常出自心靈創傷(心靈某小部分遭到削減)或道德衝突(主體無法確認自己生命具有一致性),因而它是心靈解離出來的碎塊,但具有驚人的自主性和內凝性,有如出現於意識內的一個活躍外來體,足以推翻意志(或決斷力)並妨礙記憶力。與無法察覺之心理情結發生衝突的自我是頗感無力的。在〈回顧心理情結理論〉(A Review of the Complex Theory)這篇論文中,榮格明白地把附身解釋為「短暫且不自覺、在與心理情結認同時產生的人格變化」,雖然「自我被情結吸收」這個反過來的說法也同樣能適恰表達這一轉變(Jung,1934a,段204)。
對榮格來講,佛洛伊德是第一個用個案證明「一旦用心理學說法取代教士所幻想的『魔鬼』,我們就會發現心理學和中古世紀之看法並無二致」的人(Jung,1939b)。榮格承認佛洛伊德的見解源自夏柯(後者認為歇斯底里症狀即意念「霸占大腦」的現象)以及詹內(在《精神官能症與執念》一書中,他曾就夏柯的附身與纏念之說做了更深入探討)。但不同於「講究理性的詹內」,榮格認為:
佛洛伊德和布洛爾並沒有掩飾他們的說法與附身之說十分相似,反在追隨中古世紀理論之際捕捉到了附身的起因,因而得以——可以這麼說——驅逐惡魔。他們發現致病的「意念」實際上無異於他們名之為「創傷事件」的記憶。(Jung,1939b,段 62)
佛洛伊德明白引起症狀的意念源於自我未能覺察到的情感;若要解除症狀,這些意念有必要被重新導入意識經驗的範疇內。但榮格也認為:精神分析理論並不足以表達這些引發症狀的意念所具有的強大力量及正面潛能。根據榮格的看法,佛洛伊德視之為幻覺而想除去的是:
被往昔之「荒誕迷信」視為夜魅的那個東西。他想掀開惡魔所披的偽裝,讓它回變成無害的貴賓狗——簡言之,就是把它變成「心理學用語」。(Jung,1939b,段 71)
一九二○年,在提到他自己最喜歡的浮士德和黑色貴賓狗神話時(貴賓狗實為魔鬼的化身),榮格宣稱精神分析理論過於簡化問題,並認為自己的理論在強調心理情結(自我所不喜者)本具多重意義時,不僅有益於、也能修正精神分析的理論:
魂靈不一定都是危險和有害的。一旦我們轉以「意念」(idea)來稱呼它們,它們便也有可能帶來好的結果。五旬節聖靈降臨(Pentacost)的奇蹟就是把集體無意識中的一個內容轉換成可述語言的一個最佳例子。(Jung,1920,段 596)
針對佛洛伊德對海茲曼附身經歷的評論,榮格可能會有什麼別的說法?佛洛伊德認為魔鬼的乳房若非指亡父的養育之恩,就是言聽計從的兒子所採取之陰性姿態的投射。在佛洛伊德的描述中,海茲曼所採取的這種神經質策略迫使他淪入陽具闕如或被去勢之狀,使他具備了令他害怕的陰性特徵。佛洛伊德認為有兩項事實可以支持這個詮釋:第一,海茲曼之所以為驅魔之事長途跋涉,是因為他相信唯有瑪麗亞小教堂市的聖母能幫助他;第二,他是在聖母誕辰那天從魔鬼契約脫身得救的。榮格則可能會認為:魔鬼的曖昧性別暗示了這雙性的父親意象所扮演的是善變者的角色,而非閹割者的角色。九年的孕育期以及在危機期間退行到母親懷抱——這兩件事都代表了他有可能透過藝術創造去彌合神經質的自我分裂。但我猜榮格應會同意佛洛伊德如下的看法:海茲曼放棄繪畫生涯、委身聖職的決定透露了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足夠的勇氣或整合能力。這一看法並未認為接受聖職就等於逃避;它乃是根據海茲曼進修道院後沒多久就似乎染上酗酒習慣(如佛洛伊德曾指出的)所做出的推論。
雖然佛洛伊德曾寫文章討論集體心理的問題,但他在海茲曼的附身精神官能症個案上並未假設其中有集體因素的存在。相反的、而且特具意義的是,榮格在為附身下定義時卻納入了集體元素。對榮格來講,盧登邪靈附身事件是種流行疫情,堪與他稱為二十世紀「經人誘導而發生的集體精神錯亂」相比。因此,在詮釋琴.德尚哲這樣的附身個案時,我們不僅必須考慮創傷事件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個人無意識中突然爆發的被潛抑內容,還必須考慮集體無意識所造成的影響。換句話說,榮格可能會主張:琴.德尚哲的附身精神官能症之所以能感染其他吳甦樂會修女的心靈、極化盧登市民、並把群眾從全歐洲吸引過來,原因乃在她的附身經歷不僅道出了個人被潛抑的內在衝突,也道出了由集體無意識所導致的集體衝突現象。天主教徒和胡格諾教徒在市內及圈地內(用以圈範南特敕令所致之爭執)的相爭、奉行守貞規範的天主教修會與崇拜愛神厄洛斯(Eros)之俗世的對立、路易十三世在盧登城牆被毀後下令在城外二十公里處另建新城利士留、笛卡爾因恐懼宗教法庭而決定不發表他的新知識論——在心理動力說觀點的重新解讀下,這種種社會與政治現象都可被視為「表面」事件,是與集體無意識之內容物的迸發、也就是「集體精神錯亂」的發作同時發生的。
(本文為《附身:榮格的比較心靈解剖學》 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附身:榮格的比較心靈解剖學》Possession: Jung’s Comparative Anatomy of the Psyche, 2nd Edition
作者: 奎格‧史蒂芬森(Craig E. Stephenson)
出版:心靈工坊
日期:2017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