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夢之宮
文|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
譯|廖月娟
她在五個孩子中排行第四,在一月的某個寒夜,生於沙賈漢納巴德,即舊德里。由於斷電,產婆阿蘭.巴姬就著燈火接生,然後用兩條圍巾把剛呱呱落地的她包起來,放到她母親的臂彎,說:「是弟弟喔。」當時燈火昏暗,難怪她會看錯。
嘉涵娜拉.貝龔懷頭胎之初,她和她老公就說,如果是男的,就叫他阿夫塔博。這對夫婦已生下三女,苦等了六年,終於等到阿夫塔博。他出生那夜,是嘉涵娜拉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翌日清晨,太陽升起,房間溫暖、舒適。嘉涵娜拉解開小阿夫塔博的包巾,心滿意足、萬分憐愛地撫摸這個小寶貝。從眼睛、鼻子、頭顱、脖子,摸到胳肢窩、手指、腳趾……突然驚覺,寶寶的陰莖下方還有個小小的女陰,儘管發育不良,無疑是女性生殖器。
新生兒可能嚇到母親嗎?嘉涵娜拉.貝龔的確被嚇壞了。她的第一個反應是心臟揪緊,就要粉身碎骨。第二個反應是仔細再看一次,確定自己沒看錯。第三個反應是退縮,離孩子遠遠的。
她突然腹痛如絞,一道細細的屎水沿著大腿流下。第四個反應是想死,她要和那孩子同歸於盡。第五個反應是抱起那孩子,把他抱得緊緊的,從已知世界與未知世界間的裂縫跌下去,在那黑暗的深淵中墜落、旋轉。她本來知道的一切,從瑣事到大事,對她而言,再也沒有任何意義。她只會烏爾都語,在這種語言之中,不只是生物,所有的東西,包括地毯、衣裳、書本、筆、樂器,都有陰性和陽性之分。只有她的寶寶雌雄莫辨,不男不女。當然,她知道有個字眼指的就是那樣的人—海吉拉。其實,有兩個詞彙指稱這種人,就是海吉拉和金納 ,然而光是兩個字不能構成一種語言。而人是否能存活在語言之外?這個問題自然不是以文字呈現在她面前,甚至不是一個簡單的句子,而是來自胚胎的無聲怒吼。
她的第六個反應是把自己清洗乾淨,暫時保密,甚至不對她老公說。第七個反應是躺在阿夫塔博旁邊休息一下。就像基督教的神,在天地萬物造齊之後,歇工安息。只是那神創造的世界是有意義的,而嘉涵娜拉.貝龔創造的新生命,顛覆了她對世界的認知。
她告訴自己,那畢竟不是真正的陰道。雖然有縫隙,裡面卻沒有開口(她仔細檢查過了),只是個附屬器官、新生兒的特殊症狀,時間一久,縫隙說不定就癒合、消失了。她會去她所知的每一座寺廟,向神明祈求。她相信,神明必然會幫忙,一定會的。也許神明一直在護佑著她,只是她不一定知道。
嘉涵娜拉.貝龔終於有體力走出家門的第一天,就抱著阿夫塔博到沙希德神廟。那神廟離家不遠,約莫走個十分鐘就到了。那時,雖然她還不知夏爾瑪德.沙希德的事蹟,依然步履堅定地走向神廟。也許,沙希德在召喚她。她也可能是受到那群奇怪的人吸引,去米那市場的路上,她有時會看到一群外地人在神廟旁搭帳篷。她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以前,看到那種人,她總是視若無睹。現在,對她而言,那些信徒似乎突然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人。
不是每個去沙希德神廟的人都知道夏爾瑪德.沙希德的故事。有些人知道一點點,有些人一無所知,有些人則自己編造。很多人知道,他本來是信猶太教的亞美尼亞商人,為了追尋真愛,從波斯來到德里;很少人知道,他愛上的是阿貝.詹德,一個他在巴基斯坦東南信德省遇見的印度少年。很多人知道,他已放棄猶太教,改信伊斯蘭教;很少人知道,他最後也棄絕了正統伊斯蘭教。很多人知道,他赤身裸體在沙賈漢納巴德街頭苦行,直到被公開斬首;很少人知道,他被處決不是因公然裸體,而是被控背教。當時的皇帝奧朗則布是虔誠的穆斯林,他把沙希德找來,要沙希德證明自己是真正的穆斯林。奧朗則布要他背誦〈清真言〉:「la ilaha illallah, Mohammed-ur rasul Allah(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沙希德在皇宮裡的紅堡,一絲不掛地站在伊斯蘭法官和大學者面前,接受審判。藍天中白雲靜止,鳥兒也僵住了,紅堡空氣凝重。沙希德起了個頭,就沒再繼續。他只唸出這幾個字:「la ilaha(萬物非主)。」
他說,除非他能成道,否則無法全心全靈擁抱真主。在那之前,即使他背得出〈清真言〉,也只是口是心非。奧朗則布大怒,決定處死沙希德,眾伊斯蘭法官也都同意。
去神廟膜拜的信徒若不知沙希德的事蹟,不就只是盲目崇拜,不管事實與歷史?如果你這麼想,那就錯了。因為你一走進神廟,就能強烈感受到沙希德那永不妥協的靈魂。請求沙希德庇佑的信徒都覺得,這種感應要比史實來得真切。沙希德的從容赴義彰顯了靈性超越聖禮,簡樸勝過奢華,即便自身即將毀滅,也能滿溢頑強而狂喜的愛。沙希德之靈允許每一個人依自己所需,自由轉化他的故事。
等到嘉涵娜拉.貝龔常去沙希德神廟後,對沙希德的故事變得耳熟能詳。她知道沙希德是在賈瑪清真寺的台階被斬首示眾。信徒像潮水般包圍著他,與他道別。她也知道,沙希德人頭落地後,他的嘴巴才繼續唸誦:「萬物非主,唯有真主。」接著,他像現代摩托車騎士拿起安全帽般,把自己的頭顱從地上拾起,然後走上台階,進入賈瑪清真寺。接著,就升天了。嘉涵娜拉.貝龔不厭其煩地對願意聽她傾訴的人說,沙希德那小小的神廟有如嵌在賈瑪清真寺東側台階底下的帽貝,那裡就是沙希德的斬首之處。他的血噴灑出來,積血成池,所以神廟地板是紅的,牆壁和天花板也是紅的。她說,儘管三百多年過去了,沙希德的血依然洗刷不盡。不管這神廟塗上什麼顏色,最後還是變成紅的。
那紅通通的小神廟周圍很熱鬧,有賣精油和護身符的小販、幫朝聖者看管鞋子的人、瘸子、乞丐、遊民,還有即將在開齋節被宰的肥羊。一群年老的閹人靜靜坐在帆布棚底下,以此為家。
嘉涵娜拉.貝龔得穿過這些人,才能進去神廟。她第一次去,入內之後,就覺得平靜安詳。這裡幾乎聽不到市井喧鬧,彷彿隔著很遠的距離。她抱著沉睡的寶寶,坐在角落,看著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三三兩兩前來,把紅線、紅手環、紅紙條綁在陵墓四周的柵欄上,請求沙希德護佑他們。後來,她才發現有個老人坐在另一個角落。老人像隱形人似的,皮膚乾燥如紙,纖細的鬍鬚像光線紡成。他前後搖晃,靜靜地哭泣,似乎肝腸寸斷。這時,嘉涵娜拉.貝龔才讓自己的淚珠滾下。
她向沙希德耳語:他是我兒子阿夫塔博。我帶他來到祢面前,請保佑這孩子,請教我如何愛他。
沙希德應允了她的祈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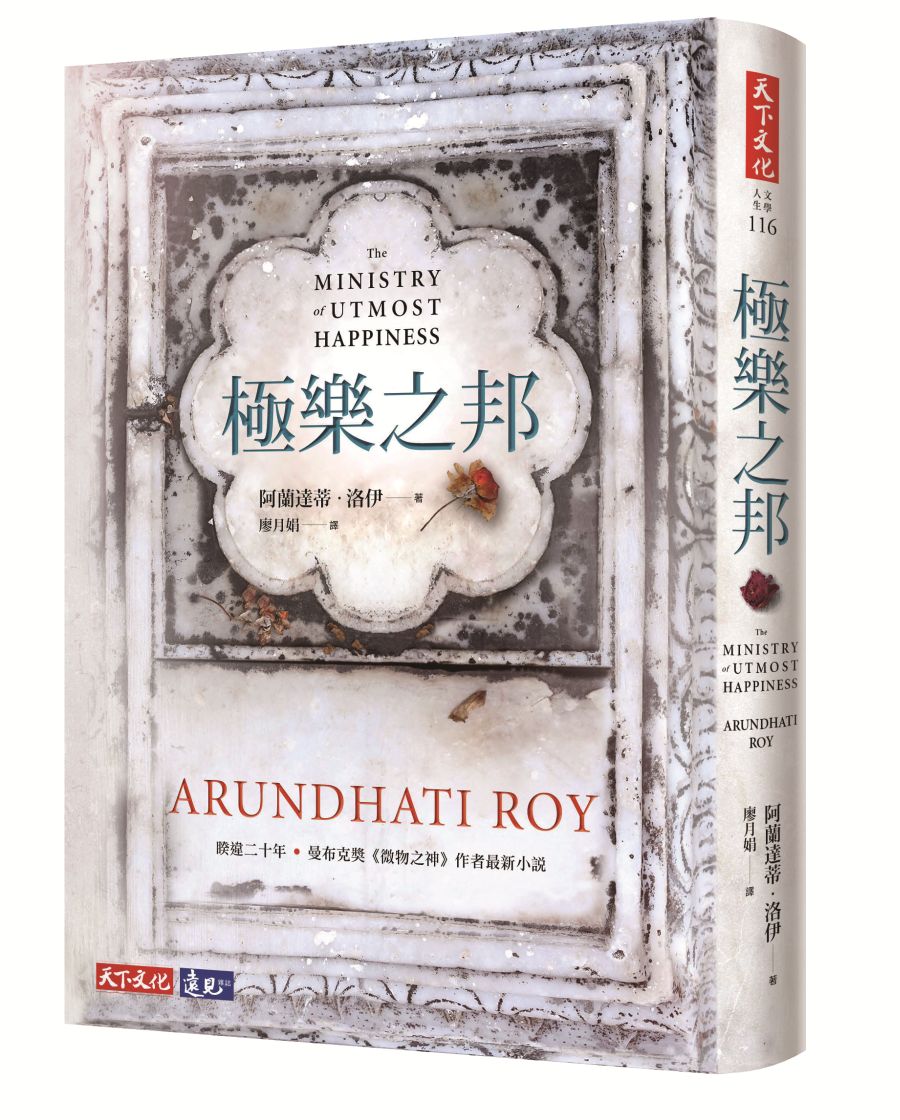
在阿夫塔博幼小之時,嘉涵娜拉.貝龔一直保守著祕密。她一邊耐心等待阿夫塔博女陰的部分消失,一邊極力保護他。就算她已生下么子薩奇柏,仍不讓阿夫塔博遠離她的視線。在旁人眼裡,阿夫塔博是她苦等多年才懷上的寶貝兒子,難怪她如此寵溺。
阿夫塔博五歲那年,到手環巷一所以烏爾都語和印地語教學、只收男生的學校就讀。不到一年,他就能用阿拉伯語背誦一大段《古蘭經》。儘管這孩子對經文有多少了解仍是個疑問,不過其他孩子也很會背。阿夫塔博天資聰穎,對音樂尤其有天分。他的歌聲甜美、動人,任何曲調只要聽過一次,就能學起來。於是他的父母決定把他送到月之宮,跟哈米德汗學習印度斯坦音樂 。哈米德汗年紀輕輕,已是尤希達,即所謂大師、巨匠。小阿夫塔博從未向老師請過假。到他九歲時,已能唱長達二十分鐘的巴達卡雅抒情曲,還會雅曼拉格、杜爾迦和巴拉威三種變調。
他在唱普力亞達那希力拉格時,輕輕掠過降Re的音,就像打水漂時,石頭在湖水表面彈跳的樣子。他唱恰提和土木里這種半古典、半流行的歌曲時,就和勒克瑙歌妓唱得一樣婉轉動人。起先,大夥兒覺得有趣,甚至叫好,不久其他孩子就開始笑他:他是女的啦。他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啦。他是男的,也是女的啦。她是他,他是她,嘻!嘻!嘻!
嘲笑讓阿夫塔博忍無可忍,他不想去上音樂課了。但他是尤希達哈米德汗最鍾愛的弟子,哈米德汗願意給他個別授課,阿夫塔博因而繼續跟著哈米德汗學習,但他再也不肯上學。此時嘉涵娜拉.貝龔的希望幾乎已經幻滅,阿夫塔博的療癒看來遙遙無期。幾年前,他就該接受割禮了,但嘉涵娜拉.貝龔用種種藉口拖延。轉眼間,已輪到弟弟薩奇柏。她知道她不能再拖了,於是,她鼓起勇氣,對老公吐實。她一方面哭得肝腸寸斷,另一方面,因為得以說出這個天大的祕密,終於鬆了一口氣。
(本文為《極樂之邦》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極樂之邦》 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
作者: 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
出版:天下文化
日期:2017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