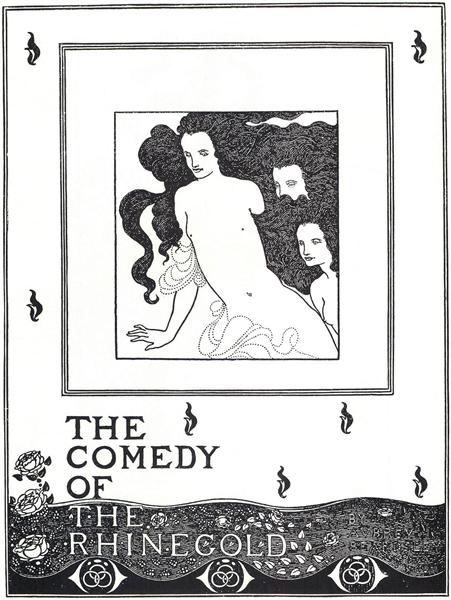
文|葛洛斯(Arthur Groos,康乃爾大學人文學科艾凡隆基金教授)
譯|鄭可喬
1851年,華格納在瑞士政治流亡時提出了一個「謙和的建議」,他想要在萊茵河畔創辦歌劇慶典,演出他自己的樂劇;當時任何一個德國文化場景的觀察者,可能都對此不太感興趣。事實上,我們的觀察者可能會認為,就音樂來說,萊茵河早已氾濫四溢。畢竟,這條河是從瑞士到荷蘭等德語地區至關重要的連結,已經被慶頌了數百年,而浪漫主義對日耳曼神話的興趣早已使這個地帶成為主要的旅遊景點,部份歸因於 1830 年代起,諸多《尼貝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 )的話劇與歌劇改編促使了這樣的情形。此外,兩個影響深遠的政治事件,也讓萊茵河成為德國音樂身份認同的群眾焦點。
首先,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終止了法國的佔領,分配了萊茵地西法利亞給普魯士,隨後,下萊茵出現了以日耳曼音樂為主的各個音樂節,很快地,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和舒曼(Robert Schumann)都躋身這個音樂活動中心的指揮,兩人都曾短暫懷有撰寫尼貝龍根歌劇的想法。
其次,就是1840 年所謂的萊茵危機,因法國宣稱萊茵河為其與德國之間的「天然」疆界而爆發,引起了萊茵詩歌和音樂的一股熱潮──在 1840 到 1850 年間,泛流的民族主義狂熱催生了將近 400 首歌曲。
這場眾人樂思泉湧的結果多數已被遺忘,除了舒曼的兩套聯篇歌曲集《艾辛朵夫歌曲集》(Liederkreis, op. 39, 1840)和《詩人之戀》(Dichterliebe , op. 48, 1840),以及他的《降 E 大調第三號交響曲「萊茵」》。萊茵歌劇匿跡於這一陣喧囂之中,華格納可能其實一直在為萊茵歌劇努力創造一個天地,今日稱其為「利基市場」(market niche)。他一定很清楚萊茵藝術歌曲的巨大吸引力, 也熟知李斯特(Franz Liszt)和舒曼的設計,特別是舒曼的〈萊茵河上〉(Auf dem Rhein , 1842),該作品開頭就是對沉在河底的尼貝龍根寶藏。

當然,要從舒曼的鋼琴萊茵到管絃樂的萊茵,需要莫大的想像力飛躍,管絃樂的萊茵預示整個音樂天地的開端,更不用說要在舞台上具體呈現出來了。這是《萊茵的黃金》的核心要素,值得我們細細檢視。讓我們從華格納開場的場景指示開始,寫著需要「碧綠的朦朧光影,愈向上愈亮,愈向下愈暗」:
舞台高處滿佈著波動的水,由右邊向左邊不停地流動著。波浪向著低處去,消逝在愈來愈細密的潮濕霧氣中。地面上大約人身高的空間,看來像是沒有水。如同雲朵般地,水漫開到夜晚的深淵裡。舞台的後方,到處都豎立著陡峭的岩壁,隔開了舞台的空間; 整個地面都高低不平,沒有一塊是平的,每個角落看起來都像是在深谷般的幽暗裡。
這個水世界隨後立刻出現了三位萊茵的女兒,她們游著、泅泳著,圍繞著河流深處中間的一塊暗礁嬉鬧。
這裡的場景指示強調了該景出現前的混沌:空間上,係藉由色調由亮轉暗的變化,以及從無限深淵聳立起來的岩石峭壁和暗礁做出的「狂野混亂」;時間則水平地藉由頂端和底部流水的暗示完成。當代藝術家與舞台設計師都不難想像這個場景,從霍夫曼(Josef Hoffmann)為1876 年拜魯特首演設計的草圖就看得出來, 但那個時代的舞台硬體限制卻是真正的挑戰:萊茵的女兒必須要游上游下,圍著萊茵的黃金繞圈。為了要營造游泳的景象, 她們站在半透明佈景後的輪車上,被推來推去。儘管如此,這條河還是一動也不動,在早期的靜態攝影媒材下,看起來比較像一池死水而不是一條河。後來的柯西瑪(Cosima Wagner)製作, 則是用類似大型釣竿的軟棒將萊茵的女兒懸吊於吊籃,隨著科技進步,這種吊具被高強度鋼絲以及最近的高空彈跳繩索取代。
燈光技術的發展也可以投射流水效果在布幕上,營造出我們晃來晃去的少女在水平河流中游泳的景象。
在二十世紀,舞台設計傾向現代主義,尤其是十九世紀末的阿道夫‧ 阿皮亞(Adolphe Appia)和二十世紀中葉魏蘭德‧ 華格納(Wieland Wagner),他們反而抽象運用舞台空間,經常使那些寫實技術顯得不必要。想當然爾,接下來的後現代主義方法往往以導演的視角代替華格納的視角,薛侯(Patrice Chéreau)百年拜魯特的水力發電大壩設景就是一個例子。美國近期的兩個製作可以說明我們介於革新與保守之間的製作選擇。大都會歌劇院羅伯‧ 勒帕吉(Robert Lepage)近期的製作呈現出抽象的藍色背景, 萊茵的女兒附貼在「機器」上,機器的變換貫穿整套製作,另一方面,湯瑪斯‧ 林區(Thomas Lynch)在西雅圖的佈景則傾向原來拜魯特的製作,自然喚起了西北太平洋的氛圍。

這兩個製作都突顯了開場一景的關鍵元素,這亦是本文主要聚焦所在:亦即是,從序奏音樂浮現出來的原始水中宇宙。華格納把這個轉變跟其更為宏大的來龍去脈一起簡潔地寫在1853 年二月十一日給李斯特的信中,隨附一份他自己出錢印的《指環》劇本:「好好看我新的詩作──裡面包含了世界的開始和結束!」這也就是說:他原本對齊格菲之死的興趣已擴大到我們今天稱之為宇宙源起,一段宇宙的起源和命運的記述。當然,最古老的文化和宗教中,皆存在這種宇宙源起或創世神話,華格納身為才華洋溢的古典主義者、名義上的基督徒,以及中世紀日耳曼文獻學的狂熱讀者,他十分熟悉的相關記述至少有三部:赫西俄德(Hesiod) 的《眾神譜》(Theogony)、聖經《創世記》,還有史圖松(Snorri Sturluson)的《艾妲》(Edda)。然而,在重新想像日耳曼神話時, 因身為現代人產生的自我意識,華格納的《指環》跟這些創世故事有兩點重要的差別。
第一點是,出現在《萊茵的黃金》裡的物質宇宙明確建構於四大元素(空氣、土、火、水)之上,這些也是從經典的古代遺跡中到現代時期所有東西的基礎砌塊。在第二景中,洛格(Loge) 給了我們創世的概觀,他報告著,在提出天地萬物有什麼比愛情更吸引人的問題之後,他的問題就被嘲笑了:「在水底、土裡和空氣中,沒有人會放棄愛情和女人。」這裡少了的第四個元素,當然就是洛格自己,這個名字乃在《指環》創作後期,才被華格納從原本的洛吉(Loki)改為洛格,這名字在北歐古語裡就是「火焰」的意思。
這些元素帶出了分配在《萊茵的黃金》中各主要段落裡不同的空間和音樂氛圍, 這些原始宇宙的元件,經常在互不相連的調性區域中,被以基本主和絃和其分解和絃呈現。大部份讀者都知道,歌劇的水世界從第一個低音降 E 音以及這個音的大三和絃浮現出來。同樣地,諸神的空氣世界在第一、二景之間的過渡段落, 從湍急河流中浮現:
漸漸地,波浪變成了雲,當一股越來越明亮的光線於其後出現時, 雲化為了細霧。當霧氣以細小雲朵的型態在舞台頂部完全消失之時,在黎明曙光中,可見到山頂的一片空地。
這個宏偉的空氣高昇在音樂上的呈現,係從急促進行的 c 小調三連音群轉變到降D大調,以厚實的管絃樂歡呼展示日出時的瓦哈拉神殿。到第三景的過渡段也包含了到另一個元素的變化, 從瓦哈拉神殿的空氣高度到了土裡,那地底深處充滿硫磺味的尼貝海姆。洛格所代表的第四個元素,火,更為複雜,有如他外型變幻莫測和道德上模稜兩可的特性,藉由快速半音的竄動,似乎不斷跳動閃爍著。
華格納《指環》與現代前的宗教宇宙源起相異處的第二點,乃是自我意識強烈的音樂性:的確,開場一景的水中世界似乎從降 E 大調前奏直接出現,沒有神聖造物主的介入。華格納機靈地操縱他的自傳,表明自己的樂思起源獨特,是自己極富創造力的潛意識成果,後來學術界也傾向於接受他這個主張:那就是前奏源於 1853 年九月五日下午,他在義大利拉斯佩齊亞鎮(La Spezia)做的流水之夢。然而,如果我們跳過有關這說法真實性的種種爭辯,並轉向更大德國古典音樂的世界,一個重要先驅就會赫然可見:海頓(Joseph Haydn)的《創世記》(The Creation , 1796-1798)。華格納當然熟知這部作品,他在1845 年指揮過。接下來的內容還在推測階段,但我希望可以透過與海頓《創世記》的簡要比較,或許可闡明《萊茵的黃金》之宇宙源起。
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這兩部作品的開端用了同樣的調性區塊或調性。眾所周知,海頓《創世記》管絃樂導奏建築在 c 小調上, 以徘徊、半音旋律線、在力度極端之間的變換,以及猶豫不決的節奏,來呈現混沌。在拉斐爾回顧《創世記》描述混沌的前幾節之後,有一整個小節的停頓,接著,合唱團開始輕聲唱出降 E 大調分解和絃,代表神的靈漸漸匯聚,盤旋於水面上,隨後出現「要有光」的命令,引發著名的極強音,4/4 拍 C 大調和絃的「大爆炸」。
當然,《萊茵的黃金》的宇宙因為缺少神聖造物者,跟海頓的世界在本質上還是有很大的區別,但海頓降E 大調分解和絃的精神,似乎也盤旋在華格納的水域之上。這個世界自己產生於一個不確定的過去,以一個幾乎難以察覺的低音降 E 音出發,在之後的 136 小節裡持續進行,經過其他樂器的加入,有著音色與和聲,形成一個降 E 和絃,再以分解和絃的型態,形成一系列節奏和旋律的變化。這一連串「流動」通常被稱為自然動機,當到達這個流動的高潮時,幕啟,萊茵的女兒出現。不久我們就會發現, 她們的原始純樸之境最終圍繞著 C 大調,也就是用來代表日光突然照亮純淨未受玷汙之萊茵黃金的那個調。

比同一調性更有趣的事情也許是,《創世記》與《萊茵的黃金》兩部作品都創造了一個自我意識強烈的音樂世界。海頓的神劇第三部份開始,天地初建成的第一個早晨,不是聖經的安息日, 而是音樂,從天上傳下來的純淨和聲,啟發了亞當和夏娃唱出了總結前六天的創世讚美。華格納的歌劇手法同樣開始於從降 E 大調前奏水世界出來的首批造物,她們的名字根據「水」的德語語意字根而選擇:渥格琳德(Wog-linde)和魏兒昆德(Well-gunde) 分別來自代表波浪的字,Woge 與Welle,而弗洛絲希德(Floß-hilde)則是從Fluß(河流)一字變化而來。她們也歌頌她們的造物者, 不過肯定不是海頓《創世記》的猶太和基督的神,而是日耳曼之「父」萊茵。渥格琳德開場的話,也是《指環》中首次出現的言語, 仍然挑戰許多聽眾:
Weia! Waga!
Woge, du Welle,
Walle zur Wiege!
Wagalaweia!
Wallala weiala weia!
喂!河水!
捲起波濤!
將浪湧至源頭!
嘩啦啦!
嘩啦嘩啦!
例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他描述大幕上升後的文字,就不太像是位完美的華格納信徒:
你看到了剛才你【在前奏曲裡】聽見的一切 — 深廣的萊茵河, 河中有三個奇形怪狀的仙子人魚。他們是半人半魚的水仙子,正一邊唱歌一邊嬉戲,陶醉地沉浸在歡笑之中。她們不唱民謠之類的曲子,或歌頌羅蕾萊 (Lorely) 和她命運多舛的戀人,只是隨便哼哼唱唱⋯⋯想到什麼就唱什麼⋯⋯
不過事實上呢,如之前所提,華格納其實是一位中世紀日耳曼文獻的狂熱讀者,他極富巧思,以格林(Jacob Grimm)的《德意志神話》(Deutsche Mythologie) 中針對水元素的討論來創作, 利用中古德語中的早期語言學證據,賦予了開場段落原始或古老的氛圍。他後來在給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的一封公開信(1872 年)中,透露了評論家帶給他的挫敗感:
在研讀雅各‧格林後,我用了一個古德語詞 Heilawac,為了我的目的,自己將它修改成Weiawage (這個詞型,我們今天在Weihwasser(聖水)這個字裡,仍然可以看到),再由此出發,走到相關的字根 wogen 和 wiegen,最後到 wellen 和 wallen,依著我們童謠 Eie popeia 的類似情形,為我的水女做出一個字根音節式的旋律。
也就是說:從萊茵的原始水域之中出現的最初言語意圖,源自跟流水有關的最古老的日耳曼文字:Wage, Woge 與 Welle,以及意指搖籃的 Wiege。於是這成了在新生天地中,一首新生語言的搖籃曲。如同華格納後來對柯西瑪所說的「世界的搖籃曲」,浮生自萊茵河的晃晃盪盪,凝聚成水之文字,從而形成第一個言語行為,頌讚賦予其生命的元素。如果我們仔細聽沃格琳德的開場敘述,我們也會注意到,這個原初的日耳曼語係以五聲音階的旋律唱出,在這裡被想像為西方調性的原始前身。
(本文為《華格納研究:神話、詩文、樂譜、舞台》部分書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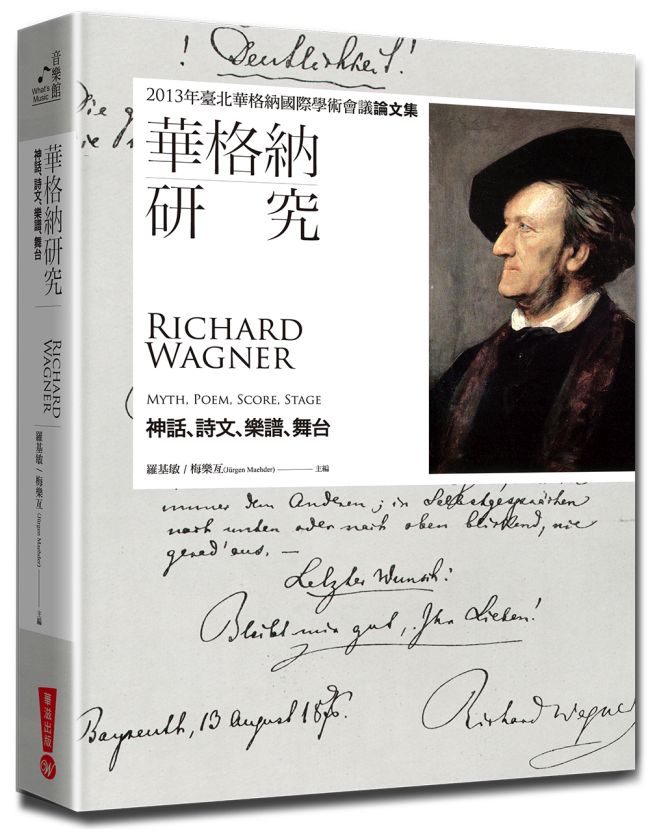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華格納研究:神話、詩文、樂譜、舞台-2013年臺北華格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編者: 羅基敏、梅樂亙(Jürgen Maehder)
出版:華滋
日期:2017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