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埃洛‧莫里斯(Errol Morris)
譯|吳莉君

在念頭
與現實之間
在動機
與行動之間
陰影落下⋯⋯⋯
──艾略特(T. S. Eliot),〈空心人〉
「你是說,你千里迢迢跑去克里米亞,只是因為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寫的一句話?」我朋友隆.羅森鮑姆(Ron Rosenbaum)用不太相信的口吻說道。
我告訴他:「錯,事實上是兩句話。」
那出自於桑塔格的《旁觀他人之痛苦》,她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
這就是那兩句話:
事實證明,許多早期戰爭攝影的經典影像都經過擺設,或是照片中的景物曾遭到竄改更動,這點並不令人驚訝。當芬頓(Fenton)帶著他的暗房馬車抵達塞凡堡(Sabastopol)附近滿目瘡痍的山谷時,他從同一個三腳架的位置拍了兩張照片:在那張膾炙人口、名為「死蔭幽谷」(〔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儘管冠上這個標題,但那支輕騎兵在發動那場死亡出擊時,並未越過此地)的第一版照片裡,有許多砲彈堆在道路左邊的地面上,但是在他拍攝第二幀─也就是經常轉印複製的那幅─照片之前,他監督別人把砲彈散置在道路上。
先做一點背景介紹。1855年,英國出版商阿格紐父子公司(Thomas Agnew & Sons)派英國知名攝影師羅傑.芬頓(Roger Fenton)前往克里米亞拍攝正在進行的戰爭,交戰雙方一邊是英國、法國和土耳其組成的聯軍,另一邊是俄羅斯。芬頓和他的助手約翰.史巴林(John Sparling)從1855年3月8日到6月26日,花了將近4個月的時間,在英軍戰線後方一輛改裝成暗房的馬車裡工作。他們生產出360張照片,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以「死蔭幽谷」為名的那兩張。
雖然這兩張照片具有經典地位,但是桑塔格的書裡並未附上插圖。事實上,桑塔格的書裡沒有附上任何照片,只有照片的相關資料。我幫讀者省點事。這就是芬頓拍的那兩張照片,根據桑塔格的說法,是「從同一個三腳架的位置」拍攝。我幫它們各取了名字:「路旁」(OFF)和「路上」(ON)。「路旁」是指砲彈出現在路旁邊那張,「路上」則是砲彈出現在路中間那張。

我花了不少時間細看這兩張照片,還有思考桑塔格的那兩句話。桑塔格指的當然不是芬頓在照片拍攝之後做了變造,只是說他在被拍攝的風景裡做了一些更動,藉此改變或「擺設」(staged)了第二張照片。但是桑塔格怎麼知道芬頓在風景裡動了手腳,或者說得更明白點,她從何得知他「監督別人把砲彈散置在道路上」?
不管有什麼證據,肯定都不是從這兩張照片裡面找到的。因為在這兩張照片裡,我們都沒有看到芬頓(或其他任何人)彎下身子像是要撿起砲彈或放下砲彈。
那麼,桑塔格怎麼知道芬頓做了什麼,或是為什麼要那樣做?桑塔格的那句話還加碼暗示讀者,芬頓有點懶惰,好像他沒花力氣親自去撿放那些砲彈,而是指揮或監督別人把砲彈擺到他想要的位置。你可以想像那個專橫的芬頓喊著:「喂,你到那邊。把砲彈撿起來,擺到馬路上。不對,不是那裡。往左邊挪一邊。」又或者,他不是懶惰。也許他只是背痛。那個心有餘但力不足的芬頓哀求說:「孩子,我的背快痛死了。你介不介意幫我撿幾顆砲彈擺到馬路上呢?」
就在我跟這些問題死命搏鬥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桑塔格怎麼知道這兩張照片的拍攝順序呢?她怎麼知道是「路旁」先拍還是「路上」先拍。想必是有什麼附加資料讓她可以替這兩張照片排出順序:之前和之後。倘若她是基於這個原因宣稱第二張照片被擺設過,那麼她是不是該把證據提出來呢?
桑塔格的書裡沒有註釋,所幸書的末尾有這樣一段致謝文:
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的馬克.哈沃斯–布斯(Mark Haworth-Booth),點出芬頓的〈死蔭幽谷〉照片有兩個版本,這兩張照片都刊登於烏里區.凱勒(Ulrich Keller)編的《終極奇觀:克里米亞戰爭的視覺史》。
我買了一本凱勒的書,立刻翻到第4章關於那兩張照片的段落。我找到下面這段內容,凱勒在裡頭提出幾項歷史發現─包括有兩張照片、兩者之間有些微差別,以及第二張照片裡的砲彈若不是芬頓自己擺的,就是在他的指揮下擺放的。
原文如下:
芬頓在同一地點拍攝的兩張照片之間,有一項微小但重要的差別,似乎逃過了攝影史家的法眼。第一張照片再現的內容,顯然是攝影師發現那條道路時的壕溝原狀,砲彈排在道路旁邊。在第二個版本裡,我們發現一項新焦點。有些圓球形的砲彈展示性地散布在整條路面上─彷彿那些圓球剛剛才投擲到那裡,讓攝影師暴露在槍火彈雨之中。記錄在第一張照片裡的平和場景沒什麼內容可述說,芬頓顯然把證據做了重新安排,好營造出原始場景所欠缺的戲劇感和危險性。
接著,在這段文字的註釋裡,凱勒進一步把他的看法延伸到芬頓的個性上:
芬頓有個傾向,會誇大他所拍攝的戰役的危險性,這點也可從1855年9月20日的《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裡看到,他在裡頭列出一連串僥倖逃過的危險情況,例如他的暗房馬車⋯⋯經常成為俄羅斯人的懷疑目標;他本人遭子彈劃傷;他的助理被米尼步槍射中手部。
但是,這些形容哪裡有誇大呢?《每日新聞》裡的這篇文章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支持凱勒的說法。若說這篇文章真有什麼,那就是它跟凱勒正在討論的內容相牴觸。難道凱勒的意思是,芬頓對《每日新聞》的記者造假(當然也有可能是那位記者誇大了芬頓的說法,而非芬頓本人誇大其詞)?難道凱勒知道那輛暗房馬車並非「俄羅斯人的懷疑目標」?或者芬頓的助理史巴林並沒有「被米尼步槍射中手部」?凱勒認為這些說法是假的,證據在哪裡?芬頓自己曾經寫道:
這張照片是拜當天駕駛(史巴林)的細心之賜,他建議或許可以在山谷裡讓車子和駕駛停下來,休息一下,我們倆都覺得在出發前拍照留影是個不錯的想法。

據說史巴林擔心這會是一趟有去無回的前線之旅,當然,這也可能是另一次的誇大或偽述。
凱勒說,第一張照片顯然「再現⋯⋯攝影師發現那條道路時的⋯⋯原狀」(「路旁」),而且芬頓顯然把第二張照片裡的砲彈「證據做了重新安排」(「路上」)。
我在其他地方說過,沒有任何事情會顯然到顯然如此。當某人說某件事情顯然如此時,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那絕對不是什麼顯然的事,即使對說話者而言都不顯然。使用「顯然」一詞,意謂著缺乏合乎邏輯的論證──只是想用說得大聲一點來斷定某事為真,並藉此說服讀者。
讀了凱勒的書後,我隨即打電話給他討論他對芬頓的說法,也就是桑塔格後來複述過的那些:
莫里斯……我讀桑塔格的時候,留意到你討論芬頓的那本書(《終極奇觀》)。她提到你對「死蔭幽谷」那兩張照片的分析,並暗示芬頓擺拍了其中一張照片。
凱勒……是的。
莫 她的大多數資料似乎都是從你那裡來的?
凱 是的,我想可以這麼說沒錯。
莫 我感興趣的是有張照片是擺拍的這個想法。也就是說,有張照片是造假的。
凱 那是某種潤飾或干預,目的是為了把原始照片所缺乏的戲劇性添加進去。說它造假有點過頭,但它是某種欺騙。這是當然的。
莫 欺騙什麼呢?
凱 嗯,欺騙指的是,它營造出一種印象,讓人以為那張照片是在極度危險的情況下拍攝,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莫 兩張照片都是嗎?
凱 第二張。路面上有砲彈那張,肯定是比較後拍的,顯然如此。
莫 為什麼?
凱 嗯,因為有兩張照片,一張裡面的砲彈出現在路邊的壕溝裡(「路旁」),另一張的砲彈在路面上(「路上」)。我們大可、大可因此認定是芬頓把這些砲彈從壕溝裡搬出來擺到馬路上,而不是反過來。他有什麼動機要把已經在馬路上的砲彈移開呢?他為何要這樣做?所以,我認為這答案非常明顯。不過你似乎對這點有所懷疑?
莫 是的。我很好奇你是怎麼做出結論,認為砲彈在路上(「路上」)的照片是第二張。你認為芬頓並未置身險境,但想要衝高場面的戲劇效果,所以把現場布置成好像他正遭受攻擊的模樣。芬頓想要向潛在觀眾傳達他很英勇的假印象。但是,你為什麼會相信這種推論呢?我的措辭可能不甚妥當。如果有冒犯之處,我道歉。
凱 嗯,我可以看出他有動機把那些砲彈從壕溝裡取出擺到路面上。對我來說那很合理。我認為這是有些人可能會做的事。至於反過來那種,我想不出有誰有理由要那樣做。我不認為可能是那樣。
莫 是因為不存在合理的解釋,所以讓「反過來」那種不可能或不可信嗎?
凱 是的。
(本文為《所信即所見:觀看之道,論攝影的神祕現象》部分書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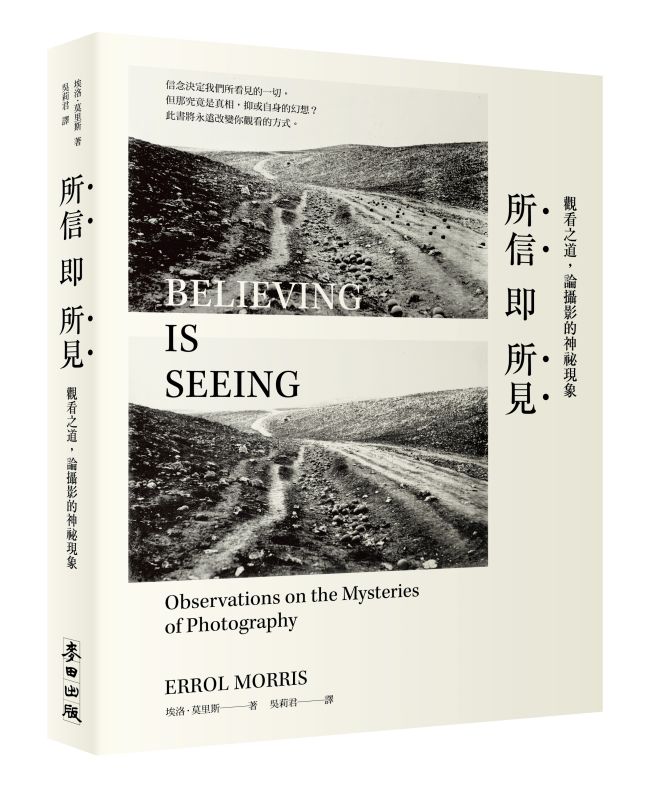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所信即所見:觀看之道,論攝影的神祕現象》 Believing Is Seeing: Observations on the Mysteries of Photography
作者: 埃洛‧莫里斯(Errol Morris)
出版:麥田
日期:2016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