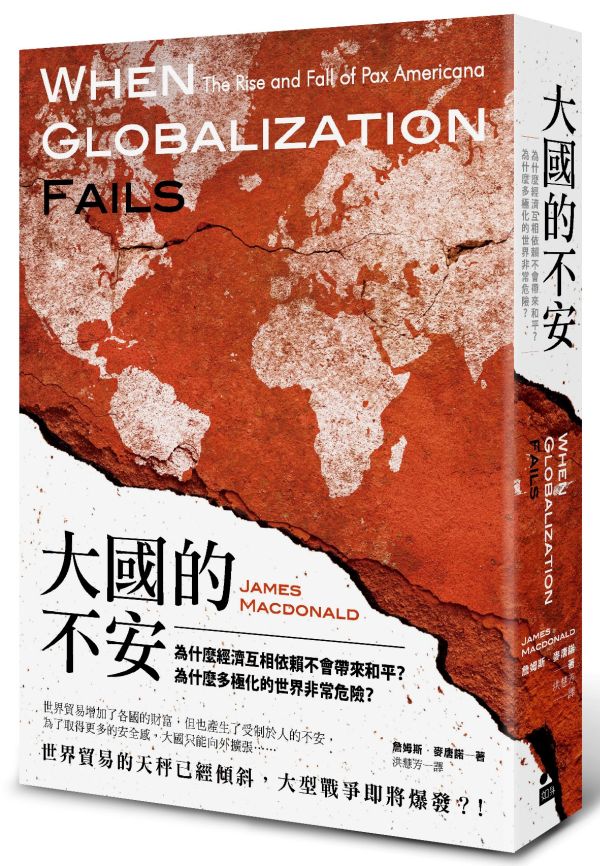
文|詹姆斯‧麥唐諾(James Macdonald)
譯|洪慧芳
中國的崛起引發了一些問題。中國不是專注於自給自足或原料出口,而是轉型成依賴原料進口及製成品出口的工業強國。這樣一來,它的地位就類似英國、德國和日本了(當初這三國就是為了取得原料和市場而導致兩次世界大戰)。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衝突,是在工業化的西方國家接受美國的領導及軍事優勢下化解的。但中國願意接受美國的指導和保護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明顯,因為中國不像亞洲四小龍,不是在美國的保護傘下成長的。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就堅守敵對的意識形態,在韓戰中又直接對抗美國,在越戰中間接反美,在世界各地都和美國不對盤。一九八○年代末期,蘇聯集團崩解時,東歐國家變成西方聯盟的堅定成員,但這些國家本來就是在槍口的威脅下施行共產主義的,他們從來不覺得共產主義是民族認同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後來不僅迅速採用西式的資本主義,也採行西式的民主。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即使中國已經放棄共產主義的經濟原則,它比俄羅斯還要堅守共產主義的過往。中國並未走向民主,而是堅持共產黨的統治。毛澤東在北京的雕像依然聳立,不像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列寧和史達林雕像已被推翻。如果連名義上民主的俄羅斯聯邦都難以決定是否加入或反對西方了,那麼依舊堅守共產主義的中國可能就更難決定了。
不過,這個問題更亟需找出答案,因為中國的規模實在太大了。韓國、台灣之類的亞洲四小龍,甚至日本,人口都只有美國的一小部分。他們除了渴求美國的保護以防共產主義的威脅以外,對原料的需求不太可能促使他們和其他的工業化國家過度競爭。但中國並非如此,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人口,境內雖然蘊藏許多天然資源,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其發展開始對一些重要物資的供給產生很大的壓力。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的石油就不再自給自足,現在是全球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二○○五年左右,中國對石油日益成長的需求開始推升國際油價。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生產國、第三大的銅礦生產國,但由於中國成長得太快,二○○○年以後,鐵礦和銅礦的進口量迅速成長,二○○四~二○○五年開始影響國際價格。二○○○年以前,糧食生產還跟得上消費,但現在中國是很大的糧食淨進口國,實際上已放棄自給自足的目標。
在公開場合,中國官員向來毫不猶豫地重申黨的路線,說中國新獲得的經濟實力不會以任何方式威脅世界和平。多年來,他們傳播中國「和平崛起」的理念。二○○五年,經濟學家已開始預測中國經濟何時將和美國旗鼓相當,在「崛起」前面加上「和平」兩字開始顯得欲蓋彌彰,於是他們把措辭改為「和平發展」。當年,中國國務院公布《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清楚說明了原則:「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致力於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中國過去不稱霸,現在不稱霸,將來強大了也不稱霸。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為了證實這番說法,中國確實可以指出,目前為止中國非凡的經濟成就並未威脅或中斷世界秩序。
然而,事實不像那些冠冕堂皇的說法那麼簡單。中國對外關係的指導原則,從一九七八年以來就是鄧小平的真言「韜光隱晦」。這個原則不禁令人懷疑,官方聲明是否只是中國變得夠強大、足以堅持主張之前的權宜之計。中國一向明確表示,它自己不稱霸,其他國家也不該稱霸。一九七○年代,中國提出另一種世界三方論。在中國看來,「三個世界」不是由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第三世界組成的,而是由兩大霸權、他們的盟友、第三世界組成的。中國藉由這個理論的提出,巧妙地把蘇聯從第二世界提升到第一世界,同時把自己從第二世界降至第三世界。這樣做有兩個目的,這樣一來就廢除了中國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爭中應該「一邊倒」的概念(暗指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有正當的理由)。這也讓中國得以用「無特權國家」的身分攻擊這兩個強國。但這招後來證實無效,中國從未停止譴責霸權的概念,所以中國把自己描述成沒有威脅的國家,卻又不斷地質疑現狀。例如,二○○二年,即將獲任為國家主席的胡錦濤為中國的崛起找了一個新理由,他說:「隨著中國的發展,我們會有更多的資源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由於一九九一年起只有一個國家算是霸權,胡錦濤這說法所指涉的對象再清楚不過了。
理論上,中國主張和諧合作而非霸權,應該會讓它成為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構的堅定成員,但它卻經常拒絕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一些中國官員譴責「責任」這個概念是西方用來箝制中國的陷阱。二○一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期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大國責任論』的概念是有缺陷的,因為那只對全球霸權有利,犧牲了其他國家的主權,以一小群優勢國家發明的所謂『普世』價值,來要求其他國家負責。」
中國黨政官員聲明的背後,存在著否認當前全球秩序的各種原因。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原因中,一端抱持複雜的意圖,例如二○○五年趙汀陽出版的《天下體系》,該書宣傳另一種「中國的」全球道義,以永恆的中國價值觀「和平與秩序」對比西方「混亂和暴力」的歷史。另一端則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的呼聲愈來愈大,亟欲為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到一九四九年共黨勝利之間中國經歷的「百年國恥」復仇。這類意見日益崛起,呼籲大家為中國受到的任何攻擊進行報復。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受到政府的鼓勵,中國政府在發生天安門事件後,就培養了一個更偏重民族主義的教育體系,結果一如葛小偉(Peter Gries)在《中國新民族主義》(China’s New Nationalism)中提到的:「諷刺的是,『第四代』似乎覺得西方帝國主義讓中國受苦受難這種新的受害說法很有意思,因為他們和老一輩的中國人不同,他們從未直接受害。」中國觀察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描述幾種不同的中國意見派別,從「本土主義者」(守舊的毛澤東主義者和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到「現實主義者」(軍中特別多,他們主張美國基本上是敵對國家,中國應該捍衛自己),再到「全球主義者」(他們認為應該融入現有的秩序)。他指出:「這種多元派別的重心不在中央,也不在全球主義者那一端,而是偏向左邊,停在現實主義者上,但本土主義展現了強大的拉力。」
換句話說,中國對當前全球秩序的立場,遠比官方聲明的意涵還要搖擺不定。由於那個全球秩序其實就是美國治世,中國其中一個立場是完全否決。連中國是否支持聯合國領導的秩序都不確定,因為中國深信,外界慫恿它在現有的國際機構內擔任負責的「團隊成員」,只是要逼它就範的伎倆罷了。軍事開支方面更可以明顯看出中國的言行不一。中國一開始是以「和平效益」(peace dividend)來推動經濟改革。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在軍事方面的支出通常占GDP的七%左右,一九六○年代末期因中蘇關係緊張而升至十%。一九七○年代與美國的和解,意味著中國可以稍微降低這個沉重的經濟負擔,但鄧小平上台時,軍費開支仍占GDP的六%左右,鄧小平認為削減國防預算是推動經濟成長的一種方式。一九九○年代初期,軍事開支降至GDP的二%左右。這段期間,中國其實是悄悄仿效日本戰後的經濟奇蹟,享用美國軍方保護傘的經濟效益,但中方從未承認,同時還持續公開抨擊霸權主義。
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出現反思。只要蘇聯存在,中國就把它視為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美國則是比較良性的霸權,或至少威脅性較低。蘇聯的解體使中美和解的威脅消失了,在此同時,美國對天安門事件的負面反應,則被視為後冷戰時期美國志得意滿,意圖以自己的想法改造世界的前奏。波斯灣戰爭顯現美國在先進軍事科技方面的驚人實力,使傳統集結式陸上軍隊(例如中國迄今依賴的軍力)幾乎毫無用武之地。
因此,中國放棄近二十年的最低國防投資政策。一九七○年到一九九○年間,中國的軍事開支每年僅增加一.八%,遠比通膨率還低。後來的二十年,每年預算成長十五.五%。一九九○年以前,中國享有「和平效益」,亦即減少軍事開支以推動經濟成長。一九九○年後,中國可享有相反的利益:利用迅速的經濟成長來提振軍事開支。即使國防預算每年以十五.五%成長,中國在軍事上的花費僅占GDP的二%左右。二○一二年,中國輕易就成為全球軍事預算第二大的國家,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的計算,高達一千六百六十億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是兩千五百億美元)。客觀來看,那比東亞其他國家(包括日本)的國防預算加起來還大,也比中國兩大陸地鄰國(俄羅斯和印度)的國防預算加總起來還大(而且也大於英國、法國、德國的國防預算總和)。中國的軍事預算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但美國的軍事開支中只有一部分放在東亞地區。
中國並未面臨像冷戰那樣的重大軍事威脅,如此大規模累積軍力的唯一合理目的肯定和地緣策略有關,是為了對抗美國的主導地位,同時也一舉戳破了冠冕堂皇的反霸權主義說法。那些行徑看來確實不像願意活在美國軍事保護傘下的其他工業化國家會做的事。
中美軍事關係的關鍵是發生在二○○○年的台灣大選,台灣人不再支持一九四九年以來幾乎壟斷政治權力、一向主張兩岸統一的國民黨,改選了主張獨立的政黨。中國把飛彈瞄向台灣進行恫嚇,美國因此派出兩艘航空母艦以阻止中國入侵的意圖。這次事件成了分水嶺,提醒中國面對美國的軍事優勢時,無法達成其最神聖不容更改的國家目標之一。於是,中國推動軍事現代化計畫,最終目標是阻止美國進入中國海域。就像一九五○年代以後蘇聯打造海軍一樣,中國打造海軍的方式也不對稱。中國偏重潛艇和導彈的製造,而不是挑戰美國在航空母艦方面的優勢。一九九九年,中國海軍推出超靜音的宋級柴電攻擊潛艦,配備難以閃避的追蹤尾跡魚雷。二○○六年其中一艘潛艇潛進了小鷹號航空母艦(Kitty Hawk)的防衞網,卻未被偵察到,因此震驚了美國海軍。更令人注意的是,「東風」DF21D陸上可操縱彈道導彈的研發,專門用來摧毀駛進中國海岸方圓一千多英里內的航空母艦。當年駐守在北京的美國陸軍武官,在回憶錄中提到中國軍事計畫和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的關連:「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高級軍官第一次提到以彈道導彈攻擊航空母艦,是我們兩艘航空母艦出現以後。他把手搭在我肩上說,我們要用彈道導彈擊沉你們的航空母艦,我們在這方面聊了很久。」
如果中國累積軍力只是為了防止美國干涉台灣的問題,那可能只有區域的重要性。但是,其戰略意涵遠比那個還大。台灣之所以對中國很重要,不只是因為收復台灣象徵著「百年國恥」的明確結束(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座落在北起日本、南至菲律賓的連串島嶼中間,這些島嶼聯合起來阻止了中國進入太平洋。台灣若是回歸大陸,這堵牆就打開了關鍵的突破口。不過,日本看到的議題正好相反:
台灣是日本海上航線的重要組成,萬一台灣被納入中國,南海就成了中國的海域,通往中東和東南亞國家的航線都會受到中國強大的影響。萬一東海也納入中國的影響範圍內……朝鮮半島將落入中國的勢力範圍。此外,中國可能利用台灣作為進入太平洋的踏板……台灣是日本的「命脈」。
許多策略家認為美國對陸上反艦導彈沒輒,新一波的軍事科技可能讓美國引以為傲的航空母艦淪為廢鐵,就像一九二○年代和三○年代航空母艦剛出現時,戰艦突然落伍那樣。他們擔心中國的反介入和區域阻絕策略(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軍事用語是A2 ∕ AD)使中國海域變得太危險,讓美國海軍難以掌控。二○一○年,詹姆斯.克拉斯卡(James Kraska)寫了一篇前景堪憂的論述《在二○一五年海戰中美國如何敗給中國》(How the United States Lost the Naval War of 2015),裡面描述中國彈道導彈突襲摧毀東海上的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
西太平洋上充滿依賴貿易的國家,而海上航線的安全向來是由美國海軍提供。尤其,日本放棄追求帝國大業以換取美國的保護,從而融入戰後秩序。中國的軍力累積反映出中國拒絕接受美國治世,中國的軍力若是威脅到美國提供的保護,戰後秩序的根本前提可能會開始崩解。
事實上,證據顯示崩解已經開始了。日本選出了保守派的總理,他意圖修改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開始強化軍力。日本的行動是那個鄰近地區的普遍趨勢,西太平洋周圍的國家,從兩韓到澳洲都悄悄地加速海軍的軍備競賽。二○一○年,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吉原恒淑和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指出:
亞太地區海軍軍備競賽的步調正在加快,那和一個世紀以前歐洲陷入的軍備競賽不同,當時列強是在競爭軍艦的數量和噸位。如今,這種海上競爭的一大要件是發生在水中作戰的陰暗世界,現在各國不使用一次大戰以前成為軍備焦點的重炮戰艦,而是在未來十年啟用看似不起眼的小潛艇。
潛艇和反潛戰是這場新軍備競賽的主要元素,因為東亞這些貿易國家最關心的是航線運輸的保護,另外可能還包括封鎖潛在敵人的能力(雖然大家都心照不宣)。該文發表之後,軍備競賽開始浮上檯面,中國推出首艘航空母艦,日本推出兩艘直升機航空母艦,那些在許多人眼中其實是小型的航空母艦。
(本文為《大國的不安:為什麼經濟互相依賴不會帶來和平?為什麼多極化的世界非常危險?》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大國的不安:為什麼經濟互相依賴不會帶來和平?為什麼多極化的世界非常危險?》 When Globalization Fails: The Rise and Fall of Pax Americana
作者: 詹姆斯‧麥唐諾(James Macdonald)
出版:如果出版社
日期:2016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