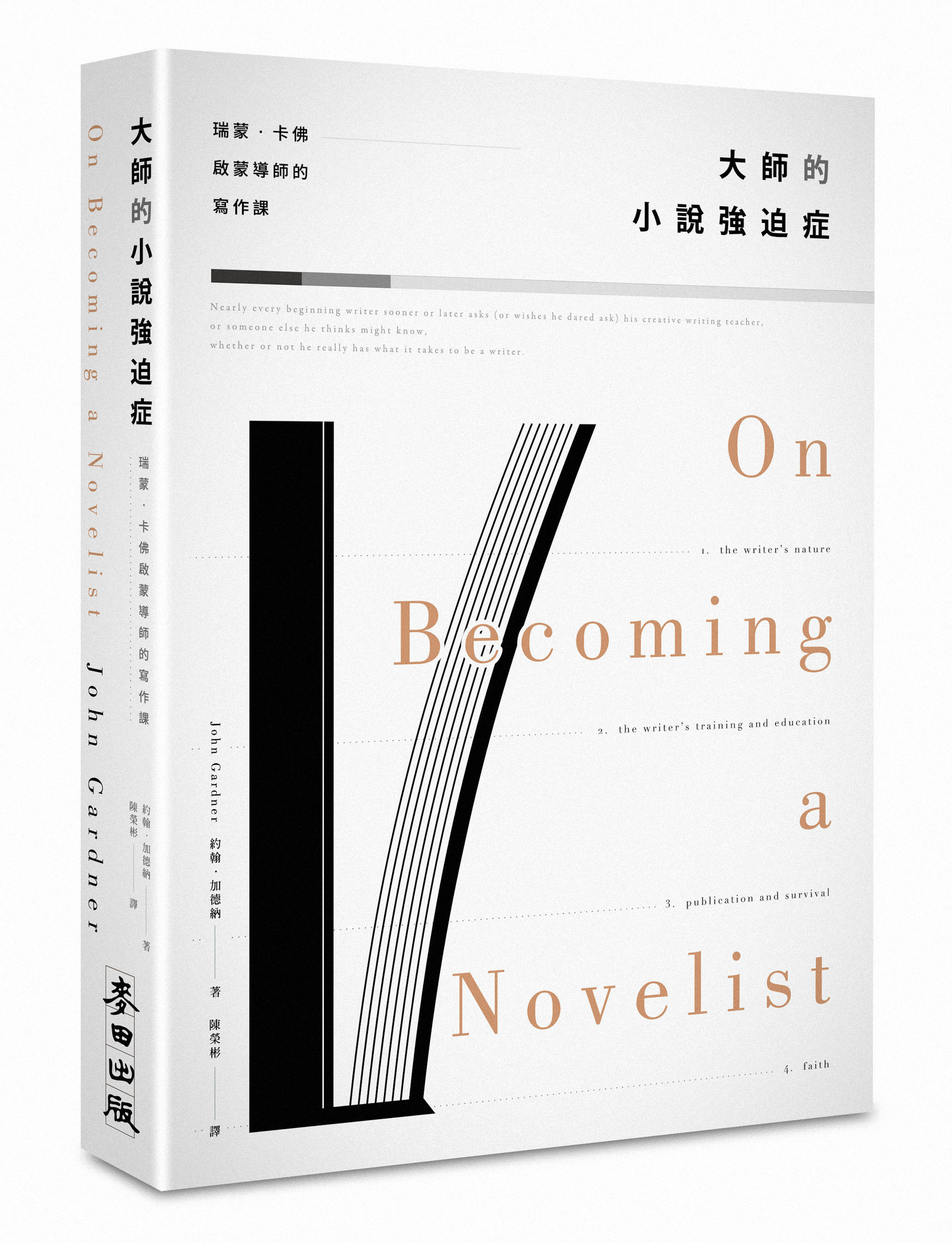
文|約翰‧加德納
譯|陳榮彬
不太成功的作家可能會這樣寫
成功機會最小的作家(那種會讓人立刻說出「我想他沒辦法」的作家)對於語言的感受性是最奇怪而且改不過來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那種動不動就會寫出下列句子的作家:「她的眼睛閃耀著喜樂目光」、「可愛的雙胞胎」,或是「他那發自心底的大笑聲」。這些都是枯燥乏味的表達方式,顯現出那位作家日常生活的情緒宛如殭屍,乏善可陳,或者他覺得沒什麼值得讓他認真思考,並以自己的話說出來的事物,所以他只會寫:「她忍住不哭」、「一邊嘴角往上揚,友善地微笑」、「用他那特有的滑稽方式把眉毛往上抬」、「他那寬闊的肩膀」、「他那環抱的手臂」、「她的雙唇動了一下,露出一抹微笑」、「他的聲音嘶啞」,還有「一片片赭色鬈髮蓋住她臉龐的兩側」。
上述措辭之所以有問題,不只是因為它們是陳腔濫調(因為過度使用而用爛了),也因為它們顯露出作家的貧乏心靈。用語言描繪這個世界時,不同的語言習慣使我們戴上一張張面具;在不同的情境中,也會戴上不同面具。上述那些貧乏措辭符合某種基督教樂觀精神,可以說是最成功的一類面具,至少在某些棘手的情況下很管用。這種面具為什麼會常被人拿來寫作,反而沒有成為一般用語?換言之,為什麼寫作藝術的功能會變成美化現實世界,使其平靜?我也不知道答案為何,但可能與我們早年所接受的寫作教育有關,因為符合禮節就是寫作的要求之一,又或者是因為我們最初遇見的老師往往強調,文字就是該讓學生變乖(或者壓抑他們的情緒)。
總之,任何小說家如果不能扯掉這種樂觀面具,那就會被毀了。常常透過那種措辭來表達枯燥樂觀主義的人,在看待或感覺事物,以及講話時,難免都帶著定見,結果會有兩個:他們會失去精確地看待事物的能力,或者是無法與一般人溝通,能講得上話的對象只剩下看法與感覺跟他們一樣樂觀而扭曲的人。一旦心理對於某種語言存有強烈認同感,任誰就再也看不出那種語言扭曲了現實,同時會覺得為什麼其他人都那麼盲目(但其他人只是比較謹慎,或者是小心翼翼而且語帶諷刺)。對於現實的看法如果扭曲了,任誰也寫不出好的小說。讀者在閱讀時會用現實世界來參照書裡的虛構世界,小說家如果帶著幼稚或者令人厭煩的生活態度創作,他的作品很快就會讓讀者感到不耐。
樂觀的面具只是逃避現實的許多常見方式之一。我們來看看某位知名科幻小說家寫的幾句話:
人們通常不會跟你說他們心底的真正想法。像是他們對上帝的看法或他們害怕會像自己的祖父一樣發瘋或他們對性行為的看法或者是他們看到你挖鼻子後順手在褲子上抹一抹,覺得你很噁心。他們總是跟你好來好去,因為沒有人想當討厭的傢伙,而且若是講了太多真話,任誰都會變成不受歡迎的人。尤其是他的確看到你挖鼻子,又用褲子擦手。如果他看到你把挖出來的東西吃掉,那就更糟了。
譯註:引自哈蘭.艾里森(Harlan Ellison)一九七○年的《邊緣之外》(Over the Edge)。
二○、三○年代的「寫手」(hack writers)慣用樂觀的風格,但後繼另一批寫手的風格卻開始「反樂觀」。這兩代寫手都喜歡用斜體字(像是上述引文裡面的人們通常不會跟你說他們心底的真正想法。),前者的樂觀開朗被某種沒有根據的憤世嫉俗精神取代,「寬闊的肩膀」也變成了「心底的真正想法」,或者更糟。新一代寫手改用一些結構零落的句子(若是想要讓自己的句子看來充滿情感,這是常見的手法),而且逗點也不見了(「祖父或性行為或你有多噁心」),藉此模仿福克納那種像是在走鋼索的修辭手法。(略去逗點是沒有問題的,除非你是想要加強句子的力道,但這也表示你的句子本身不夠力,沒有情感。)
「一邊嘴角往上揚,友善地微笑」是新一代寫手不會使用的句子,他們的說法是「跟你好來好去」,意思是講話的人都是虛偽不實的,嘴長在臉上不是用來說真話。(這種剔除人味的措辭變成某些粗劣偵探小說最愛的技巧之一,例如小說裡會把「身穿灰西裝的男人」改成「灰西裝男」,把「身穿仿鯊魚皮羊毛衣的男人」改成「鯊魚皮男」,句子就變成了:「灰西裝男往鯊魚皮男那邊看過去。他說:『滾開。』」甚至有些寫得相當不錯的偵探小說也會這樣。這就是所謂的有樣學樣。)
這種「反樂觀」風格的小說裡面常會出現一些粗魯的笑話與畫面,還有從外語中借用的俚語,藉此讓那些老古板感到震驚。當然,不會真的有人感到震驚,只不過有些人被惹惱了,誤以為那種情緒是震驚。之所以會被惹惱,是因為那些文字非常虛偽,只是模仿那些以前已經太常被模仿的東西。值得一提的是,這一類作家的問題並非在於他們比那些「樂觀的」作家更差勁。這兩種作家幾乎是同一類人:兩者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唯一渴望的就是美德、正義與明智;兩者之間僅有的差異是風格不同。上述那一位科幻小說家筆下的角色「開膛手傑克」發現自己被「烏托邦人」耍了之後,感到義憤填膺,咆哮了起來:
神經病,屠夫,色鬼,偽君子,小丑。
「你們居然這樣對我!為什麼?」
他開始胡言亂語……
年輕作家如果迷上了粗劣的科幻小說、最糟糕的冷硬派偵探小說,或是那種「說一不二」的嚴肅小說(總之就是所有將一切經驗視為垃圾的各種小說),只要肯努力,也許就能出版作品,但他很可能永遠無法成為小說藝術家。或許他也不在乎。這一類寫手有時候頗有成就,甚至受人景仰。但是就我看來,他們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微乎其微。
「樂觀」與「反樂觀」的風格會對於作家造成同樣的局限,導致作家可能忽略經驗或簡化經驗,除了有相同信念的人之外,其他人都被他們排拒。馬克思主義者的語言可能也會造成同樣的效果,還有印度教的行話、電腦的專門術語(例如「輸入」),或者商界與法界常用的乏味暗喻(「到了像起司一樣一塌糊塗的地步」)也都是。看到那種只會用某種語言風格來表達所有看法,並為此安心的學生,能不為其感到憂慮嗎?
然而,就算某個作家有語言風格過於死板的問題,也不能說他就注定不能成功。儘管某些想要當作家的人也許早已習慣使用過於簡化的語言,改不過來,但事實證明其他看起來問題一樣嚴重的人卻能改變。重點是他們必須了解問題,努力改善。問題的解決之道,是克服自己後天養成的糟糕品味,搞清楚自己和別人的語言習慣有何相同與相異之處,學會欣賞各種語言風格的相對價值(與其局限)。這意謂著他們可能必須跟某位語言敏銳度很高的老師密切合作,這位老師的「英文很好」,不只熟悉「標準的英文」,也要擅長生動而意味深長的語言,而且不見得是那種「標準的英文」。或者,他們必須好好思考如何用字遣詞,思考語句結構、韻律等類似的問題;也可以閱讀跟語言有關的書;最重要的是,要讀一些受到普遍肯定的文學作品。
每一個字句,無論是神聖、客觀或者猥褻的,都有它們的適用領域,在這些適當的情境中,人們能夠有效而自在地使用那些字詞,而不會冒犯任何人。例如,「今天我們聚集在此地」是教堂裡常出現,完全不會有違和感的句子,但如果由教室裡的教授說出來,聽起來會帶著嘲諷意味,若出現在商業信件裡,簡直就像是瘋了。至於「金髮青年」這幾個字在一本詞藻華麗的老舊小說裡,並不會引人注目,但如果是一本文字風格口語化的現代小說,就很突兀了。一種喜劇般的文化觀有助於我們了解這種現象:這種觀點認為所有世人與文學風格都有令人覺得好笑的不完美之處,也就是人類與其語言都很容易變得自滿驕傲,裝出謙卑的樣子,想耍心機卻很愚蠢,自命聰明或者假裝自命聰明。如果人類的所有風格都傾向於反映出人類的「丑態」,我們就沒有必要盲目敬畏或鄙棄某種風格。我們只需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想透過文字表達什麼(先把東西寫出來,接著自己重讀一遍,看是否真的說出了你的想法),然後持續修改用語,直到自己對文字無法提出任何質疑。
從一個更具哲學意涵的角度說來,語言難免帶有價值評斷的成分,如果不好好檢視自己的用語,就有可能不小心幫自己不認同的價值背書,到時候就丟臉了。有些比較敏感的人可能對於英語文化中貶低女性的用語感到不悅,像是我們想說「人們」的時候,選用的卻都是一些男性的字彙,例如man、men或者mankind,或者像我在提到作家這種人的時候,無論男女,我大多是用he(並不是我個人偏好此一用詞)。我們或多或少都會受語言矇騙,提到「電話線路」就會想到「大腦」,提到「太陽」就會想到「升起」,提到「發現」(隱約帶著一點柏拉圖式的哲學意味)就認為是某種一直存在的事物終於揭露(例如,「他發現了一種除煙的新方法」)。但是某些人往往被語言騙得團團轉,因為某個小圈圈的規範與偏見而「綁手綁腳」,或者因為無法擺脫某種文學模式的影響與看法(無論是福克納、喬伊斯,或者粗劣科幻小說的常見用語),而無法成為第一流作家,原因是這種人永遠無法看清真相。
(本文為《大師的小說強迫症:瑞蒙‧卡佛啟蒙導師的寫作課》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大師的小說強迫症:瑞蒙‧卡佛啟蒙導師的寫作課》On Becoming a Novelist
作者:約翰‧加德納(John Champlin Gardner)
出版:麥田
日期:2016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