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場研討會的衝擊之後,阿岡本放棄了他的法學研究,以及他的詩人活動,成為一個哲學家。
文|Leland de la Durantaye
譯|蕭育和
1968年六月,26歲的阿岡本遠離波瀾壯闊的巴黎,出席了兩場研討會,這一年對他來說意義非凡。第一場是哈佛大學舉辦,大名鼎鼎季辛吉主持的研討會,參與者都是各國政府精心選拔的「未來世界領袖」。
某一天課堂上,阿岡本打斷季辛吉,告訴他「你根本完全不懂政治」。季辛吉微笑以對,就在那一年年底,「完全不懂政治」的季辛吉成為尼克森的國家安全顧問,這是他往後歷練各種政府高階職位的開始。
阿岡本出席的第二個講座在法國南方,作東的是法國抵抗運動的英雄詩人夏爾(René Char),講授課程的是高齡79,歐陸哲學的高堡奇人海德格。在這場只有八個人參加的研討會中,有一天,海德格對出席的人說,他看不到自己的界限,但學生們也許看得到,而這就是界限的本質,也是學生的本質。
兩場研討會的衝擊之後,阿岡本放棄了他的法學研究,以及他的詩人活動,成為一個哲學家。至少是在1995年,這位哲學家的聲名,已經走出了學術小圈圈。讓他聲名鵠起的是《牲人》(Homo Sacer)──「牲人」系列的第一部──其壯志在於連結在季辛吉課堂上討論的政治問題,以及海德格講座上的那類東西。
讓很多人相當錯愕的是,阿岡本用納粹集中營,來類比了現代生活的法學空間,「牲人」系列的第二部《奧許維茲殘餘:證人和檔案》(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更是讓他飽受批評。20個年頭過去了,「牲人」系列七本大作構成的哲學與政治計畫,來到了令人意料的戲劇性完結。
阿岡本這個充滿雄心壯志的「牲人」系列,目的是要賦予政治新的根基。「牲人」是一個來自羅馬法的法學用語,用以指稱因為罪過嚴重,而被驅逐的人,透過「牲人」的儀式宣告,這個人得被殺戮而不受懲,也無法用於需要活人生命的獻祭儀式(總是不能獻祭對你毫無價值的東西)。
「牲人」被除名在社會活動與共同體律法之外,他唯一適用的法律就是成為被驅逐之人,而且無法撤銷。阿岡本選擇用這個形象來掛名一個渴望賦予政治新根基的書系,聽來有些詭異:當然,這一切端賴於你怎麼看待當前的全球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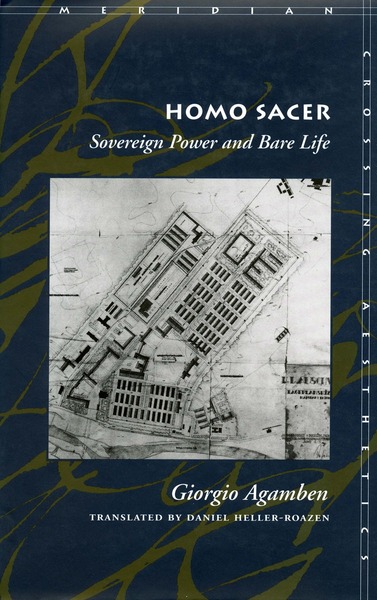
牲人系列第一部:《牲人:主權生命與裸命》英譯本書封。
在「牲人」系列第一部,讀者很快地就習慣了這樣基進的命題。「今天,(集中)營而非城邦,才是西方的生命政治典範。」這並不是說今天絕大多數的人都生活在集中營的實境體驗,而是說,公與私,神聖與世俗的劃分,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劇變,伴隨著對無界限暴力的臣服,新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形式,正在瓦解過去那些保持開放的空間。
「牲人」系列往後的作品,看起來差不多都像是對首部曲的增補與發展,很多讀者因此很合理地期待,為了鞏固這個並沒有完全得到支持的首要命題,「牲人」計畫會像是註解那樣無限期延續下去,不會有真正的終點。
過去二十年來,「牲人」系列引發了許多關注、興趣、讚賞、譴責、誤解乃至於沮喪,沮喪有兩種類型,第一種與書中某些論稱的煽動性本質有關;第二種沮喪來自於首部曲如此粗略描繪的理論擘劃:潛能與行動之間、純粹生物性生命與政治性界定的生命之間、存在與本質之間、秩序與無政府、政治與本體論之間,各種新的關係。
即便最後幾部曲說明了許多事情,這些根本的形而上連結與斷裂,仍然一如1995年現世的首部曲那樣,不甚明朗。這些如此概略描繪的本體論創見,導致許多人感到高深莫測,並譴責阿岡本故弄玄虛。出於這個理由,「牲人」系列的第八部終結《肉身的踐行》(The Use of Bodies; L’uso dei corpi),有許多人可能得要爭論好一陣子,這是系列中最細膩、最豐富、旨趣最為駁雜的一本,但它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將系列前作的種種關注,以及其對法律與禮儀性實踐、革命與鎮壓、古典哲學、主權、安濟、修道院教團、大屠殺等等,龐雜詳盡的檢視通通集結起來。
《肉身的踐行》一開始就告訴讀者「熟讀牲人系列前作的人,將會知道,不要去期待在這裡會有新的起始,更不用說,會有完結。」這是閱讀這本系列終作,打從一開始完全毋須驚訝的理路,但出奇的是,完讀到最後,需要細細思量的,卻是,在探索結論,與探索新起始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
在「牲人」首部曲出版的45年後,毋庸置疑的是,兀立在阿岡本著作中,各種(很有必要的)翻譯,反映了阿岡本博學的哲學風格,與優雅的書寫姿態。在諸多領域,阿岡本都擁有高超的駕馭能力:從古典學到現代法學、從古希臘到現代德國、從神學到藝術史,再到詩學與本體。可是,《肉身的踐行》的核心論題卻不難掌握,甚至也不需要參照古希臘或現代德國。
這個核心論題是:什麼是你的?而你會如何使用它?比如說:你的身體是你的,而你運用這副肉身過著你的生活,而在什麼情況下,它會受制於種種限制?又限制到什麼程度。總之,肉身是如何被生命是什麼又為何存在,承擔什麼義務,又被賦予哪些使命的概念,所制約與安身?
阿岡本用來問答這些論題的方法,他稱之為「系譜式」,也就是說是歷史性的。這很明顯是借用傅柯,就像傅柯從尼采那邊借用過來一樣,當然,比起這些概念沿用,有更多值得注意的東西。阿岡本的系譜學,移動到一個完全不同,特別遙遠的地帶,阿岡本這麼說:「傅柯曾經對此,用過非常美麗的比喻:歷史研究就像是當下投射到過去的陰影,對傅柯來說,投影被回溯到十七與十八世紀,對我而言,這道投影更要長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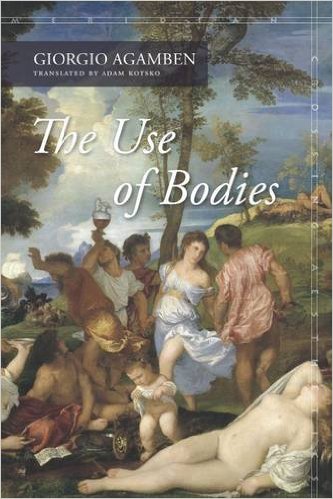
牲人系列最後一部《肉身的踐行》英文版書封。
《肉身的踐行》所投射出來的影子顯然長很多,這個本體論、神學、哲學與詩學共同探索出來的投影,其邊界被阿岡本說是「人類起源學」,或者,我們是如何變成現在這樣的?阿岡本所有別具一格書寫,至關重要的,就是這個東西。
在《肉身的踐行》與「牲人」系列中有待處理的問題,有一個解答:主體性。阿岡本對這個概念演進的各個階段,有極為細緻的系譜學研究:從古希臘哲學到當代、從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到斯多葛、聖保羅與教會神父、經院哲學、萊布尼茲與史賓諾沙、一直到大成於海德格的德國觀念論。
主體這個字就其字面原意來說,指的是「壓倒」或「在之下」,其拉丁文解釋來自於希臘文與三位一體論的「質」,雖然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完全沒用過這個字,但到了公元二世紀與三世紀,這個字詞開始隨著斯多葛學派而頻繁使用,此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以各種不同的名義,影響了現代的主體性概念。
在古希臘的本質論中,主體就其字義來說,指的是一個過程的殘餘或剩餘,像是液體蒸發後的固體殘留(亞里斯多德只有在這個意義使用這個字,那是他在討論尿液)。《肉身的踐行》的第三部分與最後,阿岡本討論了「形式生命」(form-of-life),生命是什麼而我們又該如何踐行,被賦予完全不同的意義,這也是一種完全不同的主體性概念。
從阿岡本對「使用」這個字的處理,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來它與「所有」截然不同,阿岡本最常舉的是方濟各教團,像是基督佈道那樣,「不所有」東西,而單單只是「使用」的典範。就使用的主體來說,像是詩人荷爾德林稱之為「對屬己之物無拘的使用」那樣,阿岡本認為,我們固然可以把自己看作性格使然,理智導引或者冥冥註定要做什麼,但也許把自身當作所有踐行的總和,可能更好一些,像是在某些情境中的奔放無拘的踐行,我們發覺自身正在膨脹那樣。
我們不管是為己或為人的生命形式,都可以不需要是剩餘出來,在某個部分之下的主體,可以像是某種結實,又遠不受制於具支配性地位,對阿岡本來說正經歷劇烈危機政治概念的東西。對於我們當前的緊急狀態,毫無疑問得承認,有重新構思全球處境的需要。
在另一本「牲人」系列最近出版的著作《內戰》(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中,阿岡本說我們當前的狀態是一種「全球性內戰」,為免懸疑,精確照錄:「在世界歷史這個時間點上,內戰所採取的形式是恐怖主義」,更精確地說,「當生命本身為政治所處理時,全球恐怖主義就是內戰所採取的形式」。
這樣的說法,對於不太願意接受本體論界定與政治界定實乃密切相關這種想法的人來說,可能有一點摸不著邊際,特別是當要落到那些凡俗與殘酷的細節時:這個被勘破的真相,是要怎樣跟聚焦於更具體的要素,像是中東的石油、被遺棄的阿富汗戰友、伊拉克、激進伊斯蘭的崛起、教派鬥爭、經濟掠奪、全球資本流動等等一長串具體因素清單、全球恐怖主義的解釋,並肩而行呢?
阿岡本的說法是,固然是現代現象的恐怖主義,還是有其古代源頭,並且所代表的,不單是在世界特定角落的疆界爭端,也是世界歷史中懸而未決的這麼一種個別或共有的經驗片斷,它關注的是單純的生物性過程,而被排除在政治性考量之外,然而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這成為國家所照看監管的東西(這是傅柯把現代政治稱為「生命政治」的理由),值得一說的是,這是個複雜的複合經驗,而非完全無法改變的事物狀態。
出於生命政治已經失衡這個理由,在「牲人系列」的別處,我們被告誡,通過這個首要的區分──神聖與凡俗,人與動物──要去重新思考政治是什麼,這樣重新概念化的工作必須開始。要讓例外的殘酷狀態不再成為法則,整個體系不只是需要改變,而是要推倒重練。
追隨馬克思與韋伯的腳步,更精確地說是班雅明與施密特的腳步,阿岡本在「牲人」系列反覆強調政治概念有其神聖性血脈,政治神學形構我們思想與體制的程度,但不只是政治概念,西方文化中的文學與藝術概念也被阿岡本視作神聖性血脈的分支。
1964年演出義大利電影《馬太福音》的阿岡本,那時頭髮茂密。
在另一本不屬「牲人系列」的晚近著作《火與故事》(阿岡本近年來不尋常地多產)中,阿岡本說了一個關於火的故事,這個故事也曾經被阿格農(Shmuel Yosef Agnon)、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維瑟爾(Elie Wiesel)還有其他人說過。猶太教神秘主義創建者Baal Shem Tov在遇上難解問題時,他會走進森林,升起火,口念神聖的咒語,接著他就會得到解答。一個世代過去了,繼承人遇上難題時,也同樣會走進森林,雖然已經忘了怎麼升火,還是可以禱告,依然可以得到解答,反正有所悟也就夠了。再一個世代過去了,後繼的拉比又面臨到解決不了的問題,雖然不會升火,也不再記得怎麼禱告,能走到森林裡的那個地方,而這樣也就夠了。幾代之後,最後人們會發現自己處於這樣的狀況,「我們不會升火,不會禱告,甚至也忘了森林中的那個地方,我們所記得的就只剩下這個故事。」而據說,這樣其實也就夠了。
阿岡本說這個火的故事,是「文學的寓言」。文學沒有任何最後的啟示或轉化,它不是語言終極的熾熱核心,更不是我們只要在正確地點,說出正確字句,端坐在火面前,就可能會發現的東西。阿岡本相當喜愛維根斯坦的一個短句,「借助詩,才真正完善了哲學。」這當然不是說哲學完全只能用三行體來寫,而是說,詩是哲學在語言中,所能完善的最高形式。
在《火與石》的其他地方,阿岡本說「書寫意味著凝思語言,假如你不明白,不熱愛自己的語言,聽不到低語的咏頌,發不出細膩的哀歌,那你不會是寫作者。」這時候的阿岡本,開始像是詩人一樣,對語言有著高度的敏銳。不僅是對語言慎微的使用,也在於處理哲學問題的方式,阿岡本對「形式生命」、「運用踐行」、「內戰」、「生命」、「生命形式」與「牲人」等等詞彙都有細膩幽微的語言學分析,又不至於瑣碎偏題。
但阿岡本終究不是維根斯坦,他也曾經改寫維根斯坦的話,「只有把哲學論題闡述為關於字詞意義的問題時,它們才會變得更清楚。」對阿岡本來說,哲學並不是一個封閉體,不管是它關心主題,還是書寫,語言的界限到哪裡,哲學的界限就到哪裡。
於是,在哲學中很自然發生的現象是,份量最大,比重最重的概念,往往都是無法翻譯的,哲學家對於這類概念的使用往往匯聚了多重意義:柏拉圖的「理型」(eidos)、笛卡兒的「我思」(cogito)或者海德格的「此在」(Dasein)。在阿岡本這裡,也有一個核心的詞彙:inoperosità,雖然字源相近,但語言風格與聯想有點距離的英譯是inoperative。對阿岡本來說,這個字指稱一種不再運作與活動的無為模式,不管是進行中的行動,還是已經完成的成品。而他賦予這個詞的意義,最好還是透過亞里斯多德來理解。
亞里斯多德認為,作為有其自身目的的幸福,是人世間相當獨特的東西。即便是在榮譽、愉悅與理性的狀況中,我們也都不是單單欲求這些東西本身,而是「也著眼於幸福,通過這些東西來斷定我們是不是會快樂。」亞里斯多德坦承,「要說幸福是最主要的善似乎是陳腔濫調。」而要讓它不只是老生常談,就要處理人生而為人的目的問題:
「就像對一個吹笛手、一個雕塑家或者任何一個手藝師,以及,普遍而言,對所有那些有一種特定作用或實踐行動的人來說,善…被看作在於這個作用,所以,對人來說應該也是如此,如果他有某種特定作用的話。難道要說木匠與石匠有某種特定作用跟實踐行動,而人卻是天生沒有嗎?」
木匠跟石匠當然有其作為木匠跟石匠的志業,但亞里斯多德問的是,在另一個作為人的層次上,他們是否同樣有其志業?說到志業或作用,等於是賦予人整體一種使命,一種根本上界定人之為人的活動。亞里斯多德毫不令人訝異地停止琢磨人是否有集體的志業這樣的問題。阿岡本指出,亞里斯多德問的這個問題「人是天生沒有特定作用的嗎?」應該更精確地譯作「人是天生無為(senz’opera)的嗎?」而阿岡本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阿岡本看來,人並沒有這種需要完成的千禧年或彌賽亞式使命
在所有以「牲人」系列之名而寫下的作品,阿岡本看到了以目的來看待世界,把人的本性當作涉及某種使命(不管是集體還是個別的)的完成,在政治上的巨大危險。對阿岡本來說,海德格執迷於,一個有其使命時代的想法,正好標誌了他這位哲學導師的界限。阿岡本在《肉身的踐行》中說得很明白,海德格從《存在與時間》開始的,對於「此在」的分析,之所以終生未能完成,以至於最後只能放棄的主因,正是因為海德格的此在,肩負著使命,對某個時期的海德格而言,這個使命跟納粹是相容的,這就讓此在問題變得如此棘手。
而在阿岡本看來,人並沒有這種需要完成的千禧年或彌賽亞式使命,更沒有聖靈授命,必然要做的功,沒有必須要運作的機能。這並不是說我們有多墮落,有多迷失,距離那神聖語言、純粹思想與透徹經驗的明亮火花有多遙遠。而是說,既然不存在人必須要做的東西,就不會有必須要完成的使命,必定要做的功。
忘了怎麼生火,忘了怎麼禱告,忘了森林中那個地方。
基督教神學把時間看作如箭矢般線性前進,歷史向量與永恆的交會是主導基督信仰的神秘核心,而它其中一個作用是,無止盡地放眼一個最終會到來,終末這個現世的狀態,以及世界必須以另一種方式管治的過渡狀態。
「牲人」系列造就的另一個有趣效應,是2009年巴黎聖母院大教堂邀請阿岡本來演講,當時阿岡本所做的,就是向大教堂的虔誠之士們,嚴正告誡塵世間變革時機的富饒可能。阿岡本在這個演講中,所表現出來對於彌賽亞文本與主題的濃烈興趣,並不是如何讓(諸)神降臨塵世,聖靈充滿的問題,也不是如何召喚救世主來完結歷史救贖人類的問題。
假如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們作為共同體,作為人這類物種必須要做的,沒有什麼東西是生而為人必須要完成的,那麼就可以用新的角度來看待哲學、政治與藝術活動:沒有什麼是我們必須得要做的,人的「本質」就是無拘地踐行肉身,這就是阿岡本所謂的「瀆用」(profanation):一切凡俗者,即是神聖者。
這樣的思想在「牲人」系列以前就已經頗見端倪,在《幼年與歷史》(Infancy and History: On 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阿岡本說遊樂園是這樣一個「居民都忙於慶典,撥弄著各種器物與神聖詞語,卻忘記了這些器物與詞語的意義與目的」的國度,就像孩子的玩具世界,所有東西,到了孩子手上,都會成為他構築玩具世界的另類要件:物品的根源會被棄置,原來的作用會被遺忘。
阿岡本不只一次引用雕塑家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話:棄置,才能完成作品。看來,假如「牲人」的理論計畫現在已經擱置了,很可能是這套爐火純青的「牲人」系列,阿岡本已經完成了。
原文出處:
書籍資訊
[原版]《L’uso dei corpi. Homo sacer, IV, 2》-Giorgio Agamben,2014
[英譯本] The Use of Bodies (Meridian: Crossing Aesthetics) ,2016出版
插圖credit: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