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Daniel Steinmetz-Jenkins、Alexander Arnold
譯|蕭育和
前陣子,雅各賓俱樂部網站發佈的訪談〈我們能批判傅柯嗎?〉,引起了一波波的迴響。來自比利時,彼時還少有人知的青年社會學學者Daniel Zamora,在訪談中宣稱傅柯──這位過去三十年來為基進思想做出巨大貢獻的大師──不僅僅促成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風行,也必須為左翼政治的無能對抗,負起責任。
訪談刊出之後,立刻引來眾多學者與知識分子,氣急敗壞地為傅柯辯護。傅柯的支持者主張,即便傅柯從來都不是正規社會主義者,但他可從來沒放棄對基進政治的奉獻,琵琶別抱促成現代右派崛起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
Zamora並沒因此改變心意,訪談發佈後五天,他加碼發佈了另一篇短文。他說傅柯「以一種完全跟上當下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方式」,「為摧毀福利國家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意料之中,傅柯的辯護者,則繼續斥責Zamora的主張毫無根據、去歷史化、對傅柯作品的閱讀完全是意識形態導向。
作為某種實踐,知識分子三不五時就會爭辯彼此對重要哲學家的解讀,但少有討論能達到Zamora訪談所引發的強度。他確實觸動了敏感的神經,傅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在許多面向上其實是關於一個更深刻問題的代表性論辯:當左翼在70年代開始倡議「社會邊緣」,而非傳統勞動階級時,是不是個致命的轉向?Zamora要我們相信,這答案是肯定的,而傅柯就是這個轉向最大的驅動力。
Zamora這個引發爭端的主張,假定了一個對現代歷史的特殊理解。在他的解讀當中,過去這四十年來,左翼已經四分五裂並且迷失了方向。曾經左翼把自己當作對抗經濟剝削的主要力量,可是在70年代,許多左翼放棄了全面社會經濟變革可能的信念,對於核心的政治問題,採取了一個安逸與保守的立場。
Zamora主張,最需要為此負責的是70年代的基進論者,他們為了一個更聚焦於被排除者權利的陣地,賠上了「階級鬥爭」的大旗。這些以傅柯為首,誤入歧途的運動者,從而不再是變革社會經濟的力量,甚至不知不覺被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誘惑」,在他們的支持之下,新自由主義「大獲全勝」,造就了今天,前所未見,不平等現象驚人的舉世激增。
Zamora自認證據確鑿,信心十足地做出這些論斷。這個訪談的目標是希望更多人關注他甫編輯完成,於2014年底出版的新書《批判傅柯:80年代與新自由主義的誘惑》(Critiquer Foucault: Les années 1980 et la tentation néolibérale,英譯本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於2015年11月出版),這本書完整收錄了Zamora在訪談中只能粗略述及,控訴傅柯的有力裁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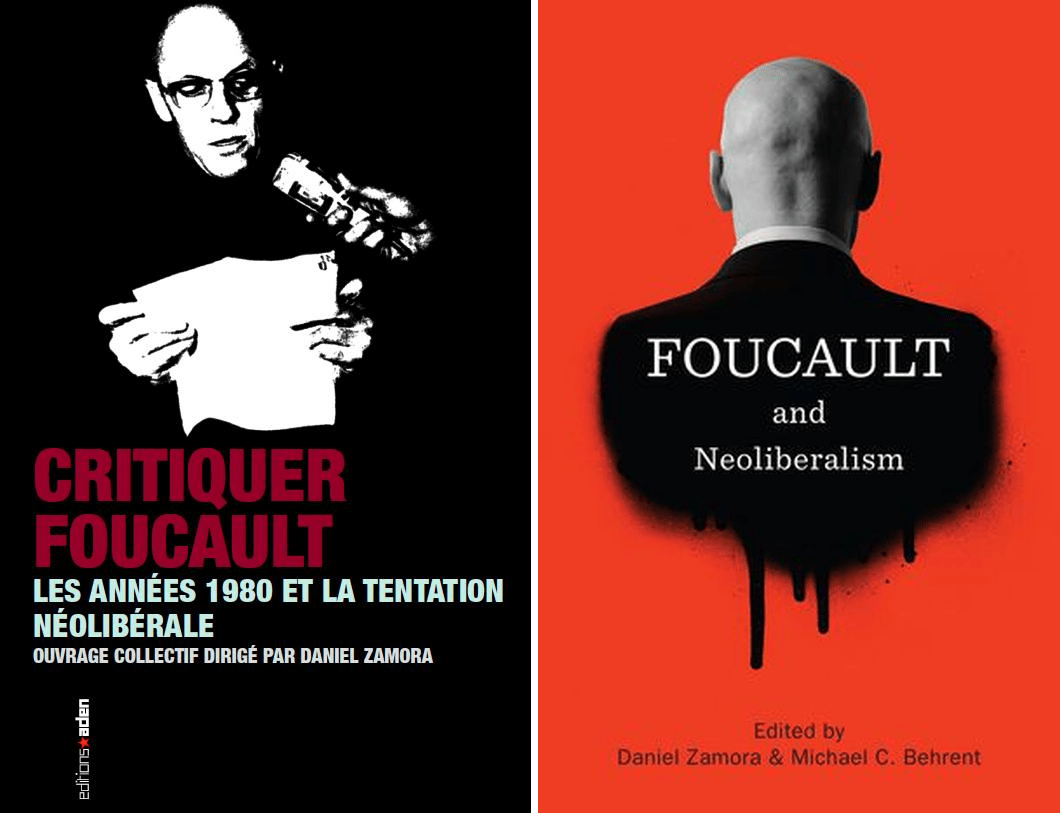
在這本書中,Zamora側重的是,他所認定的傅柯新自由主義傾向的癥結。其中最重要的論證之一,是傅柯與新自由主義極其相似,對於福利國家的批評。跟新自由主義者一樣,傅柯認定國家機制的強制性力量,已經到了一個無法接受的水平,同樣地,傅柯也跟新自由主義者一樣,相信需要用一種新的政治組織形式,取代戰後的福利國家模式,避免對其人民強加僵硬的結構。
對熟悉傅柯作品的人來說,傅柯對戰後法國國家的批判,並不讓人意外,對於那些強把人歸入預設範疇的結構,傅柯更是不遺餘力反對。在許多面向上,傅柯70年代對於國家機制的批判,立基於他早前,想要把個人從施加於他們身上的因襲規範中,解放出來的哲學計畫,他對國家的批判很明顯是質疑所有規範性結構,長期哲學計畫的一部分。
單純指出他對國家的批評言論,並不足以證明他被新自由主義「誘惑」,除了對國家的泛泛批評,我們可能需要證明,在傅柯與其時代的新自由主義者之間,還存在更深刻的親緣性,才能把兩者連結起來。
而Zamora要證明的就是這樣的親緣性確實存在。他的憑據是傅柯在70年代末期的公開講座,以及傅柯在他生命晚年所做的一些訪談。不過,Zamora討論的這些素材並沒有新東西,期待該書有任何新的檔案發現可能要失望而歸,而且,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些素材,可以發現這無法支持他所做的結論。
舉個例子來說,Zamora說,傅柯否認有「健康權」這種東西的想法,跟新自由主義者不謀而合。可是,傅柯固然不同意有這樣的權利存在,但他並不像新自由主義者那樣,認為國家提供醫療照護,將會與個人自由扞格,或者無益於個人自由。傅柯認定,健康無法量化,它是一種主體性特質,而非事實,因而無法透過法律來強制乃至於「保證」。
傅柯並不像Zamora所說的,「再生產」了新自由主義俗見,他採取的是一條不一樣的思路,他並沒有論稱個人應該在公開市場購買健康照護,傅柯談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來保障個人有生活在益於其健康的環境的權利,並且集體決定最佳方式的權利。
傅柯對法國70年代健康照護體系的批評並沒有疑問,但沒有「無條件支持健康照護體系」,並不代表傅柯對新自由主義誘惑退讓,像是Zamora要我們所相信的那樣。傅柯的批判旨促使人們創意性地重新思考這個體系,並同時維持它對健康照護的基本許諾。
在這些Zamora錯誤地指稱是傅柯屈服於新自由主義觀點鐵證的訪談中,傅柯對於公衛的關注,以及他對公衛體系能否透過市場實現的懷疑,其實都歷歷可見。傅柯這麼說,「不用說,我並不是主張一種野蠻的自由主義:有辦法的人得享健保覆蓋,沒本事的人就自己想辦法。」
Zamora對傅柯的批評也採取了另一種形式。Zamora指出,傅柯對於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思想許多重要的面向,都寄予同情。傅利曼經常被當作新自由主義的教父,傅利曼倡導最低收入補貼(the negative income tax),不管人們是否有工作,都能保證最低限度收入的負所得稅政策。
傅利曼說,最低收入補貼的好處是,不管個人的收入超出某個限度有多少,所有人都能有一個基本生計供給。通過移除國家對於什麼構成財富的「正當」與「不正當」分配,做成規範性判斷的能力,傅利曼相信,最低收入補貼能尊崇個人的經濟自由,而戰後福利國家則無法。
在進入傅柯對於最低收入補貼的看法之前,Zamora說傅柯很明顯被這樣的論理所吸引,傅柯1978年「生命政治的誕生」講座中支持這種負所得稅的分析,是他的佐證。在這個講座中,傅柯──一如他往常的學術生涯──解讀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文本,是著眼於理解其內在理路。
可是,Zamora卻說,當傅柯討論最低收入補貼的想法時,不僅僅只是描述而已,還「相當正面地評價它」。他的證據是,在讀到傅柯對於負所得稅的分析時,可以感覺到,對於負所得稅能避免強加行為模式,並一視同仁的好處,傅柯抱持了支持的態度。
Zamora必須得說「感覺到」對於這個想法,傅柯抱持了「某種支持」的態度,是因為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傅柯自己並沒有直接表現出這樣的支持態度。更遺憾的是,傅柯不只沒有明確的贊同,連隱秘的認可都沒有。
在開始慎重小心討論這個主題之前,傅柯告訴他的聽眾,他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在討論這個主題,「因為時間緊迫,也因為不想讓你們覺得無聊」,這看來不太像是一個據稱得到強力支持觀點的開場。
接著,傅柯討論這類負所得稅的用語,很清楚是在描述別人的立場,而非他自己的,他的討論基本上是臚列其主要效應與意涵。傅柯非常敏銳地指出,這個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確保人們,即便得益於社會救助,也仍然有找工作,成為經濟競爭者參與市場的動機。他這麼說,「通過負所得稅,個人會得到一個消費既定水平的保證,只要有足夠的動機,或者,你喜歡的話,足夠的挫折,他仍然始終會想要工作,而且比起領取補助,最好還是工作。」
就像傅柯正確指出的,社會救助並不會遏制找工作的動機,如果人們還是有工作能做的話,這是新自由主義看待社會政策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論點。但傅柯也解釋的非常清楚,這個態度本身有賴於另一個構成新自由主義的理念。
這個理念就是「經濟基本上是一個遊戲,它被發展成參與者之間的遊戲,而整個社會都被這個經濟遊戲給滲透,國家角色之所以重要在於它界定這個遊戲的經濟規則,並且保證這些規則可以確實適用。」
20世紀諸多知名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家,都團結在這個觀點之下,從海耶克與傅利曼,以及深受鼓舞,著手新自由改革的政治家,像是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然而,這卻不是傅柯所認可的。
傅柯也許已經發現,沒有規範性束縛的新自由主義,在某種意義是可取的,但Zamora沒有辦法說明的是,傅柯曾經在哪裡直率地辯稱市場可以完全取代國家,成為社會的主要組織性力量。
這樣的說法更沒有出現在傅柯任何已公開的作品或評論。假如傅柯並沒有力挺這麼一個對新自由主義來說如此重要的理念,那麼在完讀Zamora以後,就還是留下了這個問題:真的可以說傅柯向「新自由主義誘惑」俯首了嗎?
人類學家Jean-Loup Amselle的論文也論稱,傅柯確實被新自由主義所引誘,但Amselle所認定的是另一種形式,不只是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傅柯往後對於苦行修養的研究,助長了超資本主義。Amselle聲稱,這些研究讓人們相信不再需要為集體盡力,而要開始關注自身的發展。
毫無疑問,在他生命晚年,傅柯確實開始分析各種在心神與情緒上,個人能夠更好地照看自身的方法,同時,他也發現了新自由主義某些在哲學上幾乎繞不過去的面向。
然而,要說傅柯得為社會的零碎化──Amselle認為這助長了20世紀資本主義──負責,著實過度延伸,不只是誇大了傅柯思想中個人主義的程度,也高估了他對晚近歷史事件的影響。
這本書中的其他作者,並沒有像Zamora與Amselle那樣,宣稱傅柯對新自由主義的勃興,有那麼大影響力。他們的立論相對節制,歷史學者Michael Behrent的〈沒有人文主義的自由主義〉一文,就主張,要說傅柯為新自由主義吸引,主要是哲學上的理由。
傅柯是「策略性認同」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因為他認為這些理念少了他覺得反感的哲學個人主義,避免了對個人的規訓,而更傾向提供誘因來鼓勵或抑制個人行動,在傅柯看來,這是他對抗那些相信國家是全面變革主要動力左翼對手的有用工具。
可是,要論證傅柯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共享某些面向,並不等於證明他是新自由主義正向社會視野的擁護者。從Behrent的論文,只能論斷傅柯與新自由主義者之間,在一些哲學觀點上有相近之處,並不等於傅柯就贊同,新自由主義要把社會方方面面都與市場法則一致的構想,或者主張用政治來實現這個構想。
假如是這樣的話,說傅柯被新自由主義給「誘惑」其實非常狹義,也並不是那個往後四十年在政治上舉足輕重的新自由主義。畢竟,Zamora所描述的「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從來都不是Behrent所論證,吸引傅柯的那些東西,像是反人文主義。
更精確地說,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在政治經濟上的勝利,確實來自於這些新自由主義哲學家的啟發,但其運用與效果有更複雜與廣泛的緣由。有趣的是,Zamora企圖論證,傅柯得為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經濟不正義負責,但Behrent的論文對於這個壯志滿懷的理論計畫,卻貢獻甚少。
假如真的要批判傅柯的新自由主義觀點,恐怕在於傅柯錯估了新自由主義在其講座往後幾年的發展。Loïc Wacquant就在他的〈傅柯、布迪厄與新自由主義年代的刑事化國家〉論文中,就論稱傅柯對於19世紀與20世紀規訓社會的預測錯誤:一個通過像是監獄與收容所來控制、監控與常態化個體的規訓社會,其實正逐漸讓位給一個用比較間接方式來影響個體的社會。
Wacquant所論證的是,現實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像是勞動的去管制化以及金融市場,與規訓體制的擴張,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Wacquant這個傅柯的預測失準論,在Jan Rehmann的論文也得到共鳴。Rehmann認為,「治理性」這個傅柯認為對研究20世紀後期相當有用的概念,並沒有如傅柯所預想的那樣。
可是,要說傅柯對於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實踐的發展走向預測失準,或者他的概念並沒有如他預期那樣有用,都不能證明「後期傅柯的政治效應」必然有助於新自由主義的勃興,像是Zamora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
那什麼是「後期傅柯」的政治效應呢?據Zamora所說,傅柯引導左翼放棄了勞動階級,放棄了對抗剝削的戰爭,並對新自由主義的「反國家論」給予重要的支持,還加持了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政策,像是負所得稅與瓦解全民健康照護體制。
我們已經證明,Zamora所引述的,傅柯對於這些政策的討論,並不等於贊同它們。我們也已經看到,基於傅柯並沒有主張要用市場來取代國家,成為社會的根本組織機制,傅柯的反國家論也根本不同於新自由主義。即便傅柯相信捍衛勞動階級,對抗剝削並非70年代左翼最重要議題,這也不是什麼新東西。
早在70年代之前,傅柯就已經批評馬克思對於勞動階級的過度理想化,並且無法看到在資本主義結構之外,更多阻礙社會變革的東西。對傅柯來說,認為無產階級與對抗剝削的鬥爭是歷史動力這個理念,是19世紀思想遺留下來的東西,越來越無法適用於20世紀的現實。
傅柯認為,要真的催化變革,左翼需要的是以新的方式催生社會的新面向。
在傅柯所有主張中,Zamora認為最危險的就是這個主張。一旦左翼像是傅柯這樣,繼續傾向為邊緣而戰,而非為剝削而戰,左翼將會無助地被新自由主義碾壓。
Zamora這個宣稱並不孤單,四十年來,一直都有人把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勃興,歸咎於左翼在批判力道上失了準頭,無論是被維持現狀收編,還是孤身縮入學術圈。
對於晚近歷史的這類觀點,驅策Zamora著手批判傅柯,為了不讓左翼再繼續向下沉淪,Zamora相信,重要的是針砭出左翼錯誤轉向的時刻,好逆轉這個災難性轉向。
但不幸的是,把智識史工具化地運用,來重新引領當代政治的作法幾乎是不可能,特別是當這個被召喚的歷史是如此貧乏,不足以支持當事人所要的結論時,更是如此。
話雖如此,儘管Zamora的學術研究有所侷限,但他深信左翼應該在對抗剝削中重新出發卻是對的。如果是這樣,那就遠遠不是要遠離傅柯的影響了,或許現在正是重新處理傅柯思想的時候。畢竟,傅柯比大部分的人都更早認識到,整個社會正在經歷巨大轉變,因此,對抗剝削之戰要如何發起,也必然要跟著轉變。傅柯的思想,遠遠不是Zamora所想的那樣,令左翼無從思考對抗經濟剝削,反之,在一些重要面向上,他的思想還是能夠重新引領左翼。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現在這場戰鬥要如何發起,以及過去為何無法有效發動,那麼,還是需要跳脫傅柯的著作。與其抱怨過去的知識分子需要為當前的低迷情勢負責,或者向他們求助靈丹妙藥來解決我們的問題,最好還是開始多思考我們自身當下。
為了這個不平等的年代而「批判傅柯」,既找不到怪罪對象,也找不到出路。
書籍資訊
《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Critiquer Foucault: Les années 1980 et la tentation néolibérale)-Daniel Zamora,2015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